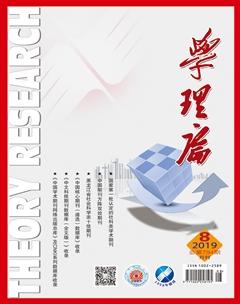馬克思哲學中的革命和正義
葛宇寧 程慕青
摘 要:在馬克思哲學中,革命和正義都是重要的范疇。在過去,由于種種原因,兩者的學理問題并未得到充分研究。但是,在新時代背景下,對其進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馬克思哲學中,革命具有十分廣泛的意義,包含了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自然革命、觀念革命等。這些革命都是通往人的解放的重要路徑,政治革命要變革舊的統治秩序,賦予人民真正的權力;社會革命要建立公正合理的社會關系;自然革命要找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之道;觀念革命則要打破舊觀念的束縛。
關鍵詞:馬克思哲學;革命;正義
中圖分類號:B0-0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9)08-0059-03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革命”和“正義”成為新時代的兩個重要概念。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多個場合使用“革命”這一概念,如“偉大的社會革命”“自我革命”“消費革命”“新科技革命”等,這些都激活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革命”含義。同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公平正義”也多次被寫進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之中,并提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追求”。甚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把追求更高水平的“公平”和“正義”視為人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此,我們很有必要深入發掘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本人關于革命和正義的思想和話語,以更好地哺育時代理論發展和實踐推進。
一、重談馬克思哲學中的革命與正義
在馬克思哲學中,革命和正義都是重要的范疇,都體現出其哲學的本質追求,那就是人的解放,都服務于人類解放事業。革命是實現人類解放的根本途徑,而正義則是人類解放的最終歸宿,或者實現人類解放后的狀態,即建立起“正義的王國”,實現人類社會發展的更高正義。然而,在長期的學術研究中,這兩個概念都沒有得到充分的闡釋。推究起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人們總是對“革命”進行狹義的理解,把革命完全等同于階級斗爭,是要以新的社會形態取代舊的社會形態,實現新舊政權的更替。在當今的和平年代,這種革命活動不處于活躍時期。二是人們囿于舊的社會認識,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正義屬于道義的范疇,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說教,過多地談論正義,會沖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在生前多次批判正義問題,“不屑于”討論正義。
然而這些都是站不住腳的。無論在馬克思本人的學說中,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革命”這一范疇都有著更廣泛的意義。比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說:“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1]在對辯證法的本質理解中,馬克思也表達了這層意思,辯證法“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這些對“革命”的使用,顯然都超越了狹義的范圍。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對廣泛的“革命”也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它是指:“在社會基本矛盾基礎上的社會生活的全面變革,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思維方式、思想觀念的重大變革。”[3]
對馬克思正義問題的傳統理解更是靠不住的。在馬克思的經典文獻中,確實可以看到馬克思本人對正義的批判和嘲諷,比如《資本論》中有一處,他提道:“在這里,同吉爾巴特一起說什么天然正義,這是毫無意義的。”[4]而且,在許多地方,如《哥達綱領批判》中,他也確實認為不應該從正義視角批判資本主義[5]。然而,這些并非馬克思哲學的本意,他只是在說我們不要濫用“正義”的字眼,尤其是不要從資本主義的法權本身來談論正義問題和展開對資本主義正義的批判。這其實是有原因的。其一,馬克思生活的年代是無產階級革命風起云涌的時代,馬克思肯定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革命上,構建一套科學的理論,從歷史必然性的角度來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會滅亡,無產階級革命必然會勝利。其二,從資本主義的法權本身出發,我們確實是無法批判資本主義,視角是存在問題的——資本主義法權顯然是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為此,馬克思對正義的視角進行了轉換,提出了社會正義和歷史辯證正義,主張從超越于資本主義法權制度之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待資本主義正義的問題。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得到客觀正確的結論,那就是:資本主義本身具有一定的正義性,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它會被更高的社會正義所取代[6]。
在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共處的今天,關注馬克思正義觀更顯得十分必要。如果單單從科學性視角來論證社會主義優越于資本主義,顯然難以完全調動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情感,我們還需要論證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具有道義性,也即它更能促進人的解放,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今天我們不能再抱著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睡大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在倫理上也申明自己的倫理立場。人們也許會因為共產主義是科學的理論而相信它,但未必因為它是科學的理論而熱愛它。”[7]正如諾曼·杰拉斯所言,在現代社會背景下,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公開地對他們自己的倫理立場負起責任,詳細說明,捍衛并完善它們。一種經過詳盡闡述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正義觀根本不會是早熟的”[8]。
在談論馬克思哲學中的革命與正義的關系之前,我們還必須對馬克思正義觀的主要內涵或者核心指向有所揭示。在馬克思哲學中,正義到底意味著什么呢?很顯然,如前所述,正義意味著人的解放以及人的解放的目的,是真正實現解放后的狀態。因此,闡述馬克思哲學中的革命和正義,我們必須著眼于發掘出革命的解放意義,或者革命對人的解放的促進性。
二、政治革命與人的解放
在馬克思的學說中,革命首先體現的或者直接體現的就是政治革命,因為生活于現實世界中的人,最先感覺到的就是舊的政權的束縛。無產階級的被統治地位,直接體現為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處于被統治地位,而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處于統治地位,從而資產階級會借助國家政權的力量來鎮壓無產階級的反抗。馬克思早年生活在普魯士的舊政權統治之下,舊政權對其的迫害,多次導致其流離失所,使其深有感觸。所以,馬克思很早就意識到:“一般的革命——推翻現政權和破壞舊關系——是政治行為……社會主義需要這種政治行為,因為它需要消滅和破壞舊的東西。”[9]
同時,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實現國家政權從反動階級手中轉移到革命階級手中,是革命勝利、成功的首要的、基本的標志[3]。不難看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首要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無產階級要通過革命的方式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然后著手對社會各方面進行改造,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的改造。
我們知道,政治是和權力聯系在一起的,而權力則支配著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因此它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影響極大。在反動政治統治之下,由于國家政權掌握在反動的統治階級手中,廣大的人民群眾處于無權或者少權的境地,因此在社會資源分配中就會出現嚴重的不公,統治階級拿走了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可以很好地發展自己。而廣大人民群眾在很多時候,連生存都成問題,更難以談上發展。政治革命就是要打破舊的權力配置,革命階級奪取政治權力,從而改變舊的資源分配標準,來為廣大人民群眾的發展提供條件。
在馬克思的政治革命學說中,政治革命是有一個歸宿的,也就是政治革命的最終結果就是消滅政治,通過無產階級的革命最終徹底鏟除私有制。沒有了私有制,也就不會再有階級的對立,沒有階級的對立,也就不再需要政黨和國家政權,政治也將消失。政治是一種具有強制性的東西,它最終將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退出人類的社會生活領域。
三、社會革命與人的解放
社會對正義的實現,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畢竟人生活在社會中,是一定社會關系的總和。如果正義不能在社會中實現,那么這種正義只能是抽象的正義,停留在觀念之中的正義。在馬克思看來,舊的不合理、不公正的社會關系對人的影響非常大。在一種落后反動的社會關系下,是不可能實現所謂的真正正義的。他說:“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要求平等的或甚至是公平的報酬,就猶如在奴隸制的基礎上要求自由一樣。”[10]
因此,“正義只能是存在于一定社會關系之中的事物,離開一定社會關系的存在,就談不上正義。在馬克思看來,社會正義的實現,不是靠人去順從不合理的社會關系,而是要改變不合理的社會關系以實現人的自由發展。”[6]當然,改變舊的不合理的社會關系,靠的是革命,需要社會革命。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對社會革命問題做過經典表述,在他看來:“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10]這表明,在馬克思看來,社會革命的主要對象就是生產關系,尤其是其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因為在馬克思看來,一切社會關系都可以歸結為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的核心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
生產資料是進行社會再生產的必備條件,是進行社會財富再創造的前提,因此哪個階級掌握著生產資料,哪個階級就會在事實上處于統治地位,就掌握著決定人們發展的權力,因為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著最終的社會勞動產品分配。在馬克思看來,革命階級在政治革命勝利掌握了國家政權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自己的經濟基礎,奪取舊的統治階級的生產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沒收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很快又通過“三大改造”,建立起生產資料公有制,其原因就在于此。
四、自然革命與人的解放
在馬克思的思想中,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分不開的,人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自然,離不開自然界提供的各種物質資料。自然界是人類的各種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來源,離開自然界,我們就無法存活下去。所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還需要自然革命,從自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比如,人類在過去,對臺風的形成和運行規律一無所知,我們就必然會被臺風所“統治”,任其自發地肆虐,人類卻無能為力。但當人類掌握了臺風的形成和運行規律以后,我們就可以準確預報臺風,從而提前進行規避其危害,以方便安排生產生活。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大致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人是自然的仆從,人類敬畏自然、恐懼自然。在傳統社會下,人類的生產力發展比較有限,很多時候,在面對自然時都顯得無能為力,自然界是十分強大的對手,人類就對自然形成了畏懼和敬畏,自然界的很多事物,在人的觀念中,都成了神,甚至一草一木都有了神性。第二階段,隨著現代的工業革命出現,人類的生產力飛速發展,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提升,自然在人的面前再也沒有了神性,它成了人類征服和改造的對象,人類自以為可以把自然完全掌握在股掌之中。然而,自然界很快對人類進行了報復,出現了全球生態危機。在這一階段,人和自然的關系主要是一種對抗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就進入了第三個階段,也即人與自然的關系調適階段,即嘗試與自然進行對話,尋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之道。
馬克思很早就意識到,人對自然的革命就是學會和自然相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馬克思說:“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11]也即,在馬克思看來,自然界就是人的身體的一部分,我們需要不斷地同自然界進行能量交換。“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對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11]也正是因為人的解放、人的發展,和自然的關系如此緊密,在馬克思那里,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和諧解決,也是共產主義的內涵之一。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11]。
五、觀念革命與人的解放
所謂觀念革命,也即觀念解放,是把人從舊的傳統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如前所述,革命在馬克思思想中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是指實現人的整體解放、全面的解放。人不僅是社會的存在物、政治的存在物、自然的存在物,同時,人也是觀念的存在物。人有思想和觀念,這是人比動物高級的地方,同時,人也受觀念的影響和支配。我們常說,觀念是行動的先導,馬克思主義首要的理論品質就是與時俱進,這些都體現出思想和觀念對人的重要影響。
舊觀念是束縛人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自由全面發展的重要羈絆。這一點,在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程中,是一個早已被實踐證明了的真理。改革開放前,人們被教條主義所束縛,不敢與時俱進,社會主義發展遇到挫折。改革開放后,我們在解放思想的指導下,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如今,我們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正昂首挺胸走進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對于觀念和理論的力量,馬克思是十分重視的,他曾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11]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在進行革命過程中,一定要注意觀念改造,改造自己的觀念,也要改造民眾的觀念,把廣大人民群眾從舊的、剝削階級的觀念中解放出來。進行這一工作的主要途徑就是宣傳教育,用新的革命觀念教育群眾,取代舊的觀念。甚至,馬克思在宣傳策略上主張,要不惜“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12]。當然,這是就宣傳策略而言。對于資產階級理論家所創造的優秀思想成果,我們還是要采取“揚棄”的態度。
六、結語
應該說,目前學術界對馬克思哲學中的革命資源和正義資源關注很不夠,未來需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在慶祝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對馬克思的一生以及馬克思的理論貢獻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并要求我們不斷深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的思想,不斷從中汲取“科學智慧和理論力量”,服務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永遠不會過時,將引領中國人民取得新的更大的輝煌。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5.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
[3]本書編寫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40-141,141.
[4]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9.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2.
[6]葛宇寧.馬克思正義理論的倫理特質[J].理論探索,2015(3).
[7]葛宇寧.“塔克—伍德命題”的破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正義批判[J].甘肅理論學刊,2015(5).
[8]李惠斌,李義天.馬克思與正義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197.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88.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2-3.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191,185,11.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