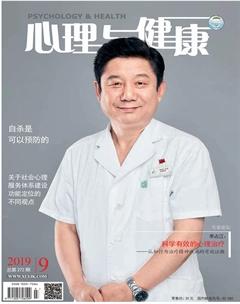關于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功能定位的不同觀點
祝卓宏
自十九大以來,全國社會心理學及臨床心理學專家積極貫徹落實十九大報告精神,緊緊圍繞社會心理服務的定位與思路、實踐模式與理論研究方向等開展了廣泛研討,努力凝聚學術共識,加緊匯聚研究力量,爭先發出學界聲音,積極引領實踐走向。
然而,在自由學術研討過程中也有專家發出不同的聲音,引發了學術爭鳴,特別是關于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定位,大家對政策有不同的解讀。本文試圖從政策語境的視角,嘗試解析我國當下社會語境下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功能定位,以求拋磚引玉,引發更多真知灼見。
由于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屬于中國新時代社會語境下特有的新概念、新命題,關于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定位及主要內容引發學界的廣泛討論,主要涉及五類觀點。
1第一種觀點認為,雖然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和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建設不同,但是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首要或核心內容是心理健康服務。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傅小蘭研究員提出“我國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工作包括:第一,構建完善的心理健康服務網絡。第二,在社會治理體系中加強心理建設”(傅小蘭,2017)。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陳雪峰也認為“從我國的發展實踐來看,當前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核心內容是通過心理健康服務來提升人民心理健康水平、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陳雪峰,2017)。顯然這兩位學者的觀點強調了目前階段心理健康服務是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首要或核心內容,基于現實基礎,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首先是心理健康服務。
2第二種觀點則明顯不同,認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要與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建設應該清晰區分開來,不能混淆兩個概念。中央財經大學辛自強教授提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內涵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和技術解決社會治理難題”,“要在制度和人的層面開展心理建設,尊重、理解并依循心理行為規律開展社會治理”,“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不是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建設”,社會心理服務不等同“治病救人”,而是“由心而治”的社會治理,“要防止當前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滑入心理健康服務的思維中”“在實際工作和政策設計中,我們可以將心理健康服務作為廣義社會心理服務的一塊重要內容,但在理論上,我們不能混淆這兩個概念”(辛自強,2018,2019)。中社社會工作發展基金會理事長趙蓬奇認為“要真正從社會治理的背景下,從社會整體的心理需求出發,來發揮社會心理服務作用,優化心理素質,開發心理潛能,影響和改善社會心態,有效提升人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和安全感”(趙蓬奇,2018)。這兩位專家的觀點明顯是在社會心理學語境下界定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在社會治理領域的的功能定位。
3第三種觀點雖然認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與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建設不同,但是,心理健康服務體系是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最重要的基礎,是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最后一關,是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守門員。北京師范大學喬志宏教授認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建設應當涵蓋從治國到治人到治病,從預防普遍性心理問題發生到干預已發生心理問題的全過程”。這一觀點明顯是以“治國治人治病”為隱喻,是圍繞心理問題的預防與干預而展開,明顯是臨床心理學語境下的話語描述。這與第一種觀點基本一致,只是對于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建設作用的界定有所不同(喬志宏,2019)。
4第四種觀點認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不僅僅是心理健康服務體系,而且是一種社會治理體系,是心理學在社會治理中的應用,是心理學應用體系和社會治理體系的雙向契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王俊秀研究員長期研究社會心態,他認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追求社會整體幸福的發展目標是社會治理的重要指向,進而也是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目標。他認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應包括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宏觀層面旨在實現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目標;中觀層面是健康社區、行業和領域的培育和塑造,這是培育社會心態的重要方面;微觀層面旨在從個體、人際、群體和群際等方面培育個體心理健康、人際關系、群體和群際和諧(王俊秀,2018)。顯然,這一觀點認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內涵非常豐富,是在心理學及社會治理宏大語境下建構的三層次體系,而心理健康只是其中微觀層面的一小部分內容。
5第五種觀點認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應是公共心理服務體系,其主要內容包括心理健康服務、社會心態培育、共同體認同建構這三大模塊,其主要功能分別為預防和治療心理疾病、提升全民族的心理健康水平,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以及塑造中華民族的統一文化認同和人類命運共同體認同。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呂小康認為必須緊緊圍繞“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這一根本出發點來理解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功能定位,而不能僅僅將社會心理服務等同于心理健康服務。他強調需要突破個體心理的小視角而從社會心理的綜合性視角,突破狹義的社會心理學這一單一學科視角而從社會治理的協同視角,重點圍繞疏解妨礙社會治理的負性社會心態和建構促進社會治理的良性社會心態這一反一正兩個方面探索社會心理服務的實務工作模式。社會心理服務本質上是一種新型的公共服務,在新華社翻譯的十九大報告英文版中,中文報告中的“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已譯為“We?will?improve?the?system?of?publicpsychological?services,?and?cultivate?self-esteem,?self-confidence,?rationality,?composure,?and?optimism?among?our?people”其中“社會心理服務體系”使用“systemof?public?psychological?services”,直譯為“公共心理服務體系”。政府理應承擔起社會心理服務的總供給者和總籌劃者的職責(呂小康,2019)。這一觀點強調了社會心理服務的公共服務性質以及政府主體性責任,增加了文化的視角和民族認同的觀點。
以上這些學者的觀點均從自己熟悉的研究領域,在不同語境下界定了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功能定位。所有觀點均認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與心理健康服務體系不是一回事,但是,最大的區別在于兩者是包含關系(圖一、圖二)還是并列或交叉關系(圖三)。
陳雪峰認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也是一個發展中的體系,從21世紀初以心理疏導和心理健康教育為主,發展到目前既重視心理健康、也重視通過心理健康服務來實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目標,未來應向更全面的、支撐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心理建設發展。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和新興分支學科的涌現,還將有更多的心理學分支學科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提供直接的學科支持(陳雪峰,2018)。
而辛自強則認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與“心理健康服務(體系)”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二者各有明確的含義,不能相互替代,不能混同使用。正確理解社會心理服務的內涵和定位是制定政策、開展實際工作的基礎,我們要防止當前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滑入心理健康服務的思維中(辛自強,2018)。他認為未來心理建設應該成為第六大建設的國家戰略(辛自強,2017)。兩種觀點均認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是不斷發展的體系,不同的是合成一條線發展,還是分成兩條線相對獨立發展。
中華女子學院兒童發展與教育學院池麗萍教授對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實踐案例進行分析之后認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普遍存在“心理健康服務”傾向。呂小康等認為目前開展的社會心理服務實踐,以及學界的相關研究,基本上把“社會心理服務”等同于“心理健康服務”。可見,目前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功能定位與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建設的功能定位存在很多重疊,更符合第一種觀點,而沒有體現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在社會治理領域的功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