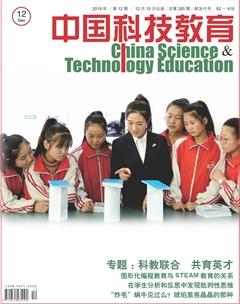泰國(guó)科技之父
陳巍,理學(xué)博士,現(xiàn)為中國(guó)科學(xué)院自然科學(xué)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科技知識(shí)在古代世界的傳播并把世界連為一體的歷程。喜愛(ài)“上窮碧落下黃泉”,品鑒各個(gè)文明在應(yīng)對(duì)相似問(wèn)題時(shí)展現(xiàn)出的智慧。
在科技史上,曾有很多人為科學(xué)事業(yè)獻(xiàn)出生命,也有不少鼓勵(lì)甚至業(yè)余從事學(xué)術(shù)研究的君主。不過(guò),兩種命運(yùn)交叉,出身社會(huì)頂層又因科學(xué)活動(dòng)喪生的情況就很罕見(jiàn)了。在并不遙遠(yuǎn)的100多年前,這樣的事情就發(fā)生在我們的近鄰——泰國(guó)。這位國(guó)王對(duì)科學(xué)的尊崇甚至使其祖國(guó)得以在殖民時(shí)代可敬地保持獨(dú)立。顯然,我們不能因他的魯莽而感到遺憾,而只能對(duì)他事必躬親的精神表達(dá)佩服。這名國(guó)王就是被尊稱為“泰國(guó)科技之父”的拉瑪四世(Rama IV,1804-1868)。
修行生涯
拉瑪四世名為蒙固,是拉瑪二世的兒子,其母親是一名陳姓華裔商人的女兒。作為嫡長(zhǎng)子,他本應(yīng)是王位第一繼承人,且自幼以知識(shí)淵博著稱。20歲時(shí),他遵從泰國(guó)習(xí)俗,即青年男子應(yīng)當(dāng)出家一段時(shí)間,而削發(fā)為僧。不料,僅僅2個(gè)星期之后,拉瑪二世就猝然去世。大部分貴族擁立年紀(jì)較長(zhǎng)、更有內(nèi)政外交經(jīng)驗(yàn)的王妃之子,蒙固的大哥即位,也就是拉瑪三世。認(rèn)識(shí)到無(wú)力改變現(xiàn)實(shí)后,蒙固只好到全國(guó)各地行腳云游。面對(duì)下層人民的艱苦生活,以及日益逼近的西方殖民主義,他在此期間絕非不問(wèn)世事,而是積極思考,為國(guó)家和民族尋找出路。
盡管身份很傳統(tǒng),蒙固并沒(méi)有把自己的觀念保守地束縛起來(lái)。1836年,他成為曼谷波穩(wěn)尼威寺的首任方丈。在這里他開始向居住在附近的歐洲傳教士和水手們學(xué)習(xí)西方知識(shí),包括拉丁語(yǔ)、英語(yǔ)和天文學(xué)等。蒙固甚至準(zhǔn)許傳教士在寺廟里布道。總體上,他贊揚(yáng)的是歐洲人達(dá)到的道德和學(xué)術(shù)成就,而并不認(rèn)為皈依他們的信仰是一項(xiàng)明智的選擇。如果我們看到,在同一時(shí)間,中國(guó)還僅有林則徐等少數(shù)知識(shí)分子認(rèn)識(shí)到了解西方的重要意義,而在1850年代中國(guó)史料里,就留下泰國(guó)國(guó)王“通佛書,善英語(yǔ),用歐人改制度,行新政,國(guó)治日隆”的記載,就能體會(huì)到作為統(tǒng)治階層一員,蒙固的開明態(tài)度是多么難能可貴。
新政強(qiáng)國(guó)
1851年,拉瑪三世去世,年近五旬的蒙固終于獲得貴族們認(rèn)可,繼承王位成為拉瑪四世。在此前27年僧人生活期間,他在職權(quán)范圍內(nèi)倡導(dǎo)的宗教改革,一方面讓社會(huì)信仰的松弛面貌煥然一新,另一方面也竭力祛除了佛教活動(dòng)中的民間迷信成分。執(zhí)政之后,他進(jìn)一步試圖使這類精神文明建設(shè)能夠?yàn)橥饨坏戎卮笫聞?wù)提供支持。
在即位前,拉瑪四世就知道清朝因全然排斥西方文明而在鴉片戰(zhàn)爭(zhēng)中完敗。由于拉瑪四世對(duì)西方已有一定了解甚至好感,他認(rèn)為西方的影響會(huì)帶來(lái)危險(xiǎn),但比起中國(guó)、安南等因抗拒招致炮火,前者危險(xiǎn)要小得多。因此他在外籍顧問(wèn)幫助下,尋求通過(guò)有限改革的方式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的近代化。
擺脫危機(jī)談何容易。拉瑪四世當(dāng)改期間,西方兩大豪強(qiáng)給泰國(guó)施加的壓力更大了。西邊有已經(jīng)控制印度和緬甸的英國(guó)虎視眈眈,東邊則是法國(guó)人蠶食而來(lái)。1863年,泰國(guó)傳統(tǒng)的藩屬國(guó)柬埔寨被迫接受法國(guó)的“保護(hù)”,這迫使拉瑪四世思考,在東面的“鱷魚”和西面的“鯨魚”之間,猶如三明治夾心般的泰國(guó),應(yīng)當(dāng)何去何從?列強(qiáng)侵入亞洲的腳步,能否繞過(guò)泰國(guó)呢?
對(duì)此,拉瑪四世三管齊下。他“以空間換時(shí)間”,被迫簽訂了一些不平等條約,策略性地放棄對(duì)部分非核心領(lǐng)土的控制;同時(shí)試圖小心翼翼地在大國(guó)之間取得平衡,左右逢源;在文化上,他期待借助推動(dòng)科學(xué)研究,展示泰國(guó)是能夠調(diào)和近代與傳統(tǒng)、適應(yīng)時(shí)代的國(guó)家,而絕非一個(gè)野蠻民族。
1868年,一次絕好的通過(guò)科學(xué)展示泰國(guó)擁抱近代文化決心的機(jī)會(huì),似乎到來(lái)了。
暹羅國(guó)王的日食
這次機(jī)會(huì)就是1868年8月18日的日全食。當(dāng)時(shí),對(duì)太陽(yáng)日珥、色球?qū)雍腿彰岬难芯浚翘煳膶W(xué)的重要問(wèn)題。它們究竟屬于太陽(yáng),抑或僅是地球大氣或月亮現(xiàn)象,此前仍處于爭(zhēng)論中。這時(shí)恰逢攝影術(shù)和太陽(yáng)光譜學(xué)的出現(xiàn),天文學(xué)家急于把這2種“新武器”應(yīng)用到太陽(yáng)觀測(cè)上。
日食常有,但對(duì)泰國(guó)如此“友善”的日食卻不常有。這次日食前后月亮剛巧處于一個(gè)非常靠近地球的位置,使得遮住太陽(yáng)的月影極為龐大。這使得西方各國(guó)天文學(xué)家都摩拳擦掌,對(duì)這次日食翹首以待。英國(guó)、德國(guó)、荷蘭等國(guó)的學(xué)者分別準(zhǔn)備在日食帶最西側(cè)的亞丁、印度,以及最東側(cè)的蘇拉威西等地展開觀測(cè)。但天文學(xué)家最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正處于泰國(guó)。在泰國(guó)灣一帶,太陽(yáng)將被完全遮蓋長(zhǎng)達(dá)6分50秒,人們能夠比在印度多獲得1分鐘的觀測(cè)時(shí)間。而且這個(gè)季節(jié)正處于印度洋季風(fēng)帶的雨季,在西邊有山脈遮擋的陸地東緣選擇觀測(cè)點(diǎn),具有最適宜的天氣條件。這樣,現(xiàn)今泰國(guó)班武里府的華高(Waghor)就成為最理想的觀測(cè)地,那里東臨大海,西邊則是海拔千米左右的高山。
于是,曾經(jīng)算出海王星軌道的巴黎天文臺(tái)臺(tái)長(zhǎng)勒維耶,開始積極運(yùn)作觀測(cè)日食事宜。幾經(jīng)波折,他終于得到許可和預(yù)算支持,組織了包括3名年輕天文學(xué)家在內(nèi)的科考隊(duì),前往泰國(guó)。而另一名與其關(guān)系疏遠(yuǎn)的天文學(xué)家讓森,選擇到印度觀測(cè)。
法國(guó)科學(xué)家事先知道泰王拉瑪四世愛(ài)好天文,但到達(dá)后,他們?nèi)圆粺o(wú)驚訝地發(fā)現(xiàn),泰國(guó)人已經(jīng)在那里建起一片臨時(shí)宮殿。拉瑪四世早已準(zhǔn)備在這里接待受邀前來(lái)觀看日食的王公貴族和外賓。當(dāng)?shù)氐屯莸牡匦危尭鲊?guó)人士都飽受蚊蟲之苦,但對(duì)于法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至少不會(huì)出現(xiàn)此前傳說(shuō)中經(jīng)常襲擊村民的猛虎了。
事實(shí)上,至少在日食之前2年,拉瑪四世就開始精心籌劃利用這次日食大展宏圖。他利用從傳教士那里學(xué)到的西方天文學(xué)知識(shí),計(jì)算出了日食的發(fā)生時(shí)間和觀測(cè)地點(diǎn)。他得到的日食時(shí)間比法國(guó)人還要精確2分鐘。
盡管占星者聲稱,國(guó)王會(huì)因親自觀測(cè)日食而導(dǎo)致災(zāi)難。但準(zhǔn)確預(yù)測(cè)日食,而不是聽?wèi){占星者擺布,被認(rèn)為是宣揚(yáng)近代科學(xué)與理性的好選擇,因此拉瑪四世在不祥預(yù)言下,仍堅(jiān)持在低洼處建設(shè)觀測(cè)行宮。
法國(guó)科考隊(duì)并不“孤單”,他們發(fā)現(xiàn)國(guó)王出于平衡的目的,還邀請(qǐng)了英國(guó)駐新加坡總督前來(lái)觀測(cè)。拉瑪四世舉行了隆重的儀式,當(dāng)時(shí)泰國(guó)灣麇集著英國(guó)軍艦及其他船只,這讓前來(lái)科考的法國(guó)人聲勢(shì)相形見(jiàn)絀。
在天時(shí)地利人和各方面配合下,日食觀測(cè)取得了圓滿成功。由于拉瑪四世精確的預(yù)測(cè),以及對(duì)國(guó)外科學(xué)家的盛情接待,此次日食被稱為“暹羅國(guó)王的日食”,它可以稱得上是落后地區(qū)為取得多重目的,而對(duì)現(xiàn)代科學(xué)的一次典范性運(yùn)用。華高后來(lái)還建有拉瑪四世觀測(cè)活動(dòng)的紀(jì)念館。不過(guò)在科學(xué)史上,除拉瑪四世外,因這次日食而享有盛名的,并非前往泰國(guó)的法國(guó)觀測(cè)者,而是從印度歸來(lái)的讓森。他在太陽(yáng)光譜中觀察到一根陌生的譜線,這最終導(dǎo)致了氦元素的發(fā)現(xiàn)。
然而,不知為何卻如占卜者所言,這為國(guó)王個(gè)人命運(yùn)帶來(lái)一場(chǎng)悲劇。肆虐的蚊蟲不但讓10余名法國(guó)科考隊(duì)員高燒不退,迫使他們迅速回國(guó),而且還讓國(guó)王父子都染上瘧疾。1個(gè)多月后,拉瑪四世與世長(zhǎng)辭,而年輕的皇子最終康復(fù),成為新的國(guó)王拉瑪五世。
日食觀測(cè)的最終贏家,屬于這個(gè)國(guó)家。拉瑪四世雖然壯志未酬,但他的精神卻影響深遠(yuǎn)。拉瑪五世全面繼承了他對(duì)內(nèi)改革寬容、對(duì)外融人世界的政策,甚至模仿父親,邀請(qǐng)英國(guó)學(xué)者到泰國(guó)觀測(cè)了1875年日全食。在拉瑪四世父子努力下,泰國(guó)安然度過(guò)19世紀(jì),成為近代史上東亞除中國(guó)、日本外唯一一個(gè)保持主權(quán)獨(dú)立的國(guó)家,而對(duì)科學(xué)善加運(yùn)用,正是他們獲取世人尊敬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