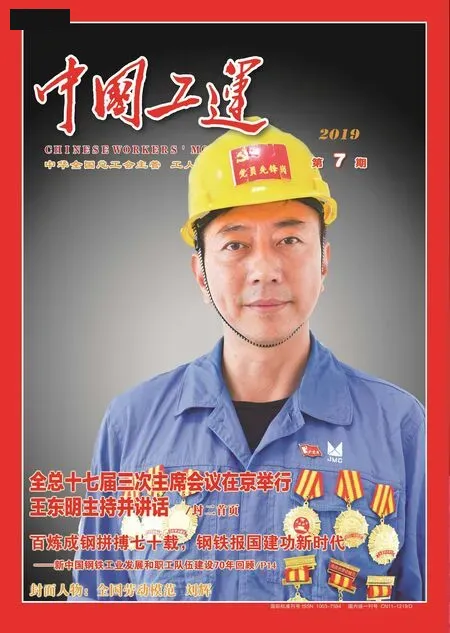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關系問題研究
文/中國工運研究所 張立新

“平臺+從業者”在我國屬新就業形態,這一發端于國外的業態“子彈”已經在國內飛了幾年,如今互聯網平臺企業叢生,網約的司機、家政員、美容師、美發師、廚師等“網約工”劇增。互聯網平臺用工有別于工作時間、地點、內容相對固定的傳統“單位制”用工,工作指令、業務信息、資金結算、獎勵懲罰等全部信息化,網約工可以選擇工作時長、服務頻次以及是否接受互聯網平臺指派,便捷靈活是其主要特點。與互聯網平臺用工的便捷靈活相伴隨,數千萬網約工群體對平臺可能存在的從屬性也被虛化,多處于無勞動合同、無社會保障狀態。互聯網平臺企業的用工創新為其勃興提供了支持,也帶來了與網約工法律關系性質的爭執。
互聯網平臺用工法律關系確認問題
多數平臺企業堅持新業態之新,就包括了與網約工不形成勞動關系。為將自己隔離于勞動關系,避免發生直接用工,許多平臺企業設計復雜的法律關系,常見的有居間、聯營、承包等民事關系,有的找用工地外包商與網約工簽合同甩責,以實現其所謂的用工靈活、“資產輕質化”等經營目標。網約工則通過勞動爭議仲裁與訴訟對抗這一創新,要求確認勞動關系。
2015年至2018年一季度北京朝陽區法院受理的188件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爭議案件均為服務業,主要涵蓋司機、家政員、美容師、美發師、廚師等職業,涉及12個互聯網平臺。在審結的171件案件中,超過84%的案件雙方對是否建立勞動關系存在爭議,這些案件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網約工對建立勞動關系的集中訴求。
互聯網平臺企業堅持用工自由,網約工期待得到勞動法保護,爭執源自現行法律體系的設計。在勞動關系中,勞動者享有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保護,最低工資保障,參加職業培訓和社會保險,勞動合同解除還可主張經濟補償金等等。多數平臺企業拒絕與網約工建立勞動關系,主要是不愿承擔這些用人成本。對網約工而言,認定為勞動關系便“應有盡有”,否定勞動關系則“一無所有”。
在勞動關系確認的規則上,我國堅持從屬性的思路,采用了統一標準,目前仍沿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5】第12號文《關于確認勞動關系事項的通知》。根據該通知,勞動關系的成立,除雙方符合主體資格外,需結合單位與個人之間的人事管理、報酬支付和業務范疇三方面判斷從屬性。依照這一判斷標準,互聯網平臺與網約工之間的人事管理若即若離,報酬獲取方式靈活多樣,特別是平臺業務范疇含混不清。網約工從互聯網平臺獲取服務信息,其勞動似乎應屬互聯網平臺業務,但互聯網平臺實際從業應用軟件開發和服務信息的整體推送,并不直接經營實體業務,網約工的勞動與互聯網平臺的業務范疇又有較大區別,這些新問題造成從屬性認定困難。
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適法性認識
“平臺+從業者”新就業形態下,受到最直接影響的是網約工及其他生產服務鏈上的從業者。平衡好新經濟發展與網約工權益保護,亟須調整傳統社會保障體系,規范社會監管體系,以及法院判例的指引。
從包容走向調整。作為第三方監管者,政府主管部門的態度對于網約平臺用工性質及其走向有很大影響。以網約車為例,2016年7月,交通運輸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7個部門聯合頒布《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要求網約車平臺公司應當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與駕駛員簽訂多種形式的勞動合同或者協議,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2017年11月,食品藥品監管總局發布的《網絡餐飲服務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辦法》中,通過具體條款對網絡餐飲平臺的用工情況進行了劃分,外賣人員可以與網絡餐飲平臺、餐廳或者委托送餐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或者協議。這些政府部門的規定,都將網絡平臺經營者與相關從業人員之間的用工關系性質按約定處理作為認定的原則,這可能形成有利于互聯網平臺企業排除勞動關系的局面。
我們認為,當前網約平臺與網約工可以選擇用工方式,但必須經過有效協商。國家應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地方立法也可以進行探索嘗試,明確不同就業形態的認定邊界,強化平臺企業的用工主體責任,加大監管力度,保障網約工的權益。立法中,根據互聯網時代勞動特征和新變化,擴大勞動關系的定義,使其更符合勞動力市場的需求,鼓勵各地就薪酬構建、勞動時間、休息休假等進行適度規范和標準制定,為網約工等新形態就業人員建立與其行業相對應的社會保險制度。
優先或參照適用勞動合同法。平臺企業與網約工可以簽訂多種形式的勞動合同或協議,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但簽訂的內容需與實際用工情況相符,并且應是經充分磋商和溝通后雙方真實意思的體現,而非單方免除法定責任、排除他方權利的條款,更不能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規定。特別是在網約工發生工傷時,能夠依據勞動法律獲得有效的救濟。
政府部門應當明確要求平臺企業投入人力資源管理,指導其與全職網約工簽訂勞動合同:符合非全日制用工的,雙方當事人可以依法訂立勞動合同,從事非全日制用工的網約工可以與一個或者幾個平臺企業訂立勞動合同。這樣既保障平臺用工需求,又保障網約工的勞動權益,還兼顧到本行業經營者如傳統用工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勞動關系認定標準適度從寬。由于互聯網平臺企業對從業者大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規范或指示,一旦因勞動者提起訴請,確認勞動關系幾乎成為規定動作,判斷從屬性成為處理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爭議裁審的核心。當前從業者數量的大幅度增長,涉互聯網平臺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可能繼續增加。圍繞現有審判框架,只有立足“實質審查原則”,即實際履行與約定不一致或雙方未約定的,以實際履行情況認定,秉承相對寬容理念,最大程度維護網約工合法權益,才能避免越來越多的網約工被“臨時工”。
互聯網平臺用工多樣化體系標準的構建
適應互聯網多元靈活用工形態的發展,進一步創造穩定就業崗位,彌合互聯網平臺與網約工處于勞動關系與民事關系之間的模糊地帶,平臺用工可以構建多樣化體系標準。
對勞動關系和其他關系用工進行精細化區分和規范化管理。行業自律性組織應出臺適合平臺企業不同用工類型的指導性文件,明確該行業勞動用工標準,杜絕平臺企業使用霸王條款、協議。例如,根據派工與接單、全職與兼職、在一個平臺與幾個平臺接活兒、有社會保險與無社會保險等等,綜合確定勞動關系或其他關系標準,為互聯網平臺和網約工提供規范指導。
構建層次性的社會保障體系。平臺企業與網約工之間勞動關系與民事關系之爭,核心是網約工能否享有社會保險之爭。設計多元靈活型用工形態和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囊括不同法律性質勞動用工社會保險,有利于維護網約工等從業人員的基本權利。具體而言,工傷保險可以在《社會保險法》框架下,對社會保險關系和勞動關系進行必要區分,即規定社會保險中的“工傷保險”以用工為前提,而非以“勞動關系”建立為前提,最大程度地減少網約工工傷損失。組織網約工加入靈活就業人員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達到保護網約工基本權益的目的。鼓勵平臺企業為網約工辦理健康險、人身意外險等,費用由平臺多承擔一些。
平臺企業與網約工法律關系屬性亟待破解
穩就業是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最大的民生。不斷涌現的新業態特別是在服務業領域,就業的空間很大,勞動爭議糾紛也在增加。互聯網平臺企業良性發展需要空間,網約工切身利益需要保障,涉互聯網平臺企業勞動爭議案件糾紛需要處理,這些問題都直指平臺企業與網約工法律關系屬性。
互聯網平臺用工法律關系究竟如何定位,還不僅僅是網約工身份確認這一單純問題,更涉及到與傳統就業如何擺布協調,滿足靈活就業市場需求和高質量穩定就業的長遠考量。不承擔人力成本是許多互聯網平臺的生存之道,可以斷定,如無法律政策干預,大多數互聯網平臺企業不會與網約工建立勞動關系,而還在壯大的網約工隊伍得不到應有的社會保障,同行業傳統就業又受到沖擊,可能累積起各種社會矛盾。
促進正規就業,實現構建穩定、和諧的勞動關系,依然是當前的就業目標。從總體上講,勞動者就業形式愈正規,勞動就業的崗位就愈穩定,勞動關系就愈和諧,而勞動關系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的根本所系。因此,以正規就業崗位的增長與正規就業人數的增長作為評估用人單位或者雇主的社會責任,是時代發展的內在要求。借助互聯網,松散的社會協作帶來效率和速度,但是,社會本身并不松散,互聯網平臺企業的社會責任并不能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