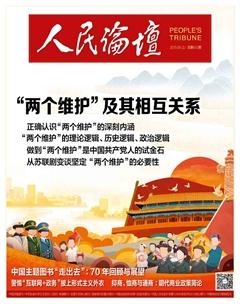從蘇聯劇變談堅定“兩個維護”的必要性
李瑞琴
【摘要】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蘇聯解體最深刻的教訓,是蘇聯共產黨本身出了問題。一個有著近百年歷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鳥獸散”“分崩離析”警示我們,要深刻理解“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重大、深遠意義。
【關鍵詞】“兩個維護” 歷史鏡鑒 【中圖分類號】D507 【文獻標識碼】A
蘇聯共產黨(以下簡稱“蘇共”)是在建黨93年、執政74年時亡黨亡國的。蘇聯解體最深刻的警示和教訓,就是蘇共本身出了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說:“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一個有著近百年歷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鳥獸散”“分崩離析”,警示我們,要深刻理解2018年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增寫“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重大、深遠意義。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蘇共亡黨亡國在這方面給了我們怎樣的歷史鏡鑒?應該如何記取?

黨的領袖的理論品質、天下胸懷、人民至上情懷,是“兩個維護”提出、踐行的首要條件和必備要素
“兩個維護”對于執政黨的領袖有著極高的要求。一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領袖成為全黨的核心,成為全國人民衷心愛戴的領袖,不是自封的,更不是在其位便可自然而成。黨的領導人需要具備高瞻遠矚的政治理論遠見,堅定非凡、無所畏懼的革命理想信念,勇于開拓創新、善于駕馭復雜局勢的高超領導能力。更為重要的是,能夠代表黨和人民事業進步、勝利的方向。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領導全國人民戮力同心,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在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紛繁復雜局勢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走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以21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思想家、戰略家的堅定品質,以夙夜在公、以身許黨的領袖風范,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人民情懷,以“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天下胸懷,贏得了黨和人民的衷心擁護、愛戴。“兩個維護”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進的歷史選擇,是執政黨政治建設、組織建設、紀律建設的客觀需要,是黨領導人民克服千難萬險去爭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蘇共自列寧斯大林之后,黨的領導人總體素質下滑,上述品質是欠缺的。黨的領導人的理論修養及其執政能力沒有與時俱進:赫魯曉夫“明顯缺乏堅定性和文化理論修養”;勃列日涅夫愛慕虛榮,平庸奢侈,是獲得“獎章”最多的蘇聯領導人,其執政后期蘇共威信嚴重下降;戈爾巴喬夫則從思想上、行動上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蛻變成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1991年8月,戈爾巴喬夫宣布蘇共自行解散時,蘇聯人民已經由痛徹心扉轉而報之以冷漠。戈爾巴喬夫喪失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基本品格,喪失了人民群眾擁戴的必備品質。蘇聯解體近30年來,戈爾巴喬夫一直是不受俄羅斯民眾歡迎的人。
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政治上理論上的高度成熟、高度自信、清醒自覺,是“兩個維護”得以提出、踐行的強大根基和力量所在
思想的旅程揮就實踐的交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準確把握時代特點、歷史新方位,把握時代發展的新變化、新要求,科學回答了時代和社會實踐提出的重大理論、現實問題。理論上的清醒與成熟、自信與自覺,是政治堅定、永葆磅礴偉力的前提和保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發軔于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戰略思維、歷史思維之巔,又寓于人類歷史長河的辯證思維、創新思維之中,立足當代世界客觀實際、尊重歷史規律、勇立世界大勢潮頭。黨中央的權威性來自于執政黨理論的清醒與成熟、自信和自覺的自然天成,來自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遠的時代意義、理論意義、實踐意義和世界意義。這奠定了“兩個維護”深厚的根基和堅實的客觀基礎。
蘇共在這方面留下了很深刻、慘痛的教訓。蘇共在執政后期,教條主義、保守主義盛行,黨內思想僵化,不思進取,遠遠落后于時代和社會實踐的要求。在改革時代,蘇共領導層本應立足于蘇聯國情,根據時代的要求,以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承擔黨和國家面臨的緊迫任務,但戈爾巴喬夫等改革派,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理論,以“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會主義”等抽象、模糊、概念不清的西方“普世價值”術語,將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灌輸、推行到蘇聯改革過程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形成、實踐于蘇聯改革的過程,正是蘇聯演變、蘇共亡黨、國家走向解體的過程,將黨和國家引向了一條改旗易幟的不歸路。
執政黨堅守人民立場、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使命初心、永恒追求,是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不竭動力和力量源泉
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堅守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政治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馬克思主義的初心,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習近平總書記說:“不謀私利才能謀根本、謀大利,才能從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出發,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檢視自己。”在中國幾代共產黨人血脈中永遠鮮活熱烈的、一以貫之的,就是馬克思主義鮮明的人民性品格。這種情懷和責任,這種擔當和使命,這種自覺和自信,如壯麗的日出,引領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公生明、廉生威”,“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這是我們黨在《條例》中增寫“兩個維護”的無畏勇氣和無窮力量,是“兩個維護”的不竭動力和源泉,是執政黨堅守人民立場“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氣概和坦蕩。
蘇共在很長一個時期里都能夠代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并且得到了人民的高度信賴,激發了人民忘我的革命和建設熱情。在蘇共的堅強領導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犧牲,奪取并鞏固了政權,打敗了外敵入侵,建設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這個人民的黨在執政后期,逐漸忽視了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出現了與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相對立的官僚特權階層。戰爭年代曾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魚水之情,成為遙遠的歷史。“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價值取向被踐踏,黨的根本宗旨被拋棄。執政黨忘卻了人民立場,忘記了黨的初心使命,注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亡黨亡國不可避免,“兩個維護”更是奢談。
執政黨高遠的戰略定力、鐵的政治規矩,是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意志要求和根本保證
源于對人類發展規律深刻認識而確立的理想信念,是執政黨高遠戰略定力的根基和源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我們確立的奮斗目標,我們既要有‘亂云飛渡仍從容的戰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長城非好漢的進取精神。”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要增強政治定力、紀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的團結統一,為全黨作出表率。鐵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為“兩個維護”提出了必備的主客觀要求和方法。黨員干部要具備“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政治定力,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紀律定力;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定力;要有“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抵腐定力。在復雜艱難的國內外形勢下,始終做到“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戰略定力、政治規矩鑄造了“兩個維護”的內在功力、意志品質。
再回首蘇聯劇變的歷史,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改革的倡導者和領導者,其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界觀,使改革從開始就走上了偏離科學社會主義的軌道。其以“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革新蘇共,放棄黨的政治紀律實行無底線民主,蘇共各項紀律尤其是政治紀律被嚴重削弱,黨內思想混亂,派別林立、亂象叢生,毀滅性地侵害了黨的肌體。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通過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聲明和新黨章,明確放棄馬克思主義指導,標志著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發生本質變化。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蘇聯亡黨亡國的雙重悲劇說明,理想信念的坍塌,黨就喪失了形成、具備執政黨高遠戰略定力、鐵的政治規矩的可能性和條件,“兩個維護”更無從談起。
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是賦予“兩個維護”的責任擔當和崇高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目的也是謀求各國發展戰略對接,形成共同發展勢頭,增強對美好未來的信心。“三為三謀”飽含對人類發展重大問題的睿智思考和獨特創見,是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孜孜以求的光榮和夢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無私崇高的價值取向,也向世界昭示了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對世界文明、人類發展作出貢獻者,才能領航世界;其理論與實踐能夠惠及世界最廣大人民,才能有引領力和感召力,才能代表人類發展大勢。“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黃沙始到金”。共產黨人的崇高使命、責任擔當,與“兩個維護”相得益彰,相輔相成,互為動因,統一于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的偉大事業中。“兩個維護”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召喚,是人民的深重寄托。
蘇共的軟弱渙散,喪失戰斗力,根本在于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崇高而遠大的目標,丟失了為人類求解放的終極理想信念。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蘇共言行不一、形式主義、夸夸其談、只說不做成為普遍現象。“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蘇共盡管在隊伍人數上不斷擴大,但是正統思想的影響力卻日趨減弱,黨的威信不斷下降。”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革新后的蘇共一觸即潰,全黨全民人心渙散。昔日列寧斯大林締造、領導的鋼鐵洪流般的蘇聯共產黨,消遁于理想信念、責任使命喪失殆盡的歷史倒退中,黯然退出歷史舞臺。
從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生死存亡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看,維護黨的領袖的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的權威,毫無疑問,是黨始終保持戰斗力、凝聚力、統一意志、在復雜激烈的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中保持清醒頭腦,在復雜而險惡的國際環境之下,立于不敗之地,并能夠不斷發展壯大的根本保證。社會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發展,從來都是在各種勢力激烈較量中開拓前進的。“兩個維護”源于我們黨的寶貴歷史傳承,警示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深刻教訓。歷史鏡鑒,猶在左右,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部負責人、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2019年第7期。
②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3年12月26日。
③[俄]羅伊·麥德維杰夫:《蘇聯的最后一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