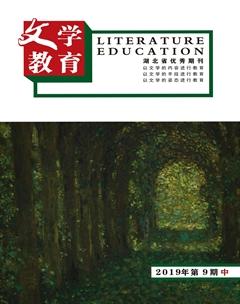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說中的空間表征與倫理張力
內容摘要:結合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和空間理論對阿加莎·克里斯蒂已出版偵探作品分析發現,克里斯蒂小說中獨特的鄉村設景空間與英國傳統文學觀念存在極大不同,帶給了讀者與眾不同的閱讀體驗。這不但是將時代倫理問題入文的寫作探索,更是為突出倫理問題而進行的功能性敘述。在這樣實驗性的空間場域中,犯罪背后的倫理問題和困境也因此得到極具深度和張力的表現,作者本人的倫理觀念也得以彰顯。
關鍵詞:阿加莎·克里斯蒂 偵探小說 空間 文學倫理學批評
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其數量眾多和構思精妙的作品受到眾多讀者的歡迎。但其作品在學術領域大多數時候仍然被作為通俗文學進行解讀,而缺乏對其深度價值的挖掘,在空間與倫理等議題上更是未受到關注。
本文立足于對克里斯蒂已出版的偵探小說的細讀,主要運用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和空間理論,從克式偵探小說獨特的鄉村設景空間切入,審視其中空間特性,以及其與倫理之間的互動關系,以揭示克里斯蒂偵探小說外殼之下倫理思考的深度和廣度。
一.突破鄉村空間的倫理想象
在當代空間理論語境中,空間指一種有人參與、與人相關的“多層面、復雜、意向性人化關系”。社會空間理論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和適用性潛能進入文學批評的視野,為研究提供了更多元的角度。
通常認為,偵探小說是源于城市的文學,與城市空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親緣關系。典型代表如柯南·道爾,其福爾摩斯系列是工業文明與殖民主義背景下都市的產物。而阿加莎·克里斯蒂作為“鄉間別墅派”的開創者,即她的兇殺案多發生在一個外表安靜和諧的特定封閉環境中,比如英國某鄉村。涉及到的人物數量有限且關系相對緊密。因此其作品空間結構常被詬病為單一。
一個海上旅行團、一座村莊、一棟公寓、一個退休軍人俱樂部,一個孤島上的別墅……相對封閉的空間,關系有些緊張的中年夫婦、樸實無華卻又愛管閑事的鄉村老太、脾氣暴躁的老將軍、反叛期的年輕紳士和活潑卻又窮困的女家庭教師……就在這群普通的登場人物中間,謀殺發生了。
同時在以波洛為主角的38部作品中,以鄉村為背景的有26部,以飛機、船艙、列車等較為封閉的場所為空間背景的有4部,以旅行異國為背景的有10部(三種背景存在交叉情況)。以馬普爾小姐為主角的14部小說空間都全程或部分設定在英國鄉村中。因此,其作品的空間通常被視為與其他古典偵探小說家相對的另一面,兩者互為城市與鄉村的二元對立而成立。
同時,出身于維多利亞時期中產階級家庭且未受過正規教育的克里斯蒂更是作為“保守的古典偵探小說代表”為批評家所嚴正批判。克式的鄉村設景也被普遍認為是緬懷過去的“英國化”鄉村生活,是一種“大英帝國想象共同體”。
但以城市/鄉村的二元對立觀點作為前提探討克里斯蒂的小說設定背景未免有失偏頗。
回到文學現場,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最顯著的影響就是使英國成為了世界上最早實現城市化的社會。其中資本流動帶來人口的大量遷徙不僅帶來了空間上人口數量直觀的此消彼長,更有兩者物質財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顯著對比。城市已然取代鄉村田園成為大不列顛社會運行的中心。
在都市想象中,鄉村呈現了“一種自然的生活:平和、天真與單純的美德”,而城市則是“一個教養、溝通、光明的中心”。但實際上,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發展,相對于城市而言,農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滿歡樂的故園;同理,城市雖然代表了新的生產方式,但城市并不必然代表進步和安全。簡言之,“城市無法拯救鄉村,鄉村也拯救不了城市”。
城市使人們的生活變得絢麗多姿,也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身份認同與社會感知,激化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城市迷宮般的空間、數量龐大的人群和異化的生活方式,使得這里成為了醞釀犯罪、藏匿蹤跡的溫床。福爾摩斯也稱倫敦為“叢林”和“大污水坑”。可以看到,城市不再是文明進步的中心,而是人人都暴露在犯罪中的危險區域。
與之相對,鄉村的變化相對緩慢,有穩定的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和存續下來的傳統。它的穩定、有序使其成為了人們懷舊和遠離動蕩污染的想象場域。奧登認為鄉村“必須得是個非常美好的地方”。在如此美好的地方“尸體必須不僅因為是尸體而令人震驚,也因為它如此格格不入,就像是客廳的地毯上狗的排泄物”。
表面上來看,克里斯蒂小說的鄉村空間完全契合以上論述。一方面,克里斯蒂小說的背景設定多為封閉且有限的空間,如困在雪中的特快列車、偏僻的小村莊別墅、茫茫大海上的豪華游輪與世隔絕的孤島;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小說里常見的時間表和建筑平面圖也代表了秩序和穩定。在如此封閉穩定的架構下,所有營造的恐懼、不安與懸疑都將在罪犯身份揭曉時隨之解決,犯罪不會破壞原有穩定的社會秩序,最終仍會回歸到和諧的世界。
但深入細讀文本,可以發現其中的矛盾之處,克里斯蒂的鄉村絕非一個單純平靜的真空空間。如克里斯蒂小說中的伯特倫旅館具有充滿舊時代榮耀氣息的裝潢、服務和精神內核。“時光倒流,你再一次置身于愛德華時代的英格蘭。……這里一切都是那么完美。”但最后卻被揭破為“實際上是多年來為人所知的最優秀、最大的犯罪集團之一的總部。”而在另一個被形容為“不合時代的古老地方”的洛塞爾別莊中,一如既往,與周邊人過著熱熱鬧鬧的城市生活不同,別莊中的人和他們老死不相往來,然而在這個平靜的村莊中的卻出現了一具尸體。這并不是偶然,“那個石棺,以及鑰匙在那里,那地方整個的布置情形,當地的人,遠近皆知。任何一個住在附近的人都會想到那是一個藏尸首的好地方。”
以盧梭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肯定人性本善,但會被文明所腐蝕;而未開化的人未被敗壞,如孔子所言:“禮失而求諸野。”因此,美德最后的陣地存留在一些偏遠的鄉村地區。而以挑戰倫理道德為本質的犯罪行為在鄉村卻并未缺席。可以看到,克里斯蒂小說的鄉村作為一個立體的空間,矛盾地包蘊了截然相反的兩副面孔,一副是承襲自英國浪漫主義的阿卡狄亞式的美德樂園,另一副是在表層下洶涌的倫理沖突的煉獄。
而兩副面孔并存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鄉村并非完全抽離都市空間的孤立場域,相反,其密閉的設定環境將所有不同年齡、階級、種族、性別的流動的人,通過情節設置壓縮于這個有限的空間之內,同時也將這些差異帶來的不確定性與混亂的可能性帶入其中;而惡之花在淳樸的鄉野溫室中幾乎毫無存在和繁衍的障礙。另一方面,維多利亞時代的倫理道德觀念并沒有隨著景致而保留下來,工業化帶來的并不只有資本和人口的物質流動,還有道德倫理層面的深刻烙印。鄉村中倫理的混亂和失序程度不亞于甚至更甚于都市,馬普爾小姐就曾洞察過其中的罪惡:
“在鄉下,我認識一個女人,她只是為了要得到一點保險金,便毒死她的三個孩子。還有那個斯坦威老太太,她的女兒死了,接著就是她的兒子,后來她說她自己也中毒了。……后來發現是她自己把毒藥放進去的。……那并不完全是為錢,她妒忌他們比她年輕,而且是活著。她害怕——這話說出來很可怕,但是,這是確實的——她怕他們在她死以后過得很快樂。”
維多利亞時代大英帝國引以為傲的家庭觀念、經濟觀念等等倫理都在文本中被徹底粉碎,這種粉碎造成的是文本中超越空間建構層次的張力和震撼。
二.超越烏托邦空間的實驗倫理場域
縱觀英國歷史,工業革命以來,在帝國衰退與社會危機的陰影中,英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一直試圖進行關于重建倫理秩序的探索。在哈維(David Harvey)、林奇(Kevin Linch)看來,空間具有重要的倫理塑造功能,人創造著空間,空間又塑造著人性。具化到文學層面,浪漫主義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認為鄉村空間存在人性回歸的感召力量:
“不會停止內心交戰
……
直到我們建起雅路撒冷
在英格蘭綠色歡快的土地上”
無獨有偶,與克里斯蒂同時期的英國詩人拉金(Philip Larkin)認為相對于都市生活,鄉村生活離自然更近,是滋養人類感情更為合適的土壤。相對于都市中人,身處鄉間的人們更近淳樸天然,更具有美德。因此他認為,重建倫理的理想方法是回歸鄉村空間。如在其作品《1914》中就明顯表現了對鄉村空間修復婚姻觀等倫理觀念的希望:
繁花盛開的草叢、廣闊的田野、寂靜的小麥地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自得其樂
太陽照在留著小胡子的咧嘴憨笑的古樸面孔上
穿著深色衣服的孩子們在玩耍
男人們留下整潔的花園
成千上萬樁婚姻比現在的延續時間更長
鄉村空間在這里可以被納入西方社會中烏托邦的譜系中加以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否認。但問題在于,一方面,這種觀點忽略了空間作為“人化關系”的屬性,沒有看到建構這種理想生活空間的重要主體條件在于,作為空間建構者與使用者的人要具有理想的倫理素質。這顯然與道德淪喪的現實不符。另一方面,烏托邦往往只能給人以精神上的慰藉,而缺乏落到具體層面的行動性和規劃性。
相較之下,克里斯蒂的空間設景是對英國鄉村文學傳統的反叛,她質疑鄉村作為倫理與美德高地的合理性。她更多從現實條件出發,認識到了當代社會空間與發展倫理問題的復雜性,超越了“空間烏托邦”的局限。具體證據在于她小說空間的粘合性結構。這種空間具有明顯的鄉村物質外殼,而不符合城市空間的論述:
“住在鄉下——一座好大的老房子——有馬,有狗——在雨中散步——木柴生火——果園里有蘋果——沒什么錢——舊蘇格蘭呢衣服——穿上好幾年的夜禮服——沒人照料的花園——秋天到處都是小野菊花……”
同時這里的空間內核充滿不穩定和不確定性,更難以直接對應到鄉村空間的論述:
“在鄉下有一個案子,在麥登漢溫泉附近。只是一個身體很弱、態度和藹的人物,想得到一大筆錢……事情就是那樣開始的,但是結果出了三個命案。”
這種粘合性結構背后的設計理念類似于希區柯克的麥格芬效應,“她本身是空泛的,圍繞著她卻形成了一張罪惡網絡。”平靜的鄉村外殼和洶涌的都市內核都是敘事背景和技巧,真正的主角是犯罪背后的倫理沖突。
三.空間與倫理的互動關系
英國文學傳統中,都市如柯南道爾筆下的“大污水坑”倫敦是天然的倫理角斗場,充滿混亂和危險,而鄉村卻是平靜美好的象征,甚至是都市一系列倫理問題的救贖所在。克里斯蒂打破了這種二元對立的設定,使犯罪被置于一種田園詩的氛圍中。她將鄉村作為小說空間外殼,暴力性隱藏于背景;將都市作為小說空間內核,使倫理的核心問題顯露了出來;她吸收并延續了社會現實的模糊性和復雜性,拒絕了對于鄉村的固定想象,超越了烏托邦的倫理想象,而將筆觸探向了更深的領域。在此空間中,克里斯蒂對犯罪行為進行了重新排布,將文本人物和讀者對于空間和倫理的確定感和安全感全部剝離,強化了混亂與不安的表達效果,突破了倫理問題書寫的傳統模式。
以波洛的《帷幕》(curtain)與福爾摩斯的《最后一案》(The Final Problem)為對照,兩個文本主要情節基本一致,即偵探選擇親自動手制裁法律無法制裁的罪犯。但兩個文本設定的空間背景存在極大不同,并由此折射出了不同的倫理觀念層次。
福爾摩斯葬身的萊辛巴赫瀑布是一個壯闊而險惡的地方,當代最危險的罪犯和最杰出的護法衛士將永遠葬身在那旋渦激蕩、泡沫沸騰的無底深淵中。這個空間設景以其壯闊險峻的外在形態賦予了福爾摩斯的死亡以古希臘羅馬式的神圣、崇高色彩。
同時,這個有限的容納人的格局是對封閉式空間的回歸,對應著法理沖突的之下小說烏托邦式的結局。在一系列都市或其他同構復雜空間中激烈的正邪對決之后,福爾摩斯已經近乎肅清了倫敦中的邪惡,而與莫里亞蒂的對決是這個烏托邦建立的最后一個舉措。
“如果我能為社會除掉他這個敗類……我就會覺得我本人的事業也達到了頂峰,然后我就準備換一種比較安靜的生活了。……且能集中精力從事我的化學研究。”
“如果我想到象莫里亞蒂教授這樣的人還在倫敦街頭橫行無忌,那我是不能安心的……”
作者的倫理觀念在這里表露無遺,“我永遠把福爾摩斯看作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人,最明智的人。”福爾摩斯對莫里亞蒂的私刑是法律的補充,毫無爭議地代表了社會大多數的正義。自此,社會的害群之馬被清除,社會回歸了正義與美德的烏托邦。
從之前的論述可知,克里斯蒂的小說空間是一種絕佳的日常性倫理實驗場所。斯泰爾斯莊園的設定凝聚了作者極大的心血。它作為波洛第一次出場的地方,既是開始,也是結束。一開始的斯泰爾斯莊園是難民波洛和傷員黑斯廷斯上尉相遇的場所,遠離戰爭,顯得十分寧靜。
“斯泰爾斯莊園則坐落在小站的另一方向,離它有一英里地。這是七月初一個寧靜、暖和的日子。……如此寧靜,簡直使人不能相信,就在離這不很遠的地方,一場大戰正在按預定的過程進行。我感到自己已突然置身于另一個世界。”
在經歷了跨度數十年的時空變遷后,相對于《斯泰爾斯莊園》中能夠用平面圖概括的有限空間,克里斯蒂將其改編為更加復雜的空間層次。
“當我走在走廊上,從開著門的房間,可以看到把古式的大寢室隔開的好幾個小房間。”
“房間里面擺設了便宜貨的現代化家具,看到這些家具,使我感到索然無味。要是我,我會選些和房子的建筑形式調和的東西。”
古老莊園被改造為高級現代旅館,處處顯示出過去與現代、觀念與現實的斷裂,其中的餐廳、庭院、私人房間、可供偷窺的鑰匙孔、甚至“帷幕”(curtain)這個象征空間阻斷切割的復雜意象,從私密空間發展到到公共空間,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現正義與法律的沖突,揭示了波洛在其中所面臨的復雜倫理困境。
面對可以為法律懲處的罪惡,波洛可以毫不猶豫地進行制裁,但面對法律之外的犯人,波洛是否有作為法律補充的立場而施加懲罰?《最后一案》中的這種倫理困境被簡化為了懸崖上的一場兩人間的私人決斗,即一種線性的矛盾。而《帷幕》卻結合了現實社會中倫理問題的復雜性,將這種矛盾進行了深化。文本空間中,同時存在且活動的有波洛、諾頓(即犯人X)、黑斯廷斯、茱蒂絲、富蘭克林等人物,波洛除了懲治罪犯,同時還承擔著挖掘、梳理以及緩和這些人物錯綜復雜的倫理關系的功能,而兩者本質上都是對倫理混亂的糾偏行為。諾頓利用復雜的空間場景,把黑斯廷斯推過墻角,通過視覺的錯位使他誤以為女兒茱蒂絲和紈绔子弟阿勒頓存在不正當的關系。而波洛也從鎖孔往洗澡間里偷看黑斯廷斯的反常行為,通過下安眠藥來制止他將諾頓所蠱惑之下產生的殺人意圖付諸行動。復雜的空間中,曲折的人物關系下,偵探不再藥到病除,而是在一團亂麻的現實難題下進退維谷。
參考文獻
[1]盧冶,傳奇與日常的辯證法:“黃金時期”偵探小說與現代性,《長江學術》,2013年出版
[2][美] Williams·Raymon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P, 1973. P23
[3][美] Williams·Raymon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P, 1973. P34
[4][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伯特倫旅館之謎.徐炳雄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5][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伯特倫旅館之謎.徐炳雄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6][英]阿加莎·克里斯蒂.命案目睹記.陳巧媚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7][英]Purkis ·John,. A Preface to Wordsworth.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8][英]阿加莎·克里斯蒂,命案目睹記,陳巧媚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9][英]大衛·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0][美]凱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11][美]凱文·林奇:城市形態,林慶怡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12][英]阿加莎·克里斯蒂,陽光下的罪惡,劉月榮、李玉杰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13][英]阿加莎·克里斯蒂,命案目睹記,陳巧媚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14][英]阿加莎·克里斯蒂,陽光下的罪惡,劉月榮、李玉杰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15][英]阿瑟·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全集》;丁鐘華譯,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
[16][英]阿瑟·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全集》;丁鐘華譯,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
[17][英]阿加莎·克里斯蒂,帷幕,王朝輝,鞏玉芹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18][英]阿加莎·克里斯蒂,帷幕,王朝輝,鞏玉芹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介紹:羅君藝,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試驗班2015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