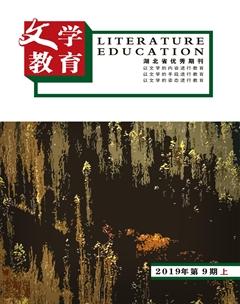論情節與線索理論于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應用
內容摘要:情節與線索作為文學批評理論體系中重要的理論方法,歷來頗受關注,據此對文學作品進行分析的不在少數。本文將據上述兩種理論對中國古代小說中的典型作品——《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下面簡稱《珍珠衫》)進行分析,探討情節與線索理論于分析中國古代小說中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情節 線索 珍珠衫 中國古代小說
文學理論的建立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充滿矛盾的過程,直到今天,很多理論都無法以一種客觀而明確的姿態出現,其中包括今天將要討論的“情節”與“線索”理論。現以中國古代小說中典型作品——《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為例,探討情節與線索理論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 一.“情節”與“線索”的定義
? 1.情節
“情節”的定義最早出現在亞里士多德《詩學》中,亞里士多德認為“情節”是“對行動的摹仿”,“這些(指行動)應出自情節本身的構合,如此方能表明它們是前事的必然或可然的結果。這些事件與那些事件之間的關系,是前因后果,還是僅為此先彼后,大有區別。”亞里士多德顯然已經注意到了“復雜行動”之間的“因果”和“時間先后”兩種關系,但他未將這兩種關系與區分“情節”與“故事”聯系起來。20世紀20年代,英國作家福斯特在文藝理論專著《小說面面觀》中專列“情節”一章。他認為“情節是事件的敘述”,且“重點在因果關系上”;而“故事是按時間順序安排的時間的敘述。”顯然,福斯特的“情節觀”是在亞里士多德“情節觀”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二者的區別在于亞里士多德對“情節”的認識是圍繞西方“敘事詩”這一文體展開的,其定義也存在為“詩學”服務的因素,而福斯特對“情節”的定義則圍繞“小說”這一敘事文體展開,力求將“情節”與眾多相關概念進行區分。
福斯特的“情節”理論目前已為大多數人所認同,在傳入中國后,成為中國文學批評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方法準則。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理論也存在缺陷,即在敘事類文學作品中“因果”的表現以及對“因果”的解讀往往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在中國古代小說的創作中,即表現為“命理”與“巧合”情節的產生。這兩種情節的設置與當時的社會思想文化和作者的價值取向密切相關。某種思想文化導向下創作出的文學作品,在文學作品中會有所反映。同樣的“因”在不同思想觀念的影響下可能會創作出不同的“果”,那么就會產生不同的情節。從讀者的角度來看,同樣的情節,不同的讀者因思想觀念與價值判斷的不同也對“因果”有不同的解讀。下面我們將要分析的《珍珠衫》也存在這些問題。
? 2.線索
與“情節”理論相比,“線索”理論的研究可謂“門庭冷落”,在眾多文學批評理論中,舉凡提及“線索”這一術語,幾乎都是對具體文學作品線索的分析。尋其定義,則多出現在寫作類著述中,且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這一理論看起來似十分簡單,但在具體作品分析的過程中,仍存在許多問題。
首先,“線索”究竟該如何定義。目前在各寫作指導類著述中,使用較多的概念是:貫穿在整個敘事性文學作品(如小說、戲劇、電影)的情節發展中的脈絡。它把顯示人物性格發展的各個事件聯系成為一個整體。這個說法抓住了線索與情節的關系,看到了線索對人物、事件的推動作用。但問題在于,“線索”在所有文學作品中是否都具有貫穿全文的特征呢?對于多事件敘事類作品,其中每個事件的線索看起來各不相同,此時又該如何解釋?
關于“線索”第二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便是線索的分類。通常認為小說的線索可分為以下幾類:以“人”為線索;以“物”為線索;以“中心事件”為線索;以“主題”為線索;以“情感”為線索。這里的分類標準是什么?其次,這個分類涵蓋范圍是否完整?像《紅樓夢》這樣的作品究竟該劃分到哪類中呢?是將描寫賈府由盛而衰的過程視為線索,還是將封建衛道者與叛逆者的矛盾以及寶黛叛逆性格的發展視作線索,亦或是將寶黛愛情悲劇作為線索呢?
有人提出線索的劃分與對作品主題的解讀有很大關系,這種看法雖有一定的道理,但終究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且沒有把線索與主題之間的關系說清楚。因此,解決這類問題的關鍵還是要把線索的具體定義、所涵蓋的范圍以及判定準則弄清楚。下面我們將要分析的《珍珠衫》便是其中一列,線索看似明確,在分析過程中卻有許多不能解釋之處。
? 二.《珍珠衫》的情節與線索
《珍珠衫》是明代馮夢龍精心編纂的短篇擬話本小說集《喻世明言》中的首篇,講述了蔣興哥與王三巧、陳大郎與平氏這兩對夫妻之間復雜錯綜的關系,以及由此引發的“珍珠衫”多次易主的故事。這篇小說篇幅不長,線索看似簡單,但情節卻一波三折。
? (一)情節
1.因果報應式情節
情節的進展與事件的發生往往與人物密切相關,人物作為小說的核心要素,其行動的前后關系,便即情節的展現。《珍珠衫》中每個人物的命運,無不帶著“因果報應”的意味。在小說中“善因善果”的人物以主人公蔣興哥為主,輔之以陳大郎妻子平氏和進士吳杰;“惡因惡果”的人物主要是客商陳大郎;女主人公“王三巧”則善惡兼具,形象較為復雜。
圍繞蔣興哥展開的情節都是在“善因善果”的原則下一步步發展的,其大致發展脈絡可以歸結為:求親被拒——耐心等待——抱得美人——夫妻恩愛——外出經商——因病逾期——識破奸情——怒休妻子——善還嫁妝——巧娶平氏——偶遭牢獄——被救團聚。這些事件環環相扣,每一環既作為前一環的“果”,同時又作為后一環的“因”,層層推進,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蔣興哥的結局其實是建立在他“善良”的品質之上的,他在面對每一個事件時都遵循了善良的本性,做出下一步舉動,哪怕當下看來略有所“失”,但終會在之后給他設置一個“善”的“回報”。
除蔣興哥外,平氏作為陳大郎的原配夫人,在發現丈夫似有異心后,還能放下懷疑,遠去他鄉看望丈夫,替他處理后事,這樣“善良”之人,最后作者也為她設置了一個“善”的結局:改嫁興哥,并成為其正房夫人。而王三巧改嫁之人——進士吳杰毫不介意三巧兒之前的婚姻經歷,愿娶她為妻,始終善待三巧兒,并幫助三巧兒設法救出興哥,在得知二人關系后,還愿成全二人,使他們夫妻相聚,作者同樣為其設置了一個美好的結局:仕途順利,子嗣滿堂。
作為反面人物的“陳大郎”,他的“果”則截然不同。他偶遇王三巧,貪圖美色,找薛婆幫忙,在薛婆的一番苦口婆心和巧計幫助之下,終抱得美人歸。陳大郎雖有帶三巧兒遠走之意,但終究是見不得人之事,只能暫且分開。三巧兒將“珍珠衫”作信物贈與陳大郎,卻因此被蔣興哥發現二人之事。在經商途中又遇到強盜,最終落得人才兩空,客死他鄉。作者為陳大郎設置的這些情節,無不以他貪戀人婦的“惡因”而生,步步將其推向他應得的“惡果”。
小說通過人物的命運展現“因果報應”的思想,并通過情節的設置傳達作者的個人價值取向,帶有很強的主觀性。
2.“巧合”式情節
在《珍珠衫》中,蔣興哥的祖傳珍寶“珍珠衫”對“巧合”情節的出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珍珠衫”主要出現在五處:蔣興哥與三巧兒離別時將“珍珠衫”交于三巧兒保管;三巧兒將“珍珠衫”贈與陳大郎作信物;陳大郎身穿“珍珠衫”巧遇蔣興哥;平氏偷藏“珍珠衫”;蔣興哥娶平氏重會“珍珠衫”。在五個情節中,“珍珠衫”制造了兩個“巧合”,一是陳大郎與蔣興哥偶遇時“珍珠衫”的“外露”致使陳、王二人的私情敗露,二則正是平氏藏“珍珠衫”的舉動才會有后來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巧合”情節不是突然產生的。文章一開頭花費大量篇幅敘述蔣、王二人的結合與恩愛,致使讀者讀到蔣興哥離家將“珍珠衫”留給王三巧保管時,并未有任何質疑;當王三巧將“珍珠衫”贈與陳大郎時,讀者明白,“珍珠衫”的“易主”則暗示人的“易心”;但接下來,陳大郎與蔣興哥偶遇時“珍珠衫”的外露導致二人私情敗露,則完全顯示出作者在此情節中賦予“珍珠衫”的作用。“珍珠衫”第二次發揮制造巧合情節的作用表現在陳大郎妻子平氏察覺丈夫變心后“藏衣”的舉動與后來平氏改嫁蔣興哥得以“珍珠衫”重新回到蔣興哥手中的結果。這些巧合都與“珍珠衫”脫不開干系。
當然,文中也有與“珍珠衫”關系不大的巧合情節,如陳大郎與蔣興哥的偶遇,平氏改嫁之人恰巧為蔣興哥,蔣興哥遭遇牢獄之災時審判案件的恰是王三巧改嫁之人吳杰。這些情節雖與“珍珠衫”關系不大,卻也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作者通過“巧合”情節的設置,使故事向其所希望的方向發展,以此傳達個人的價值取向,同樣帶有強烈的主觀性。
3.情節的不同解讀
正如我們上面提到的問題,情節設置本身帶有作者的主觀態度,但讀者對情節的解讀并不總能與作者的意圖相一致,也會帶有讀者本身的主觀判斷。《珍珠衫》中較有代表性的情節便是陳大郎與王三巧二人偷定私情而又不得善終的情節。傳統意義上,對此情節的解讀以及作者的本意當是陳大郎“惡有惡報”,但在《<喻世明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之新解》中,作者曹小豐為陳大郎伸冤,作為同樣做出有反禮教行為的王三巧,只因是事件中的被動者,便得到了作者以及讀者的諒解,并將其做法視作符合自然情欲給予寬容,而作為主動者的陳大郎則成了作者和讀者的批判對象,落得命喪黃泉的下場也被認為是“惡有惡報”。曹小豐將這樣的矛盾態度解釋為作者“情教”觀的矛盾。
曹小豐的說法站在現代社會的立場上看是有道理的,作者對王三巧給予了一定的寬容,但也并不是真的對她毫無“懲戒”,在小說的結尾,平氏因早于王三巧嫁給蔣興哥而成為正房太太,而王三巧只能成妾室。這個懲罰雖看起來無傷大雅,但對古代女子來說,怎能不算一種活著的懲罰呢?
當然,在這里,我們不是要討論出孰是孰非,而是通過對此情節的不同解讀,能夠看出,同樣的情節,讀者會因價值判斷標準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這也是文學批評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理論——文學接受的問題。
? (二)線索
《珍珠衫》以中心意象“珍珠衫”的幾次“易主”為據,可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極力鋪陳蔣興哥與王三巧的感情至深,直到二人分別,蔣興哥才放心的將祖傳之物珍珠衫交于妻子保管。“珍珠衫”作為點睛之筆,在第一部分的最后才出現,一是為第一階段故事的平穩發展作一個終結;二是為下文的“波折”埋下伏筆。
第二部分從“珍珠衫”的“易主”到“敗露”再到平氏的“私藏”,“珍珠衫”作為主要線索的重要性逐步顯露出來。王三巧將“珍珠衫”贈與陳大郎,后被蔣興哥發現私情暴露,再到平氏察覺異常“私藏珍珠衫”,情節逐漸走向“失衡”的狀態,這都是隨著“珍珠衫”的“易主”而形成的。
第三部分,故事情節徹底失衡,“珍珠衫”的“暴露”引發了一系列后果。“珍珠衫”從陳、王二人感情的見證物變成了王三巧被休的導火索,既是意義上的轉折又是故事結構形式上完全失衡的一大紐節。前面的層層鋪墊至此達到高潮,“珍珠衫”線索的作用至此完全展露現出來。
第四部分,“珍珠衫”重歸蔣興哥,蔣、王重聚,故事至此又重歸平穩。陳大郎客死他鄉,平氏家破人亡,無奈改嫁蔣興哥,使得“珍珠衫”又重新回到蔣興哥手中,“珍珠衫”的線索意義至此結束。
“珍珠衫”在小說中發揮了極強貫穿力,完全可作為此篇小說的主要線索,但問題在于,在第四部分,“珍珠衫”重回到蔣興哥手中時其線索意義隨之結束,而故事情節卻并未發展完整:三巧兒和吳杰的結局還沒敘述完整。從這里來看,“珍珠衫”雖作為主要線索將故事中的主要情節串聯在一起,但并沒有如“定義”中所敘述的那樣“貫穿全文”。因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線索”的作用在于將故事中主要情節的發展脈絡串聯起來,勾勒出故事的大概輪廓,而并不旨在將故事所有材料從頭到尾的連接起來,于每個細節下都藏有“線索”的身影呢。
? (三)情節與線索的關系
1.情節與線索相互交織
情節作為小說三要素之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與人物、環境、結構等密切相關,同樣,情節與線索也不絕是兩條平行線,而是時有交集的。
在《珍珠上》這篇小說中,情節與線索的交叉點就體現在“人物”上。上述在對此小說“線索”——“珍珠衫”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珍珠衫”的主人經歷了從蔣興哥——王三巧——陳大郎——平氏——蔣興哥這樣一個變化,而這幾度變化,卻巧妙的將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串聯在一起,“珍珠衫”見證了人物之間關系的變化過程,從這一角度來看,線索是人物之間的紐帶。
再從情節與人物的關系來看,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中這樣表示人物與事件的關系:“人物產生事件,事件影響人物,二者結合緊密”,“人物自應發展平穩,但情節需出人意表”。在這篇小說中,蔣興哥與王三巧作為核心人物,一切事件皆從二人開始,而后面發生的種種事件卻也都可能導致二人不同的結局,如我們上述談到的小說第四部分,倘若作者在“珍珠衫”回到蔣興哥手中時戛然而止,兩個核心人物的結局就無法達到最圓滿的境界。
在這篇小說中,情節的發展由人物的行為導致,線索的貫穿同樣在人物手中完成,因此,人物是這篇小說與情節的契合點。
2.線索連接情節,情節推動線索
通過上述對《珍珠衫》情節與線索的分析可以看出,線索將小說的主要情節連接在一起,而情節的發展又推動線索向下一個情節前進。二者的共同作用構成這篇從線索與情節結構兩方面回到“原點”的圓形結構小說。
首先,“珍珠衫”作為線索,在每一部分都發揮了其不同的結構意義,而每一部分都有其主要情節,線索在每一主要情節中的不同意義一方面符合每部分的主旨思想,另一方面,這種變化能夠很好的將每一主要情節連接起來而不顯突兀。
其次,小說情節的發展方向也推動了線索向這一方向邁進,如王三巧的變心這一情節致使了“珍珠衫”被她作為信物贈與陳大郎;陳大郎的異常舉動,致使其妻子平氏的“藏衣”等等。
最后,這篇小說以其完美的結構而脫穎而出,不僅僅表現在傳統意義的文章框架結構上,更表現在情節結構與線索結構上。蔣、王二人從最初的恩愛甜蜜再幾經變故后,最終仍走向團聚;“珍珠衫”在幾經易主后又回到蔣興哥手中。從這方面來看,不得不說作者設計巧妙,構思驚奇。
? 三.小結
通過上述的一系列論述,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中國的文藝理論體系還是外國尤其是西方的文藝理論體系,都不是絕對準確完整的,其中還是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與值得思考的現象。在分析具體文學作品時,對所應用理論的“得失”應當有全面的認識,尤其是理論體系所適用范圍的問題。以中國古代小說來看,雖然現在也劃分出了古代文論這樣一個專業學術領域,但其理論體系并不完整,倘若以現代文藝理論或西方文藝理論來作為依據,又頗多相悖之處。因此,最根本的還是要將文學理論體系逐步完善,使之與文學實踐步伐相一致。
參考文獻
[1]亞里士多德.詩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2]愛·摩·福斯特.廣東:小說面面觀[M].花城出版社,1984.
[3]馮夢龍.三言二拍[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2.
[4]曹小豐.《喻世明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之新解[J].安康學院學報,2012(03)
【作者介紹:王夢琦,喀什大學人文學院2017級研究生(喀什大學與南通大學聯合培養),研究方向:近古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