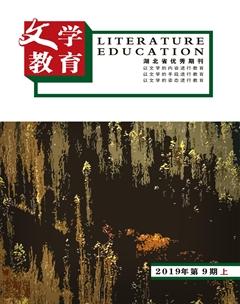從想象到異像:歐洲視覺材料中中國形象的變遷
張艾琪
內容摘要:視覺材料是影像史學研究中的重要途徑。經由視覺材料所傳達的歷史信息,再對這些信息作出分析和解讀,以此來解決圖像中的歷史問題。本文的研究聚焦于中國形象在歐洲視覺材料的變遷。17世紀前,以《馬可·波羅游記》為代表的文學作品,啟發了歐洲對中國的想象,這種想象也通過視覺化的方式影響到當時的藝術創作。隨著大量商人和傳教士到達了中國,以中國為題材的視覺材料被越來越多的帶回歐洲并廣泛傳播,開啟了歐洲本土對中國形象的深化認識和二次創作,影響到繪畫、瓷器、地圖、建筑等多個視覺藝術領域。從圖像的角度研究歐洲如何理解“中國”,不僅拓展了歷史研究的材料、提供了新的視角,還可以深化我們對歐洲與中國交通的認識,以此深化對“他者的眼中的中國形象”的認識。
關鍵詞:視覺材料 中西交通 中國形象
? 一.中國形象在歐洲的形成
中國與歐洲分處亞歐大陸的東西兩端。在歷史上的很長時期內,因為地理上的隔絕,使得二者各自獨立發展起自身的藝術與文化。很長時間內,雙方都不知彼此的存在,而隨著生活在亞歐大陸中部地區的游牧民族,通過遷徙、貿易等方式,或直接或間接的發生了以商品為主的物質交流,這就是歐洲最初了解中國有關信息的途徑。
13世紀后,隨著蒙古帝國的崛起和隨之而來的大范圍擴張與征服,使得亞洲大陸相互閉塞的地區得以貫通。同時,蒙古帝國也打破了原有的貿易格局,使拜占庭和阿拉伯商人所壟斷的東西方貿易得意通過其他方式進行。這就為中國與歐洲雙方的交往打開了通道,也使中西交通間的通暢階段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17世紀前,歐洲對中國的形象認識的主要來源,就是中國出口外銷傳入歐洲的商品,其中最大宗同時也產生了最大影響的就是瓷器。在1514年,威尼斯畫派畫家喬凡尼·貝利尼(Giovanni Bellini)所創作的油畫《諸神之宴》(The Feast of the Gods)中,畫中的諸神便手持有來自中國的青花瓷,這也反映出當時中國瓷器在歐洲所具有的尊崇地位。而就在這幅畫繪成的同一年,葡萄牙的商船通過新航路到達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由此便開啟了近代以來歐洲國家與中國的第一次直接貿易。
可以說,歐洲像一雙眼睛,緊緊盯著東方。這種對中國所處的東方世界的向往以及此前歐洲人所能看到的所有關注中國的符號元素,這些視覺材料一并形成了歐洲早期時代對中國形象的認識和建構。隨著新航路的開辟后,越來越多的商人、傳教士、旅行者、使團直接進入中國,并將中國的物品直接帶回歐洲,讓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可以直接看到中國的形象,讓曾經只存在于幻想中的這個“神州”愈發的貼近與熟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歐洲人也開始根據自身的想象創作有關中國的藝術作品,而這些創作主體很多都是從未來過中國的歐洲教士、畫家、建筑師等群體,他們中的很多人一生之中并未來過中國,卻成為了創作有關中國藝術和形象的視覺材料來源。
? 二.歐洲的“中國”視覺材料創作
前文也提到,中國瓷器在歐洲的影響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隨著十六世紀葡萄牙人開始直接把中國的瓷器販賣回歐洲開始,瓷器的收藏便開始迅速流星于成歐洲上流社會之中。而來自中國瓷器上的各種圖案花紋等符號則構成了歐洲人對中國最初的視覺認知,將其視為這些來自異域的“神秘的符號”。而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隨著中國出口歐洲瓷器的數量達到一個頂峰,此時的歐洲各個主要國家都紛紛在廣州設立商館來進行瓷器貿易。由此,通過這些貿易公司和船隊,這些帶有中國視覺元素的瓷器便被銷往世界各地。
除了瓷器和繪畫外,另一種歐洲人所生產的關于中國的視覺材料便是中國的地圖。近代,最早進行中國地圖創作繪制的是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他在1655年繪制了名為《中國新地圖冊》(Novus Atlas Sinensis)的地圖集,其中共有17張地圖,包括了一張中國總圖、15張中國各省的分省圖,以及一張日本和朝鮮的全圖。值得注意的是,這套地圖冊中并沒有包含當時已經屬于清帝國的滿洲、新疆、西藏和蒙古地區,這也反映出歐洲當時對中國地理范圍的認知。在這套地圖冊繪制的清代初期時,還沒有經過康熙年間系統的大規模測繪,但這幅地圖已經達到了此時制圖技術下很高的制圖水平。
《中國新地圖冊》繪制成后約半個世紀,在康熙皇帝的主導下,當時身在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于1708年到1717年間曾對中國進行了一次較為全面的地圖測繪。這次測繪的結果和行程的地圖成為了一本新的中國地圖集,被稱為《中國、朝鮮及韃靼斯坦的部分地區:最近的部分地區,來自耶穌會傳教士1708-1717年繪制的地圖》。這部地圖集繪成后被送到了巴黎,讓當時著名的地圖制圖師讓·巴蒂斯特·昂維爾(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制圖并重新匯編成一本稱為《全新中國以及中國韃靼和西藏地圖》的地圖集。①昂維爾的這部地圖集成為了歐洲使用時間最長的一部中國地圖集,直到19世紀才被新的地圖所取代。
在沒有照相機等機械復制影像技術的時代,18世紀時的歐洲人傾向于通過繪畫的方式來記錄和表現他們腦海中的中國世界。尤其是在啟蒙運動時期,來自中國的建筑與園林藝術成為歐洲知識界所崇尚和津津樂道的藝術形式。17世紀后到18世紀早期歐洲曾出現過對中國園林和建筑的模仿行為,誕生了一批所謂的“東方建筑”,也形成了一種“貌似圖畫”(picturesque)式的歐洲園林風格。
隨著耶穌會士大量進入中國,通過他們傳遞的往來于中國和歐洲的書信也愈發頻繁,由此產生了一片觀眾中國的土壤,并在歐洲生根發芽。在當時身處中國的利瑪竇,通過他所留下的札記也可以看出此時歐洲人對中國園林的評價。在他的書中,利瑪竇曾經對南京的瞻園進行過描述,提到“花園里一座色彩斑斕未經雕琢的大理石假山,假山里面開鑿了一個供避暑之用的山洞,內中接待室、大廳、臺階、魚池、樹木等一應俱全,洞穴設計得像座迷宮。”在所有的中國建筑中,歐洲人最感興趣的就是亭子和塔,在建筑領域對歐洲影響最大的無疑也是這兩種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