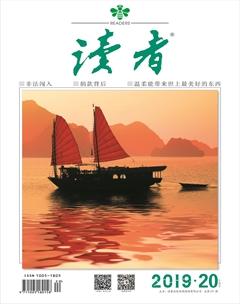福與慧
黃永武

常聽說:“才子短命,才女薄命。”真是天妒奇才?老天讓身懷一把慧劍的,總是以鋒利之刃割傷自己的命運?
乍看世上的例子,你會覺得:有“慧”的人,還真是沒有“福”。有“福”的人,總是那么“庸”,所以叫“庸福”。有“慧”的人,總是那么“清”,一點慧光,像靈氣一般清逸,如何也不肯在“庸福”上常駐。不過細想一下,這也不是什么天命注定,實在和才人的個性有關,悲劇總是個性造成的。
才人總是過分焦躁,不能安分,不肯忍受生命的歷程慢慢展開以成其大。像唐代的鬼才詩人李賀,二十七歲就死去。他是一個急躁、悲觀、容易激動的青年,自負、早熟,擁有智慧與才情,但一遇挫折,就否定現實,對人生絕望。他喊出:“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似枯蘭!”才二十歲就忍不住“不得意”了。“看見秋眉換新綠,二十男兒那刺促!”才二十歲就想象秋容滿面、老態的可怕了。因為急躁、悲觀,所以作詩的時候,恨不能把心都嘔出來才肯罷休;喜歡將生命作孤注一擲,不相信“安靜可以養福”的道理。更不想想,連圣人孔子要到達“從心所欲”的生命境地,也要由“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逐步展開而來。
才人總是過分敏感,不滿現狀,以一種叛道精神來與環境對立。如因科場案被罷黜的唐伯虎,放誕玩世,在葬花于藥欄東畔時大叫痛哭。后來林黛玉也作“葬花詩”,多愁善感的性格,加上鄙視世俗,詛咒功名,執拗古怪而孤立無援,最終成了薄福的人。相比之下,薛寶釵就安分和厚,守拙柔順。其實,“福”就是“備”,“備”就是“百順”,古人說“日順其常,福莫大焉”,但才人都厭惡庸常平順,總想有些驚人之舉,就像用夜明珠來照明,固然“奇”,卻不如電燈燭火的“常”。奇的東西難以長久,所以庸常的福人恒享快樂,而卓異的慧人常抱幽恨。
才人總是過分炫己,盡情宣泄,不把儕輩看在眼里。才人的“驕”如遇到外界的“妒”,驕妒互會,難免成一場禍事。像唐代寫“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的劉希夷,年輕時就中進士,姿容又美,他的舅舅宋之問想把“年年歲歲”這聯妙句據為己有,劉希夷起先答應送給宋之問,后來又到處宣揚這是他的作品,一個驕,一個妒,宋之問就派家奴用土囊把劉希夷壓死。劉希夷死時年未三十。這就如象因牙被擒殺,蚌因珠被割裂,才人以炫露招災。
再則才人常“暴得大名”。對暴得的東西,人們常常不去珍惜,所以不懂惜福。才人又常有“出群”之想,于生命深處自覺有一種無邊荒涼之感,所以常缺少一股慈祥安恬之氣來享“福果”。才人又喜歡恃才任氣,事到得意處,不肯留余以“養福”,言到快意處,不肯留余以“蓄德”,自以為那是真摯激烈,將靈光全發無余,因此總少一些渾樸的元氣來廣種“福田”。所以佛家主張“福慧雙修”,把福配上德,多行“利他”之舉,才可以把“慧光”保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