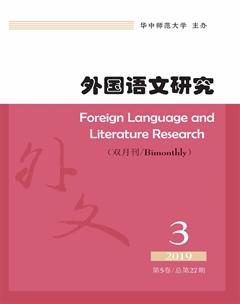戴維·洛奇傳記小說中“作者的回歸”
內容摘要:“作者之死”的實質是否認作品中作者的“在場”,剝奪作者對文本的控制權與解釋權。在傳記小說中,戴維·洛奇以作者身份、批評者身份進入小說文本,以彰顯作者“在場”;洛奇還把與小說主人公“對話”的“前傳記”過程寫入小說,成為小說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洛奇在傳記小說文本中前景化了作者的編輯、寫作、評論等行為,有力回應了現代批評理論對作者權威的否定,從而實現了“作者的回歸”。
關鍵詞:“作者之死”;戴維·洛奇;傳記小說;“作者的回歸”
基金項目:廣東省社科規劃學科共建項目“英國作家戴維·洛奇傳記小說研究(GD18XWW22);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當代英美傳記小說研究”(YB2018055)。
作者簡介:蔡志全,五邑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南京大學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
Title: “The Return of the Author” in David Lodges Biographical Novels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s to deny the authors “presence” in the work, and to deprive the author of the right to control and interpret the text. In the biographical novels, David Lodge enters the novels as the author and critics to highlight the authors presence; Lodge also writes the “prebiographic” process of “dialogue” with the protagonist of the novel into a novel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xt. In his biographical novels, Lodge foregrounds the authors acts of editing, writing, commenting and so on, and responds strongly to the denial of the authors authority by modern critical theories, thus realizing “the return of the author”.
Key Word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David Lodge; biographical novels; the return of the author
Author: Cai Zhiquan, Ph.D.,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Wuyi University (Jiangmen 529020, China). 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czqzsu@126.com
現代以降的諸種“反作者主義”(anti-authorialism)①理論,無論是邊緣化作者還是宣告“作者之死”,其實質是否定作者與作品的關聯,否定作者的原創性,否認作品中作者的“在場”,旨在“終止作者的特權”(Lodge, After Bakhtin 98),解除作者對作品的控制權和解讀權。貝爾西(Catherine Belsey)指出,“作者—文學的絕對主體—之死,意味著文本的解放,從它背后的一個在場的、賦予它意義的權威中獲得自由”(Belsey 134)。不過,以“作者之死”為代表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理論,乍一看似乎宣告了作者的“死亡”,實際上卻再次把“作者”推向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風口浪尖(Bennett 9)。“作者之死”本身就是一個悖論:“當我們談論‘作者之死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要引用巴爾特、福柯、德里達”(周小儀 82)。面對“作者之死”的理論困境與悖論,博克(Seán Burke)給出了解決辦法:重新探索“事實上”的作者,而非“原則上”的作者是克服“作者之死”說抽象和簡單化傾向的有效途徑(Burke, The Death and Return 154)。后來,博克進一步指出,克服這一矛盾的有效途徑是把作者放在具體的社會歷史情景中考察。這正是福柯從考古學向譜系學的轉變,也是新歷史主義、文化唯物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批評家對作者的理解(Burke, Authorship xxvii)。從這個角度而言,以歷史上的著名作家為主人公的傳記小說,是博克所謂的“把作者放在具體的社會歷史情景中考察”的一種重要且有效的方式。
英國文學家兼文學批評家戴維·洛奇(David Lodge, 1935- )對“反作者主義”作者觀頗有微詞。他指出貶低作者、甚至宣告作者“死亡”的觀點大多出自評論家、理論家之口,而非作家之口。他曾以作家的身份為作者辯護:“我要告訴巴特,我的確對我寫作的小說感覺到一種父母般的責任,從某種重要意義上講,這些小說的創作就是我的過去,在創作一部作品的過程中,我的的確確為之思考、受之折磨、為之而生”(Lodge, After Bakhtin 15)。就讀者而言,從作品中尋覓作者或許是人類的一種本能反應。所以,無論是作家還是普通讀者,他們對于作品與作者之間的關聯都保持著興趣與好奇。在傳記小說創作中,作者與讀者不僅實現了“視域融合”,甚至完美地合二為一。因為“(傳記小說的)作者也是讀者,或者說,作者首先也是讀者”(Priest 304)。與普通讀者不同的是,傳記小說家身兼讀者與作者雙重角色,他們會在小說中把閱讀前輩作家傳記和著作時的體驗、思考寫出來,或者說以同行的身份去揣摩、體會。
戴維·洛奇創作了傳記小說《作者,作者》(Author, Author, 2004)與《風流才子》(A Man of Parts, 2011)。在這兩部小說中,洛奇關注反思作者問題,重塑作者身份,回應甚至反駁以“作者之死”為代表的“反作者主義”作者觀。一方面,洛奇以作者為小說主題,從多個層面對作者身份、原創性、作者與作品的關系等問題作出了深刻反思。另一方面,洛奇運用多種小說技巧與表現手法,揭示傳記小說的創作過程,展現作者的“在場”,昭示小說文本中的作者控制(authorial control),指引、提點讀者閱讀。洛奇的兩部傳記小說重溫作者主題,強調凸顯了作者對作品的控制,實現了作者的回歸。
一、 作者作為文學批評者
洛奇的傳記小說以亨利·詹姆斯和H· G·威爾斯等前輩作家為主人公。與其它題材的傳記小說不同,作家傳記小說不僅要再現作家生平,還要評述作家的作品。因此,“戴維·洛奇的虛構藝術或許可以說屬于獨特的一類:他的作品在文學與批評或理論的狹窄邊界之處寫成,因為一種寫作類型使另一種類型被其自身獨特的建構叛道離經的手法和實踐所感染”(Necula 160)。從內容上看,傳記小說“一半是批評,一半是敘事”(Bradbury 487),介于小說與批評之間,是“小說和批評的邊界領域”(Currie 21)。“小說中有不少整段的內容,讀來仿佛是一部侃侃而談地講述十九世紀文學史的手冊中的內容”(Moon 636)。陳榕指出洛奇傳記小說文本具有文學批評特征:“在洛奇鋪陳這些情節時,有時卻會不自覺地流露出批評家的筆法。比如他在小說中引用詹姆斯等人的書信原文時,往往用斜體專門標出,讓人看了不禁莞爾:就差給信加上注釋,標明出處了”(陳榕 111)。陳榕的上述評論,點出了洛奇傳記小說文本的文學評論特征。不過,我們認為文本中“批評家的筆法”并非是洛奇“不自覺地流露”,而是他有意為之的結果,旨在強調小說作者“在場”,在寫作,在評論。
傳記小說從作品中尋覓作家的生平,反推再現作家構思、創作的過程,換言之,傳記小說的創作過程(從作品到生平),可以視為小說中作家主人公創作(從生平到作品)的逆過程,這是文人傳記(小說)獨特之處,體現了文人傳記小說的獨特魅力;與此同時,這個逆過程實際上揭示了小說的“虛構”本質,打破了小說文本的“真實”幻象,也就是說作者在小說中展示創作過程,討論小說的寫法,甚至加入對小說的評論。
洛奇的傳記小說不僅展現小說家的創作過程,還常常會加入對小說的創作、主題、文學價值等問題的研究和評論,這些構成傳記小說文本的重要內容,甚至能夠發揮真正的文學批評作用。在《作者,作者》的結尾,洛奇運用“自我介入”(self-insertion)元小說手法直接進入小說文本,以作者身份評論詹姆斯死后的生活。這部分內容直接使用作者的語言,洛奇以敘述者身份從當下視角評論亨利·詹姆斯:
……就我而言,我在設想這一幕死亡場景時,好像是透過水晶球那透明的弧形表面看到的,也許,亨利·詹姆斯一生最痛苦的事實是,他先是在作家生涯的中期受到羞辱和拒絕,在《居伊·多姆維爾》崩潰時達到低谷,隨即又成功地恢復了自己的創造力和信心,寫出了后期的幾部杰作……(洛奇,《作者,作者》 444-445)
作者介入構成了小說文本的一個元層面(metalayer),通過凸顯“在場”的作者展現小說講述歷史故事的特征。在這個元小說層面,讀者可以清楚地看見作者洛奇在行動:創作、解釋、虛構另一位作者的生平與思想。讀者完全明白這就是戴維·洛奇想要展現的亨利·詹姆斯。在小說框架中,洛奇把自己描繪成一個擁有主動權的作者形象,能夠控制讀者對小說中詹姆斯的理解。這部分內容具有重要意義:連接了作者洛奇與作家詹姆斯。“可是作者的手指還異常堅韌地扣著生命之線不肯放開。不到萬不得已他不會松手”(洛奇,《作者,作者》444),這小段文字彰顯了一位固執且富有魔力的作者形象,他求生的意志堅定,藐視死亡。更重要的是還引入了一個元層面,讓小說作者進入小說文本。敘述者即作者洛奇的話語用斜體文本,旨在與小說的主要文本相區別。同時,這兩部分用省略號鏈接。洛奇悄悄地把自己與亨利·詹姆斯并置。省略號表明盡管詹姆斯已經去世,不過小說并未結束。既然詹姆斯已經無法繼續敘述,洛奇就以講述者的角色介入。在此洛奇描繪的作者有點像魔術師,可以透過“透過水晶球那透明的弧形表面”用魔法召喚過去的一幕幕場景。這段文字通過展現作者在工作為文本找到了作者。
穆拉(Moura Budberg, 1891-1974)是威爾斯一生中真正愛過的三個女人之一。雖然穆拉拒絕與晚年的威爾斯結婚、也不愿意與他同居,不過在洛奇看來,在威爾斯心中,穆拉同樣享有妻子的地位,或者把她當成事實上的妻子。在《風流才子》中洛奇引用了威爾斯寫給穆拉的幾封書信的片段:
甜甜的小穆拉,你告訴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在做。你告訴我不要做的事我都沒做。我還活得好好的,盡管今天下午落下一顆飛彈,顯然是落在遙遠的天邊,因為我沒有聽到它的聲音……我把全部的心和愛都給你,艾吉……(Lodge, A Man of Parts 33)
《風流才子》文本中展現了洛奇對上述三個書信片段進行了文本分析,尋覓字里行間隱含的意義的過程。他繼而給出了自己分析研究的結論:“(威爾斯在信中)反復提到穆拉叮囑他用木板封住窗戶,意在在家務事的安排上,賦予她一種妻子的角色。他害怕孤獨,害怕沒有女性伴侶關心他的健康,這種恐懼一直困擾著他。總有一天會說服穆拉搬到漢諾威排屋來住,他還沒有完全放棄這樣的希望”(Lodge, A Man of Parts 33)。在此,洛奇不僅給出了自己的分析結論,還把原始的參考資料以及分析研究過程展示給讀者,因為“元小說的寫作方式抬舉恭維了讀者,認為讀者與作者在智力上是平等的”(洛奇,《小說的藝術》 247)。洛奇把自己放在與讀者幾乎“平等”的位置,他的身份轉而成為歷史資料的分析者與研究者、小說文本的編輯者,同時邀請讀者積極參與,邀請讀者一同分析、思考史料,引領、提示讀者得出最終的結論。
《海上女王》(The Sea Lady, 1902)是威爾斯創作的一部具有傳奇色彩的小說,“是對水女神烏狄妮(Undine)神話的演繹,有趣地融合了奇幻與現實兩種對立元素,不過主題嚴肅”(Lodge, A Man of Parts 145)。在《風流才子》中,洛奇首先介紹了這部小說的內容梗概:“邦廷一家(the Buntings)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們住在桑蓋特(Sandgate)海濱的一座房子里。有一天,他們發現有一位年輕漂亮的女子在海里艱難地游泳,已經筋疲力盡。他們救她上岸,用毯子把她裹起來,正好也遮住了她的尾巴。她的美麗驚艷眾人,迷住了一個名叫查特里斯(Charteris)的青年……”(145)。洛奇接著講起了小說的創作緣起:“這部小說的靈感來自1900年夏天在桑蓋特海灘的一次經歷”(146)。這年夏天,威爾斯一家帶著梅·尼斯比特②在海灘別墅度假,他們一起到男女共浴的浴場游泳,梅就是小說中水女神的原型。洛奇引用了小說中的一段文字:“不,我想剝下你身上緊繃的泳衣,舔舐你那每一寸嬌嫩的肌膚上流淌的海水,然后在沙灘上立刻瘋狂地跟你一番云雨,就像愛琴海島上的森林之神薩梯(Satyr)和寧芙女神(Nymph)一樣”(147)。洛奇通過這段文字,想象了當時觸發威爾斯寫作這段文字情景:“17歲的梅已經是一位亭亭玉立、豐滿性感的大姑娘了,在晨光的映襯下,身著泳裝的梅向他走來,就像一位年輕的女神。她的泳衣是簡潔的學生款,而且過于短小,緊緊地包裹著她的身體,凹凸有致(147)。在此,洛奇不僅介紹了《海上女王》這部小說的內容梗概、靈感來源,還想象還原了威爾斯當時的創作場景與內心活動,巧妙自然地把小說片段與自己的想象虛構融合,形成新的傳記小說文本。
二、作者作為虛構編輯人
戴維·洛奇在《風流才子》中嘗試運用了虛擬對話/自我采訪(self-interview)的寫作手法。年邁的威爾斯有時會聽見一個聲音并和它對話,這個聲音“清楚地說出他已經忘記或者壓抑起來的事情,有他樂意回憶的事情,有他不愿想起的事情,有他知道別人會在他背后說的事情,還有將來在他死后,人們在傳記、回憶錄、或許甚至是小說里可能會說起的事情”(14-15)。“訪談部分讀起來就像《巴黎評論》對威爾斯的訪談,不過歷史上并未實際發生”(Fay)。這一創新寫作手法成了目前研究評論這部小說的一個熱點。
有些評論肯定了洛奇的創新手法。首先,“自我采訪”豐富了文本表現方式,“(自我采訪)突破了單調的自由間接引語”(Morrison),“自我采訪避免了威爾斯自言自語的沉悶單調”(Siddiqui)。其次,“自我采訪”增強文本的“復調性”,“這個聲音為威爾斯提供了一個就他的書和道德回應批評家的機會……作為一種技巧,這是一次有趣的實驗,非常適用于一個有許多事情要解釋的主人公”(McDowell);“這種手法巧妙,有時顯得尖銳,暴露了威爾斯理想與行動間的一些矛盾”(Doherty)。再次,“自我采訪”具有敘事價值,“自我吐露心聲恰恰是統領小說第一部分內容的重要線索”(FitzHerbert);作者洛奇以自我采訪向威爾斯發問,發問內容變得越來越復雜,最終迫使威爾斯以對位模式拷問自己,質問自己的觀點(Siddiqui)。最后,“自我采訪”賦予作家更多自由,“這種混合形式的好處在于開放了作品的結構,避免文獻資料的阻塞堆積,讓作家自由地直述主題或強調主題”(Mars-Jones)。
另一些評論提出了批評或質疑。有評論質疑“自我采訪”與全書內容的兼容一致性,“洛奇使用的這個聲音介于腹語口技(ventriloquising)與不言而喻之間,這種古怪的寫作手法就很扎眼”(Robson);有評論質疑其文本敘事價值,“敘事價值并不高——這樣的“辯論”不會得出任何結果”(Doherty);還有評論質疑其文學性,“自我采訪手法,即引導他質問自己的過去,可在威爾斯1944-45年間的篇章碎片中找到一些根據;不過洛奇使用的質問方式聽起來就像當代心理輔導課程,或者有時像大學里的討論會”(Parrinder)。
值得指出的是,“自我采訪”具有自反小說特征,暴露了文本的虛構本質:“這個‘聲音對當時尚未撰寫的關于威爾斯的書籍了如指掌——麗貝卡·韋斯特對她們緋聞的說法,安東尼·韋斯特對他母親所謂修訂版的修訂,邁克爾·科倫(Michael Coren)草草撰寫的傳記中,明顯無事實根據的反猶太主義的指控,忠誠的費邊社成員所著的費邊社歷史,等等”(FitzHerbert)。
上述分析評論揭示了洛奇這種文本實驗的一些特色與作用。這部作品中包含了多種相互作用的敘述聲音。首先,有一個全知的敘述者,向讀者提供背景信息,講述威爾斯的生平。其次,對話中威爾斯的聲音,時而辯護,時而講述,時而解釋。第三,對話的另一方“威爾斯頭腦中的”聲音,用黑體字印刷。這個聲音與威爾斯交談,質疑威爾斯,給他辯解的機會。此外,文中還有用斜體文字印刷的“真實”材料引文片段。這些文本穿插于主要文本之中,虛構的聲音以及“真實”材料片段游離于小說真實之外。用黑體字區分的聲音代表文本的編輯人,他控制敘事方向,強調威爾斯生平中的某些事件與謬見/觀念。在自我采訪文本中,洛奇創造性地引入了另一個敘述聲音,一個虛構的編輯人(a fictional editor)。威爾斯頭腦中的這個聲音通過控制對話話題,討論文本參與主題建構。洛奇借助這個聲音巧妙地引領讀者去了解威爾斯的生平,同時這個聲音還讓威爾斯有機會去解釋相互矛盾的表述。因為整部小說并非以威爾斯的視角展開敘述,讀者只能從對話中獲得威爾斯的一些所思、所感。
基納(John F. Keener)在《傳記與后現代歷史小說》(Biography and the Postmodern Historical Novel, 2001)一書中提到了霍爾姆斯(Richard Holmes)的“前傳記”(prebiographic)(Keener 168)概念。霍爾姆斯把傳記作者與傳主的關系稱為“在二人進入相同的歷史背景、相同的事件軌跡之中時,他們持續不斷的生活對話”(168)。基納指出通常情況下這些內容不宜寫入敘事文本中。本文認為洛奇把“前傳記”階段的內容寫進了《風流才子》的敘事文本。這個潛在聲音持續不斷地回顧威爾斯生平中的事件。在小說中洛奇把傳記家與傳主之間的這種對話關系以訪談的形式呈現出來。傳記家在構思傳記的“前傳記”階段與傳主這樣對話時,他就像編輯人一樣組織建構文本。通過在小說中引入“前傳記”對話,洛奇編輯建構了傳記小說文本。文本中作者行為的前景化是對現代批評理論質疑作者的回應。將書寫經驗作為一種永恒的活動而不是一種文學產品,這是以洛奇為代表的當代傳記小說家向巴特將“作者”還原為“他寫作的過去”的妥協,同時也與創作過程關聯實現超越,仿佛持續寫作是抵制成為其作品的過去的一種有效手段。
在小說文本中,潛在的聲音用黑體字,威爾斯的聲音用常規字體,這樣兩種敘述聲音就涇渭分明了。用這樣的方式呈現文本就構成了訪談文本,黑體字的聲音與小說的主要聲音(威爾斯的聲音)就得以區分了。洛奇曾在《寫作人生》中引述威爾斯的作品來證明這種敘事手法的合理性:
我沒有證據表明威爾斯晚年經常自言自語—但我這么做也并非完全無理由,因為在他的幾本著作里,特別是《挫折分析》(1936),含有類似的對話元素,其中主要人物有爭議的觀點(這顯然是表達了威爾斯自己的看法),受到另一個人物(書中假定為正文的編輯)的質疑。(洛奇,《寫作人生》 229-230)
上述引文可以證明洛奇寫威爾斯有時候會自言自語,好像已經得到了威爾斯的認可。這個聲音具有多種功能:它代表文本的編輯者,一個獲得授權的聲音,可以質問威爾斯的人格;它也是一位評論威爾斯作品與生平的批評家。作為編輯,這個聲音會把“對話”以及隨后敘事引向特定的方向。威爾斯頭腦中的這個聲音讓他可以為自己辯護,也可以為自己辯解。有時候這個聲音同意威爾斯:“確實如此。包括安伯”(Lodge, A Man of Parts 370),以一種毋庸置疑的批判態度評論威爾斯的言辭。有時候這個聲音附和威爾斯同情他人:“或許她并不想讓布蘭科·懷特難堪”(370)。有時這個聲音完全是批評:“嗨,你是咎由自取”(137)。這個聲音偶爾還會生氣,質問:“傻瓜!難道你真的幻想你可以毫無情感后果地和這個女孩私情謎語?”(410)此外,這個聲音有時會被威爾斯打斷。對話的參與人都是平等關系,這是作家之間或者是批評家之間的對話。不過,這些對話不僅僅涉及威爾斯的私人生活,還提出了原創作者問題。這樣,洛奇虛構了編輯人,為威爾斯提供了一個評論自己作品的平臺。
三、作者“在場”與權威
羅蘭·巴特在隨筆集《S/Z》中提出了“可讀的”(readerly)文本與“可寫的”(writerly)文本概念。所謂“可寫文本”就是“可被寫作(被重新寫作)的東西”(152),“可讀文本”是“可以被閱讀但不可以寫作的東西”(152)。巴特認為“可寫文本”“使讀者不再成為消費者,而是成為文本的生產者”(152),“可讀文本”的“讀者陷入一種無所事事,不聞不問和總之是嚴肅的狀況:他不去自己發揮作用,不去充分地接近能指的誘惑力和寫作的快樂,他天生只有接受或拒絕文本的可憐的自由”(152)。具體而言,“可寫性文本,就是無小說的故事性,無詩歌的詩意,無論述的隨筆,無風格的寫作,無產品的生產,無結構的結構化。可是,什么是可讀性文本呢?那便是產品(而非生產),這種文本構成我們文學的龐大整體。”(153)巴特指出進一步區分這種整體需要有一種二級操作,這種新的操作便是解釋(153)。在可讀文本中,作者已經講清楚了作者的隱含意義,作者無須發揮主觀能動性,直接閱讀接受就可以了。在可寫文本中,讀者必須積極主動地去探尋意義,讀者也參與意義的生產。可寫文本暗合了“作者之死”,因為文本的意義取決于讀者而非作者,作者與文本意義無關。而可讀文本的意義早已由作者設定,完全由作者引導、控制。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可讀文本反映了作者的權威和存在,寫作可讀文本宣告了“作者的回歸”。
洛奇用父母與子女關系來比喻作者與作品的關系:出版發表的作品如同成年后離家的孩子,獲得了完全獨立的生命,作者再也無法完全預期或控制。因此在創作過程中,作者通過大量的再閱讀、修改甚至是重寫,盡一切可能讓自己的小說足夠強健,免受批評的影響(Lodge, The Year of Henry James x)。為此,洛奇竭力不給傳記小說文本留下多少解讀的空間。洛奇傳記小說中存在大量“可讀文本”。在這些文本中,讀者按照作者的意圖指引去理解閱讀,只需通過簡單閱讀就可以獲取文本意義。洛奇的小說文本意義清楚明確,雖然有時候小說文本為讀者開放了思考空間,不過洛奇馬上又明確闡釋作者意圖,解讀空間也隨即關閉。
洛奇在兩部傳記小說文本中盡力擠壓意義的解讀空間,使之成為“可讀的”而非“可寫的”文本。在《作者,作者》的開頭,作者近乎為讀者提供了所有可能需要的細節信息,讀者基本不需要調動想象力就可以理解。小說的開頭寫道:
倫敦,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切爾西切因巷卡萊爾公寓的二十一號樓的主臥室里(房產經紀人的措辭再恰當不過了),這位著名的作家已漸漸走向死亡……(洛奇,《作者,作者》 3)
這段文字向讀者介紹了小說的主人公。雖然小說直奔主題,采用了倒敘手法,不過讀者還是可以獲得所有重要信息:主人公的職業、愛好、行蹤、年齡、健康狀況,甚至還有性取向。對此我們可以對比參看科爾姆·托賓( Colm Tóibín, 1955- )的傳記小說《大師》(The Master, 2004)。詹姆斯的性取向問題是《大師》的主題,貫穿建構于整部小說中。洛奇開門見山地點明這個問題,沒有留下任何可想象的神秘空間。甚至連“主臥室”(master bedroom)這個雙關語都用括號作了注解,這樣讀者就不會漏掉誤解了。
在《風流才子》中,洛奇用三頁的篇幅介紹了基本信息。小說開頭第一段開頭一下子就把讀者帶回到1944年那個春天,遠景鏡頭掃過位于英國的漢諾威街(Hanover Terrace)攝政王公園西側的聯排別墅,歷經德軍的多次空襲轟炸,房子已經破敗不堪,無人修整。接著鏡頭由全景轉為近景特寫:
精致的拱廊延伸到建筑物的盡頭,拱廊的表面已剝皮、脫落,是這些房子前門的共用過道。支撐建筑物中心景觀的巨大的多立斯柱的表面也在剝皮、脫落,中心景觀是一組嵌在三角形邊框內的古希臘羅馬人物雕塑,這些人物神態各異……(Lodge, A Man of Parts 3)
洛奇的兩部傳記小說的開頭都采用十分傳統的場景設置,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手法,由一位全知敘述者描述小說的主人公和故事發生的場景。
上文中討論的威爾斯頭腦中的聲音,事實上也提領讀者出入于威爾斯生平故事之中。《風流才子》的部分文本與其說是在解釋主人公生平中的具體事件,不如說是在不同敘事層面討論主人公的生平。解釋性元素植根于緊密交織的故事里的對話中。讀者不需要仔細思考就可以解讀威爾斯的生平。值得注意的是,威爾斯頭腦中的聲音提出的問題或許也正是讀者閱讀時會提出的疑問。通常而言,這個聲音成了讀者的替代人,它會觀察、疑惑、想象。類似情況也出現在《作者,作者》中,洛奇本人曾以作者的身份進入元敘事層面。在這個層面,洛奇相當于一位導游,把讀者帶入他對亨利·詹姆斯的觀念與思考中。他徑直根據自己的想法從外部資料中引用篇章段落,這樣他當場就給出了分析解讀,基本沒有給讀者留下多少建立自己觀點的空間。洛奇在傳記小說文本框架中充分發揮了他作為作者和批評家的角色,關閉了讀者的解讀之門。
在這兩部傳記小說中,作者有意識地引領讀者閱讀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在《作者,作者》對《居伊·多姆維爾》首演夜的描寫中,在寫到詹姆斯在臺上謝幕被喝倒彩時,作者運用多種敘事視角從多角度、多方面給讀者提供了各種信息,可謂面面俱到,讀者可以毫無費力地了解到各方人士的反映。所有這些場面匯聚到一起給出了一個全景解讀,避免了單一視角的主觀片面。在此之前,洛奇警告讀者指出“伊麗莎白·羅賓斯立刻看出其中的危險”(洛奇,《作者,作者》 301)。隨著這一幕場景的發展,愛瑪·杜默里埃作為小說的一個敘事視角人物,向丈夫提出了讀者讀到此處時也可能提出的問題:“齊齊,他們干嘛這么亂喊亂叫的?”(302)佛羅倫絲·貝爾問道:“亞歷山大怎么啦?他干嘛不把亨利拉下去?”(303)在這些人物的對話中,他們會不時地提問,這起到了引導讀者進入敘事的作用,逐漸將讀者引向結局,同時還從不同側面分析這一幕場景。到這一幕結束時,讀者也得到了答案。隨后,詹姆斯再次直接詢問亞歷山大讓他上臺的動機,對此亞歷山大的回答是他沒有預料到觀眾會用這種方式回應(303-304)。關于這個場景有一個關鍵問題,也就是整個故事的中心:詹姆斯為什么沒有得到他所期望的認可?洛奇讓故事中的人物與讀者一起思考發問,確保讀者也能夠明白。更為重要的是,這段文字可以說明在這部小說中,幾乎沒有一個問題被落下沒提問,沒回答。這樣,哪怕是最不愛動腦筋的讀者,也可以明白洛奇的作者意圖了。
四、結語
“作者之死”的實質是要剝奪作者對文本的控制權與解釋權。恢復作者對文本的控制權與解釋權是實現作者“回歸”的關鍵。戴維·洛奇的兩部傳記小說重申、證明了作者對文本的控制權。傳記小說是由傳記、自傳、小說、文學批評等多種文類混雜而成的新興文類,作者控制這些文類以何種方式、何種比例混合,決定文本中真實與虛構的關系,使之達到某種文類平衡。作者控制還展現在小說文本敘事中。文本的自反性敘事,昭示作者的“在場”,昭示作者在控制文本。洛奇在傳記小說中,運用元小說手法“前景化了作者的存在”(Lodge, After Bakhtin 43)。洛奇以作者身份進入小說文本,以此賦予小說文本一個元敘事層面。洛奇還把與小說主人公“對話”的“前傳記”過程寫入小說,成為小說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文本中作者行為的前景化,是對現代批評理論質疑作者的有力回應,也是實現作者“回歸”的有效途徑。
注釋【Notes】
① “反作者主義”反對把與作者相關的知識與文學文本一起作為文學批評研究的對象。Séan Burke在《作者之死與回歸:巴特、福柯及德里達的批評與主體性》(The Death and Return of the Author: Criticism and Subjectivity in Barthes, Foucault and Derrid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一書中駁斥了羅蘭·巴特等三位法國學者的“反作者主義”作者觀。
②供職于《時報》的戲劇批評家尼斯比特(E. F. Nisbet)是威爾斯的好朋友,他有一個私生女叫梅·尼斯比特(May Nisbet)。后來,尼斯比特得了重病,把女兒托付給了威爾斯。威爾斯答應做梅的監護人,因此梅稱威爾斯“伯蒂叔叔”。
參考文獻【Works Cited】
羅蘭·巴特:《羅蘭·巴特隨筆選》。懷宇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Barthes, Roland. A Selection of Roland Barthes Essays. Trans. Huai Yu.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S/Z. Trans. Richard Miller. London: Cape, 1974.
Bennett, Andrew. The Auth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Besley, Catherine. Critical Practice. New York: Methuen & Co. Ltd., 1980.
Bradbury, Malcolm.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3.
Burke, Seán. The Death and Return of the Author: Criticism and Subjectivity in Barthes, Foucault and Derrida.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4.
Authorship: From Plato to the Postmodern: A Reader. Edinburgh: Edinburgh UP, 1992.
陳榕:為亨利·詹姆斯的心靈畫像——讀《大師》與《作者,作者》。《外國文學》1(2007):103-112、128。
[Chen, Rong. “Spiritual Portrait of Henry James: Review of The Master and Author, Author.” Foreign Literature 1 (2007): 103-112, 128.]
Currie, Mark. Metafi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Doherty, Mike. “Book Review: A Man of Parts, by David Lodge.” National Post. July 08, 2011
Fay, Sarah. “Sex and Prophecy.” New Republic. Jan 10, 2012
FitzHerbert, Claudia. “A Man of Parts by David Lodge: review.” The Telegraph. Mar 15, 2011
Keener, John F. Biography and the Postmodern Historical Novel.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1.
Lodge, David. After Bakhtin: Essays on Fiction and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90.
---. The Year of Henry James. London: Harvill Secker, 2006.
戴維·洛奇:《作者,作者》。張沖、張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 Author, Author. Trans. Zhang Chong and Zhang Qio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小說的藝術》。盧麗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The Art of Fiction. Trans. Lu Lia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0.]
A Man of Parts. London: Harvill Secker, 2011.
——:《寫作人生》。金曉宇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
[---. Lives in Writing. Trans. Jin Xiaoyu. Zhengzhou: Henan UP, 2015.]
Mars-Jones, Adam. “A Man of Parts by David Lodge–review.” April 17, 2011
McDowell, Lesley. “A Man of Parts, By David Lodge.” May 14, 2019
Moon, Michael. “Burn Me at the Stake Always.”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4 (2005): 631-642.
Morrison, Black. “David Lodges novel is an intimate portrait of HG Wells.” The Guardian. April 10, 2011
Necula, Lidia M. “David Lodge and the Ficiton of Truth or Textualizing Consciousness Through Fiction.” Interstudia 6 (2010): 159-167.
Parrinder, Patrick. “Review of David Lodges ‘A Man of Parts.” Financial Times. Mar 26, 2011
Priest, Ann-Marie. “The Author is Dead, Long Live the Author.” Life Writing 4 (2007): 303-305.
Robson, Leo. “Review of A Man of Parts: a Novel.” April 27, 2011
Siddiqui, Mohsin. “REVIEW: A Man of Parts by David Lodge.” Dawn. August 8, 2012
周小儀:《從形式回到歷史——20世紀西方文論與學科體制探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Zhou, Xiaoyi. A Return of History: On the Western 20th Century Literary Theories and Discipline System. Beijing: Peking UP, 2010.]
責任編輯: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