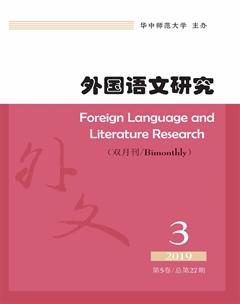葛譯《天堂蒜薹之歌》對中國文學對外傳播的啟示
滕梅 鄭許紅
內容摘要:本文以莫言作品《天堂蒜薹之歌》的英譯為例,以其對外傳播效果為依據,分析其對外傳播主體模式,并探討其對外傳播對中國文學對外傳播的啟示和借鑒。《天堂蒜薹之歌》成功傳播的原因有三:一是莫言日漸上漲的國際聲望促使《天堂蒜薹之歌》得以再版,而其兼具世界性和民族性的作品在拉近與西方讀者距離的同時,也滿足了西方讀者對東方的好奇心,使其獲得讀者青睞。二是國際化的出版平臺拓寬了其傳播渠道,擴大了其受眾范圍。三是文化代理人葛浩文以讀者為中心,歸化翻譯,提高了譯文的可接受度,推動了其在國外的傳播。然而此書的翻譯過程中,刪減、改編的現象屢見不鮮,這種操控手法有時并不利于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由此可見,中國文學對外傳播應優先推介名人名作,積極尋找合適的文化代理人,采用中外譯者合作翻譯的模式,主動開拓國外權威傳播渠道,推動中國文學真正走上世界舞臺。
關鍵詞:《天堂蒜薹之歌》;對外傳播模式;文化代理人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東西方翻譯政策比較研究》(14BYY009)。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this research analyzes its mode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 and explores its enlightenment up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ree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international success of The Garlic Ballads: Firstly, Mo Yans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stature facilitated the publishing of its second version. With both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book not only makes itself familiar to the target reader, but also satisfies their curiosity for China. Secondly, the globalized publishing house expanded it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allowed it to reach to a wider audience. Thirdl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Howard Goldblatt as a culture mediator, increased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translation by focusing more on target readers and applying the strategy of localization. However, omission and adaptation are very common in the target text, which goes agains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ultu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masterpieces of outstanding writers should be exported with priority. At the same time, attention should also be paid to finding proper culture mediators for these masterworks and cultivating more channels for its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The Garlic Ballads; communication mode; cultural agent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廣泛,中國文化“走出去”也已成為一項備受關注的國家戰略。中國文學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其對外傳播也成為了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文學》英文版和法文版創刊時便已開始,之后更有出版“熊貓叢書”、設立“大中華文庫”項目等一系列對外譯介中國文學的有益嘗試。
2012年10月,中國作家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文學一時間成為全球讀者注目的焦點,為其對外傳播創造了一個絕佳的契機,而莫言作品的成功對外傳播也為中國其他文學作品的對外傳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天堂蒜薹之歌》(以下簡稱《天堂》)是莫言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也是吸引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第一部莫言作品。在授予莫言諾貝爾獎時,瑞典皇家科學院常任秘書長彼得·英格倫就推薦《天堂》為品讀莫言的入門書。因此,本文將以《天堂》為例,以其對外傳播效果為依據,分析其傳播模式,探討其傳播過程對中國文學對外傳播的啟示和借鑒。
一、《天堂蒜薹之歌》傳播效果分析
傳播效果是檢驗傳播活動成效的重要尺度。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是文化傳播行為,譯介作品只有到達目標受眾并對其產生影響,傳播行為才有意義。因此,中國文學首先必須通過各種渠道被受眾所接觸,到達目標讀者并對其產生影響,對外傳播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1.1 《天堂蒜薹之歌》的圖書館館藏量及銷售量
采用全球圖書館收藏數據來衡量作品的世界影響力和傳播效果是一個廣泛而可靠的評估標準,“圖書館的館藏對于圖書的文化影響、思想價值的衡量是嚴格的,也是檢驗出版機構知名度、知識生產能力等諸項因素最好的一個標尺”(何明星12)。同時,圖書館也是讀者,尤其是學生讀者接觸文學作品的重要途徑之一。
全球圖書館收藏數據可以從聯機計算機圖書館中心(OCLC)獲得。截至2013年底,已有來自全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3000多個圖書館使用OCLC的服務,其中包括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因此,OCLC被學界普遍用來衡量一部作品在世界的影響范圍。根據筆者2019年2月對OCLC提供的書目數據檢索,《天堂》的作品館藏量約為1634冊,與何明星(13)統計的2012年8月的504冊相比增長了近兩倍。館藏中以葛浩文的英譯本為主,主要分布在英美國家的各級圖書館中。
除圖書館藏書外,圖書的銷售量可以直觀地反映文學作品在目標語讀者中的傳播情況,體現文學作品的傳播效果。據統計,2012年10月之前,《天堂》的海外總銷售量僅為2535冊;2012年10月11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截止到2013年10月,美國拱廊出版社的《天堂》銷售量已達9635冊,僅一年的銷售量便比莫言獲諾貝爾獎前的總銷量多出接近2.5倍(鮑曉英15)。由此可見,莫言獲獎對其作品的對外傳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此以前,對于中國作家來說,“其作品在英語世界的銷量若能超過三千冊已屬不俗”(王侃 166)。以此標準來看,《天堂》的銷量已是相當不俗的業績。
1.2 《天堂蒜薹之歌》的讀者評價
受眾是傳播活動的終點,是傳播效果的最終實現者。書評可以直觀地反映讀者對文學作品的態度以及文學作品對其產生的影響,因此也是衡量文學作品對外傳播效果的一個重要手段。亞馬遜網上書店是世界上銷量最大的書店,知名度高,讀者覆蓋面廣,因而亞馬遜網上書店中對《天堂》的評分及書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西方讀者,尤其是大眾讀者對本書的接受程度及態度。截至2019年2月,亞馬遜網上書店對《天堂》的評分為3.5顆星(滿分為5顆星),其中29%的讀者打滿分,79%的讀者打的分數為三顆星及以上,所有書評中超過64%的讀者給出了正面評價。有不少讀者表示莫言的作品引起了他們對中國的興趣,他的小說是了解中國的一個很好的選擇。然而,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即便是對本書持正面態度的讀者也對中國持不同程度的負面態度,認為中國的革命并未給農民帶來任何益處(JustPlainBill1)。這一印象顯然不利于中國國際形象的建立。
大眾媒體對文學作品的推薦和報道會影響讀者對其的接受情況,因此也是衡量其傳播效果的一個重要途徑。《紐約時報書評周刊》分別于1995年和2012年發表過關于《天堂》的書評,《紐約客》等多部重要雜志也曾推薦過此書。《紐約時報》將其喻為中國鄉村版的《第二十二條軍規》。此外,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從五四到六四: 二十世紀中國的小說和電影》一書中,邁克爾·杜克贊譽此書“是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界描寫中國農村復雜生活的最構思奇絕,藝術風格完備的作品之一”(寧明 53)。
由此可見,《天堂》無論是在西方普通讀者中還是在專業領域都得到了較高評價,也獲得了西方主要媒體的認可。一定程度上,它成功地引起了西方讀者對中國的興趣,基本達到了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目的。
接下來,本文將分析《天堂》對外傳播過程中的傳播主體,即作者、譯者以及出版商,探究他們對作品傳播效果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而探討其對外傳播對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啟示與借鑒。
二、著名作者——世界性話題奠定傳播基礎
莫言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籍作家,其作品已經被翻譯成十六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發行,并先后獲得包括東京電影節“金麒麟獎”、法國“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等在內的多個重要國際獎項。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其作品的銷售量驟增,在海外的出版數量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峰。不少國家都是從2013年才開始翻譯莫言作品,其中包括《天堂》的希臘語譯本。顯然,莫言的獲獎進一步促進了其作品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
2.1中國故事,世界價值
莫言作品兼具世界性與鄉土性,推動其獲得世界文學界的認可。莫言在福克納的啟示下創造了自己獨有的文學領域“高密東北鄉”,并在作品中借鑒了著名作家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天堂》中的魔幻現實主義體現于其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從多個視角以多次重復的順序講述整個故事,同時穿插以動物形象和象征主義手法,虛實變幻。此外,傳統文化、人性的怪異、歷史的異化等一系列國際文學界最熱門的主題在莫言作品中都能夠找到。西方化的敘事技巧與西方文學界的熱門話題相結合,必然更易引起西方讀者的共鳴。這使得莫言作品對西方讀者的吸引力大為增加,奠定了其對外傳播的基礎。
誠然,莫言深受西方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然而他也一直致力于將中國的文化特色融入到作品當中,尋找自己個人的、本土的、民族的小說語言和小說風格。“在《天堂》中,他將傳統的說書以‘鑲嵌文本的形式融入其中,而在《檀香刑》中融入本地說唱藝術‘貓腔的形式、明清小說章回的結構等等,打破了西方傳統的敘事形式,展現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叢新強、孫書文11)。莫言的作品滋養在中國豐厚的傳統文化之中,他在融入世界的過程中,立足于傳統文化的根基,追尋并堅持自己的獨特道路。正因如此,他才贏得了世界的關注。
2.2傳統故事,現代手法
西方讀者在接受中國當代文學時通常有兩種思維定勢:一是求同,尋求與自己的文學相似的東西,尋找熟悉感和認同感,以喚醒他們記憶深處的某些情感。二是求異,尋求一種全新的,與自己的文化完全不同的東西,以尋求東西方文化的互補(姜智芹189)。自改革開放以來,西方讀者對中國的好奇心與日俱增,希望通過閱讀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來了解中國人的生活和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正是這種強烈的“求知欲”使很多中國當代優秀文學作品被翻譯成外文。
作為土生土長的中國故事,《天堂》中使用了大量的山東方言,同時穿插了中國傳統文學形式說唱,描繪了中國的山水風情、傳說神話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內容。這本帶有強烈的地方特色的書很好地滿足了西方讀者的求異心理。
與此同時,雖然《天堂》言說的是中國故事,但是書中體現的傳統文化、地域特色以及對人性的拷問等主題卻是世界文學所關注的話題;小說的呈現形式也頗具現代派風格。在小說的敘述過程中,莫言打亂了傳統的敘事順序,利用插敘、倒敘等手法來敘述高馬、高羊和方四嬸一家的故事。同時,他綜合運用了聯想、回憶、幻覺、夢魘等西方現代派手法,來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使敘事方式錯落有致而又豐富多彩。
由此可見,《天堂》本身無論是從主流詩學的角度,還是從其藝術手法,傳達主題的角度,都符合譯入語國家的審美情趣和要求。而作品中包含的許多與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獨特的語言和敘事形式等,給西方讀者帶來全新的閱讀體驗,滿足他們對東方的好奇心。這一系列特征都有利于《天堂》在西方世界的傳播與接受。
三、文化代理人——漢學大家推動傳播效果
謝天振教授曾指出,中國文學“走出去”目前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誰來譯的問題”(謝天振3)。翻譯不只是一項語言的轉換,更是文化的交流、思想的傳遞。譯者要有跨文化交際的能力,知道譯入語文化需要什么,目標讀者需要什么。有學者指出,中國文化走出去應“借帆出海,順勢而為”,選擇或偶遇合適的文化代理人(焦鵬帥、顏海峰 95-97)。《天堂》的成功譯介也得益于葛浩文這位優秀的文化代理人。
3.1 漢學大家,鼎力推介
葛浩文翻譯過中國二十多位作家近五十余部作品,堪稱漢學大家,其翻譯的作品屢獲國際大獎。作為莫言的諾獎推薦人,他推動莫言的作品進入以西方語言為主的諾貝爾獎評委們的視野,并獲得他們的青睞。正如王寧所言:“如果沒有漢學家葛浩文和陳安娜將莫言的作品譯成英文和瑞典文的話,莫言的獲獎至少會延宕十年左右,或許他一生都有可能與這項崇高的獎項失之交臂” (王寧7)。
此外,葛浩文也在利用自己的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對莫言的作品進行積極的推介。許子東教授稱曾親見葛浩文對莫言的力推,并稱“其強勢態度,十分少見。”著名漢學家顧彬曾指出“無論葛浩文去任何地方,他都公開推廣莫言”,葛浩文“創造了國外的莫言,創造了國外的中國現代文學”(尹維穎 1)。
此時,葛浩文的身份不再局限于一個翻譯作品的譯者,同時也承擔起了莫言作品代理人的角色。他憑借著自己的身份優勢和在目的語文化中的社會地位,向美國的出版機構以及歐美的讀者積極地推介莫言作品,促進了莫言作品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而莫言作品的成功譯介證明,國外漢學家可以同時起到譯者和文化代理人的雙重作用,具有國內譯者無法比擬的優越性。
3.2 歸化策略,讀者為重
文化身份的認同感在文化作品進入異域文化傳播中起著關鍵作用。葛浩文雖在中國生活多年,但他長期扎根于美國本土文化土壤,對于讀者的喜好,市場的需求相比于國內譯者有更深的了解。他明確主張“讀者中心”論,認為譯者“最重要的是對得起讀者,而不是作者”(季進 46)。翻譯時他主張使用“歸化”策略,在相對忠實前提下,根據目的語讀者的文化、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對譯文進行調整。《天堂》便是在這樣的翻譯觀的指導下翻譯的。
通過對比《天堂》的原文與譯文不難發現,譯文中多處與原文不符。在本書第五章的開篇,瞎子張扣唱道“老百姓依賴共產黨,賣不了蒜薹找縣長。”葛浩文的譯文是:“Be brave, fellow townsmen, throw out your chests – if you cant sell your garlic, go see the country administrator.”張扣此話的本意是號召鄉親們相信黨和政府,從側面反映中國政府是值得信賴的。在譯文中,此段卻被翻譯為張扣煽動百姓對抗政府,將不作為的地方政府形象刻畫得深入人心。而百姓們被逼無奈的反抗之舉也被刻畫成一次有目的、有計劃的維權行為。這與原作中描繪的生活備受壓迫而不自知也不反抗的農民形象顯然不符。然而,維護自身權益一直為西方文化所推崇,葛浩文如此翻譯,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讀者的意識形態和審美情趣。
為了追求諷刺效果,《天堂》中包含了許多違背人倫道德、超乎人們接受范圍的情節。葛浩文在處理此類細節時,最常使用的方法便是刪減。如第七章第一節中,可能觸犯譯入語讀者道德觀念的一段關于亂倫的對白在翻譯時全部被刪除。在第八章第三節中,一位乞丐自我作踐、毫無尊嚴地學狗叫來表達對施舍者的感激,因可能會給西方讀者帶來不適,葛浩文在翻譯時選擇省略了這一段帶有侮辱性的文字。
由上可見,為了提高譯作的可讀性,迎合目標讀者的審美情趣和閱讀喜好,亦或是為了順從譯入語語境的道德倫理觀念、意識形態,葛浩文在翻譯《天堂》時進行了有意識的操控,利用刪減、改寫、意譯等以譯入語文化為導向的歸化翻譯策略與方法,使其更易被讀者所接受,促進其在英語世界的傳播。
四、贊助人——權威平臺擴大傳播范圍
勒菲弗爾指出,贊助人是指那些能夠促進或阻礙文學的解讀、創作與重寫的權力載體(Lefevere 16)。對于譯者而言,最直接的贊助人就是出版社,出版社的讀者定位以及實力對譯者以及譯作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影響。無論是哪個國家的讀者,都會青睞那些權威的、自己所熟悉的出版社,進而更愿意選擇和接受由這些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在文學作品對外傳播的過程中,譯入語文化中的本地出版社在知名度和影響力方面有著先天的優勢。《天堂》的成功譯介,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這種先天優勢。
作為《天堂》的出版商,企鵝集團(美國)公司和拱廊出版社均為美國知名出版社。企鵝出版集團(Penguin Group)是世界最著名的英語圖書出版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眾圖書出版商之一,在世界范圍內擁有著廣泛的銷售渠道和讀者群。拱廊出版社善于發掘、出版和推廣世界各國杰出的作家作品,經其推介的新人,如法國作家Andre? Makine等后來大都曾獲過世界文學大獎。莫言是拱廊出版社唯一簽約的中國作家,共有五部作品被出版,其中《天堂》于2006年出版,2012年進行了再版。
企鵝集團(美國)公司和拱廊出版社的盛譽使莫言的作品在面世之前便贏得了讀者的信任。同時,作為本土出版機構,這兩個出版社對于譯入語讀者的喜好把握更為準確,其廣闊的出版渠道和龐大的讀者群體也使作品一經面世便能進入目標讀者群體的視野,對本書的推動作用不言而喻。
出版社對翻譯活動的影響絕不僅限于利用其社會地位來提高譯作的影響力。作為商業出版社,市場與利益是出版社考慮的首要因素,經濟因素決定了一本書是否能夠被翻譯,以及用什么樣的策略進行翻譯。葛浩文曾坦言“很多時候一部作品能不能翻譯,還得看出版社的意思呢,……(讀者閱讀效果)是國外出版商、編輯最關心的問題”(李文靜 59)。為了提高作品的可接受程度和經濟收益,出版社必然會干涉甚至操縱翻譯活動,《天堂》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葛浩文將《天堂》譯稿交給出版社時,國外編輯認為這是一個充滿了憤怒的故事,故事結尾太悲傷,不符合美國讀者口味。在葛浩文的勸說下,莫言專門改寫了故事的結局,葛浩文將其重新翻譯。重譯完成之后,出版社很快出版了這本書,并受到了西方世界讀者的歡迎。更具戲劇性的是,此后中國國內出版的《天堂》中文原作,也采用了經美國出版社要求修改后的結局,而非其原來的結局。
五、《天堂蒜薹之歌》對外傳播的啟示
憑借著國際知名的作者、世界性的話題和優秀的文化代理人,《天堂》成功地在西方世界傳播開來,不僅得到了諾獎評委等專業人士的認可,也獲得了普通讀者的青睞。然而,不得不指出的一點是,在《天堂》的傳播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譯者任意改寫、贊助人恣意操縱等問題,這都不利于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和中國國際形象的建立。
5.1 廣泛傳播,然略有偏頗
從內在因素來看,《天堂》內容兼具國際性和民族性,用現代化手法言說世界性話題,而穿插其中的中國特色文化亦滿足了西方讀者對神秘東方的好奇心,推動了它的成功傳播。從外力因素來看,《天堂》的成功傳播因素有三:一是作者的國際聲望。莫言獲得諾獎,為其本身和作品贏得了世界知名度,將其作品傳播推向了新的高潮。二是文化代理人葛浩文憑借其語言與文化背景優勢,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使譯作能夠為西方讀者接受和認可。同時,他利用自己雄厚的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極力推薦莫言及其作品,推動其對外傳播。三是憑借知名商業出版社在英語世界享有的地位和名聲,《天堂》譯作一問世便獲得了讀者信賴。這無疑促進了其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接受。
盡管《天堂》的對外傳播整體上比較成功,但其對外傳播的模式仍然存在弊端。首先,翻譯項目單純由漢學家發起,這就意味著文本選擇和翻譯策略等均受制于其個人的喜好及研究專長。選材的主觀性會導致選材過于片面,進而導致國外讀者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產生錯誤、甚至是扭曲的印象。
其次,完全由國外漢學家主導文學外譯,還可能會出現對中國文學作品“詮釋不足”或“過度詮釋”的情況。漢學家雖了解中國文化,但不可避免仍然受到本土意識形態的影響,翻譯時難免帶有自身文化的優越感和對“異質文化”的焦慮感,“用洋人的眼光看中國文學作品”(吳倩 151-152)。為了讓西方讀者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他們可能會有意無意地選擇削弱中國文學作品中異質性的東西,從而導致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乃至中國形象出現不同程度的誤釋與誤讀。
《天堂》對外傳播最大的弊端便是贊助人對譯本的操縱。其結局章節的刪改雖獲得了國外讀者的喜愛,卻并不利于中國形象的建立。出版商作為贊助人把控了作者和譯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操縱了譯者和作者的翻譯與寫作行為。因此,要讓中國文學以其本來的面貌真正走出去,就必須解決國外出版商、贊助人為迎合西方讀者口味而任意篡改文學作品的問題。
5.2 中西合璧,歸化推介
中國文學對外傳播是一項系統的浩大工程,不僅涉及到文本的翻譯,還要考慮譯本的傳播和接受的問題。從《天堂》對外傳播的得失中,我們可以獲得以下啟示。
首先在選擇對外譯介的作者方面,應優先選擇獲得過國際大獎,在國際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作品進行推介,利用其在國際上的地位促進其作品在世界的傳播。同時,在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應積極選擇合適的國外文化代理人,利用他們的文化身份和語言優勢,促進中國文化在國外的傳播。此外,為了克服由漢學家本身喜好導致的選材片面和詮釋過度或不足的問題,應選擇中外合作翻譯的模式,即國外漢學家或學者與中國學者優勢互補,合作翻譯。
然而,專注于中國文學翻譯的漢學家少之又少,經濟效益匱乏使許多譯者對翻譯中國文學望而卻步,即使翻譯也要受出版商操縱。因此,要讓中國文學真正的“走出去”,首先要解決優秀譯者匱乏的問題。設立國外翻譯人才培養專項基金及翻譯項目資金,自主培養合格的譯者,吸引國外學者自主翻譯和傳播中國文學是有效的解決方法之一。中方出資,為譯者提供充足的經費保障,提高翻譯中國文學的吸引力,保障譯者翻譯自由,在促進中國文學對外傳播過程中也顯得尤為重要。
對外傳播作品的翻譯策略也是不容忽視的一部分內容。歌德提出翻譯文學進入譯入語文化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譯者語言上采用歸化翻譯,以譯入語讀者熟悉的語言傳達異域的信息;第二階段是譯者努力進入異國情境,根據譯入語傳統改寫原文內容;第三階段是譯者追求譯作與原作完全一致,真正取代原作,達到全譯階段,也就是對原文完全異化翻譯(王輝 63-64)。目前,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仍然處于第一階段,因此在翻譯時應更多考慮普通讀者的審美趣味,用他們喜聞樂見的方式傳達中文作品的思想內容,降低閱讀難度,提高讀者對譯作的認同感。在此階段,歸化翻譯是更好的選擇。以此方法培養出固定的讀者群,讓讀者首先從態度上接受中國文學和文化,然后再逐漸轉變翻譯方法,增加作品中異質性的因素。當然,歸化翻譯并不意味著任意的篡改和刪減,改變的并非是原文的內容和主題,而只是語言的表達方式。
同時,還應加強與國外商業出版社的合作。國外商業出版社,尤其是知名出版社具有傳播渠道廣、覆蓋面大、影響力強等優勢,并且他們比中國出版社更了解譯入語市場,也更受國外讀者的信賴和青睞。因此,加強與國外出版社的合作對中國文學對外傳播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是一項跨語言、跨文化的復雜活動,決定其傳播效果的因素眾多。但是,只要我們不斷地汲取經驗教訓,樹立正確的傳播觀念,選擇恰當的翻譯策略,提高翻譯質量,不斷修正改進傳播方式方法,中國文學就不僅能夠“走出去”,更能夠真正地“走進去”,為世界人民所接受和欣賞。
引用文獻【Works Cited】
鮑曉英:從莫言英譯作品譯介效果看中國文學“走出去”。《中國翻譯》1(2015):13-17。
[Bao, Xiaoying.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a Case Study of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Mo Yans Work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1 (2015): 13-17.]
叢新強、孫書文:莫言研究三十年述評。《東岳論叢》6(2013):8-16。
[Cong, Xinqiang and Sun Shuwen. “Review of Studies on Mo Yan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Dong Yue Tribune 6 (2013): 8-16.]
何明星:莫言作品的世界影響地圖——基于全球圖書館收藏數據的視角。《中國出版》21(2012):12-17。
[He, Mingx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Mo Yans Works — With a View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Data of the World Libraries.” China Publishing Journal 21 (2012): 12-17.]
季進:我譯故我在——葛浩文訪談錄。《當代作家評論》6(2009):45-56。
[Ji, Jin. “I Translate Therefore I am — Interview with Howard Goldblatt.”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6 (2009): 45-56.]
姜智芹:中國當代文學海外接受的解讀偏好。《中國比較文學》3(2015):187-194。
[Jiang, Zhiqin. “The Interpreting Preferenc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Overseas Recep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 (2015): 187-194.]
焦鵬帥、顏海峰:內涵·誤區·路徑——中國文化“走出去”再思考。《山東外語教學》3(2017):92-98。
[Jiao, Pengshuai and Yan Haifeng. “Connotation, Misunderstandings, Paths—O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Out.”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3 (2017): 92-98.]
JustPlainBill. “Review of The Garlic Ballads: A Novel.” May 11, 2017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李文靜:中國文學英譯的合作、協商與文化傳播——漢英翻譯家葛浩文與林麗君訪談錄 。《中國翻譯》1(2012):57-60。
[Li, Wenjing. “The Cooperation, Negoti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 Interview with Howard Goldblatt and Sylvia Li-chun Li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1 (2012): 57-60.]
寧明:莫言海外研究述評。《東岳論叢》6(2012):50-54。
[Ning, Ming. “Review of Overseas Studies on Mo Yan.” Dong Yue Tribune 6 (2012): 50-54.]
王輝:從歌德的翻譯三階段論看歸化、異化之爭。《外國語言文學研究》2(2006):62-67。
[Wang, Hui. “On the Dispute about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Goethes Theory of Three Translation Stages.” Research in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2006): 62-67.]
王侃:中國當代小說在北美的譯介和批評。《文學評論》5(2012):166-170。
[Wang, Kan. “Review of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North America.” Literature Review 5 (2012): 166-170.]
王寧:翻譯與文化的重新定位。《中國翻譯》2(2013):5-11。
[Wang, Ning. “Repositioning of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 (2013): 5-11.]
吳倩:當代西方翻譯文學中的中國鏡像、意識形態及改寫。《浙江社會科學》7(2014):151-155。
[Wu, Qian. “The Image of China, Ideology and Rewriting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7 (2014): 151-155.]
謝天振:“中國文學走出去”:問題與實質。《中國比較文學》1(2014):1-10。
[Xie, Tianzhen.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blems and Essenc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1 (2014): 1-10.]
尹維穎:沒有譯者葛浩文,莫言就不可能獲獎。《晶報》。2013.05.07
[Yin, Weiying. “Without Howard Goldblatt, Mo Yan Wouldnt have Won the Nobel Prize.” Jb.sznews.com. May 7, 2013
責任編輯: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