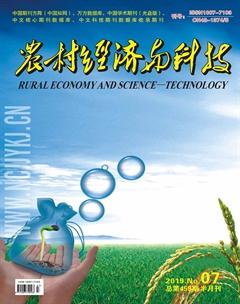論資源性資產在集體產權改革中的折股量化方式
陳長燦
[摘要]目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正在各地陸續推進,不少地方已提出應對資源性資產進行折股量化,但上述資源性資產具體應如何折股量化,中央文件對此并未作規定,在實踐中則眾說紛紜。而不論是從相關法律規定,還是從農地“三權分置”的改革趨勢看,只有選擇以相關土地的“經營權”、而非以土地“所有權”或“承包權”進行折股量化,才是切實可行的路徑,也才能有效保障農地的集體所有權,并維護集體經濟組織新增成員對集體土地的應有受益權,促成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利益關系的平衡。
[關鍵詞]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資源性資產;折股量化;土地經營權
[中圖分類號]F321.32[文獻標識碼]A
1 問題的提出
自從《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中發〔2016〕37號)(以下簡稱“中發37號文”)發布以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正在各地陸續推進。“中發37號文”規定:對于集體的經營性資產,應“推進經營性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上述文件同時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利用“未承包到戶的集體‘四荒地(荒山、荒溝、荒丘、荒灘)、果園、養殖水面等資源”發展現代農業項目。由于集體名下未發包到農戶的資源性資產,其本身即具有作為經營性資產的潛質,且部分村居也已在實際開展經營性的運作。不但已有學者提出資產折股量化的范圍應拓展到資源性資產,在各地改革實踐中,也有不少地方已明確提出應對資源性資產進行折股量化。
但是,上述資源性資產具體應如何折股量化,中央政策文件對此并未作規定,在實踐中則眾說紛紜。部分地方提出應采取面積量化的方式,部分地方則主張以上述資源性資產的收益進行量化,部分地方則對具體量化方式未做明確規定,也由此在實際執行層面引起了某種混亂。也正是由于折股量化方式的不明確,也引起了人們對“集體土地股份化是否會影響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擔憂。在此,筆者擬通過梳理相關法律規定,并結合我國農地“三權分置”改革的背景,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以便理清相關工作思路,明確改革路徑。
2 農地“三權分置”改革與資源性資產的折股量化
2.1 農地“三權分置”改革背景下相關土地權能的可流轉性分析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頒布的《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已明確“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實行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并行”,并提出了“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的要求。依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農地的所有權歸屬于農民集體,其轉讓受到嚴格限制,集體所有的土地只能通過法定程序轉讓給國家。而根據《土地管理法》等相關法律及政策規定,農村集體土地只能由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進行承包,農地的“承包權”系由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專屬享有,也不屬于可以公開流轉的范疇。與此不同的是,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規定,農地的“經營權”則屬于可以公開流轉的范疇。因此,就集體名下未承包到戶的資源性資產而言,其相關土地的“經營權”可依法進行公開流轉,而相關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則均不屬于可以公開流轉的范疇。
2.2 股份經濟合作社的主體性質及其出資要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九十九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取得法人資格。因此,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所成立的股份經濟合作社也依法取得其法人資格。此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規定:法人應當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住所、財產或者經費,且法人以其全部財產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就股份經濟合作社而言,其作為法人而獨立擁有的財產,系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由相關資產折股量化所形成。雖然目前我國尚未出臺專門規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法規,但不論是從《公司法》還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均明確要求作為法人名下資產的出資財產,應屬于依法可以轉讓的財產。此外,從法理層面分析,相關資產在被折股量化為股份經濟合作社的資產后,將被用于承擔股份經濟合作社的各項債務,如相關資產屬于無法依法轉讓的財產,則將難以用以承擔股份經濟合作社的有關債務。
可見,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用以折股量化的資產(即作為股份經濟合作社名下資產的財產),應屬于依法可以轉讓的財產。如前所述,在農地“三權分置”改革背景下,由于相關土地的“經營權”可依法進行公開流轉,而相關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均不屬于可以公開流轉的范疇。因此,在折股量化相關資源性資產時,應以相關土地的“經營權”進行折股量化。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12月新修正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中,將原《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第四十六條改為第五十條,第一款修改為:“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可以直接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實行承包經營,也可以將土地經營權折股分給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后,再實行承包經營或者股份合作經營。”通過上述法律的修改,將原先法律條款中規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在表述上修改為“土地經營權”,不但與農地“三權分置”改革的要求保持了一致,也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以相關資源性資產的土地“經營權”、而非以土地“所有權”或“承包權”進行折股量化,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
3 資源性資產折股量化方式的現實意義與重要影響
對于資源性資產折股量化方式的探討,其意義并不僅在于為相關資產的折股量化提供切實可行的具體操作路徑,上述問題的明確,還將對股份經濟合作社相關債務的承擔、農地集體所有權的保障、有關征地補償款的分配等重大事項產生重要影響。
首先,在相關債務的承擔和農地集體所有權的保障方面。由于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相關資源性資產僅系以其土地“經營權”進行折股量化而形成股份經濟合作社的資產,相關土地的“所有權”并未折股量化,因此,相關土地的“所有權”并不用于清償股份經濟合作社的各類債務,在股份經濟合作社的運營過程中,即使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須以其擁有的全部財產清償外部債務時,相關的集體經濟組織屆時也僅將因此而失去相關土地的“經營權”,而仍然保留相關土地的“所有權”及其直接相關權益(例如:作為土地所有權人對相關經營主體使用農地的情況進行監督、在相關土地被征收時作為土地所有權人獲得相應補償的權利)。
其次,在有關征地補償款的分配方面。一方面,由于土地補償費是國家在征用土地時對土地所有者因喪失土地所有權而進行的補償,根據現有法律規定,其補償的對象是土地所有權人。鑒于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相關資源性資產僅系以其土地“經營權”進行折股量化,而原集體經濟組織仍保留相關土地的“所有權”,故相關土地因征地而獲得的土地補償費仍應歸屬于原集體經濟組織所有,上述土地補償費不納入股份經濟合作社的資產范圍,亦無須用于清償股份經濟合作社的各類債務。另一方面,在集體經濟組織對相關土地補償費進行內部分配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等司法解釋規定,其享受對象范圍為“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因此,上述土地補償費的享受對象范圍與股份經濟合作社的股東范圍,二者也并不必然一致。對于符合上述法定享受對象范圍條件的村民,即使其并未持有股份經濟合作社的股份,也應有權獲得相應的土地補償費,由此也可保障在本次改革基準日之后集體經濟組織的新增成員對集體土地的受益權,有效平衡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利益關系,減少相關矛盾沖突。
4 結語
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以相關資源性資產的土地“經營權”進行折股量化,是在堅持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順應農地“三權分置”的改革趨勢,所采取的切實可行的做法,既保障了農地的集體所有權,也維護了集體經濟組織新增成員對集體土地的應有受益權,實現了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利益關系的相對平衡,將有利于促成改革工作的順利推進。
[參考文獻]
[1]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研究”課題組,“中國農村組織研究”創新工程項目組.溫州市農村產權制度改革: 特點、問題與改革方向[J].經濟研究參考,2014(27):3-10.
[2] 高海.論集體土地股份化與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堅持[J].法律科學,2019(1):169-179.
[3] 田韶華.論集體土地上他項權利在征收補償中的地位及其實現[J].法學,2017(1) :6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