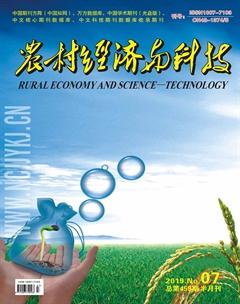失地農民陷入“貧困危機”的可能性調查
張麗美
[摘要]根據對S村失地農民的實地考察和訪談,分析S村農民失地后三年如一日的生活狀態:不思進取、不事生產、坐吃山空、輕視子女教育。可預期,在1~3年內,這些失地農民如果不改變目前的生活狀態,將陷入“貧困危機”。
[關鍵詞]失地農民;青壯勞動力;閑置;貧困危機
[中圖分類號]C915[文獻標識碼]A
時值“精準扶貧”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人們在關注如何幫助貧困人員脫貧時,往往忽略了那些將要步入貧困的群體。在城市化發展中,因國家政策,如土地征收、房屋拆遷后的失地農民在“一夜暴富”后,時隔多年,會不會陷入“貧困危機”?如果會,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的?基于這樣的調研目的,調研組選擇了位于G省省會新區邊界的S村(三年前因修建該市輕軌總站而進行了土地征收和房屋拆遷)為調研對象。
調研組進入村落時,該市“小康XX”工作已經運行了1個多月,政府派駐的工作小組基本上完成了S村村民的摸底調研工作。故課題調研對象除了S村村支兩委、村民外,臨時加入了進駐該村的政府工作小組成員。調查方法是失地考察和訪談,研究方法是定性分析。
1 “一夜暴富”后的“不思進取”埋下了陷入貧困危機的種子
S村在政府征地之前,村民們在完成自家土地的耕種之外,基于地理位置,會在農閑時間從事副業勞動——城鄉載客、運貨、清潔等體力勞動,掙錢以補貼家用。耕種已經解決了家庭飲食問題,甚至剩余農作物因便利的地理位置能非常容易地轉化為貨幣,而農閑進城務工更是增加了村民的家庭收入,使得S村村民比較容易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土地征收后,村民們一次性獲得了一大筆補償款,加上無地可耕,整個村落的勞動力一下子脫離土地,出現了大量青壯勞動力閑置在家的現象,其中90%是男性,持續時間已達3年之久。
經了解村干部得知,以前(土地被征收以前)迫于現金壓力,村民自然會出去找工作掙錢。如今,家里突然有了一筆“巨款”,又不知如何運用,導致這筆巨款閑置,自然顯得很富有,同時他們(村民)認為自己變成了有錢人,對工作的要求高了,自認為自己可以不用從事“下等”(體力勞動)工作了,故閑置在家看孩子做家務,代替了女性平時的工作,而女性無所事事以后,就“開著轎車掃垃圾”無助于家庭經濟建設。據統計,S村98%家庭擁有至少一輛價值在10~15萬元的轎車,女性從事的工作大多是保潔類的低收入工作,月工資在2500~3000元左右,每月車子的消費大概在1500~2000左右,99%的進城務工的女性是開著轎車去上班的。
失地農民出現這樣的生存狀態并不意外。第一,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突然改變導致的不適效應。由半工半農變成無地可依,即使擁有一筆現金,但是本身的素質無法使其產生經濟效益,從而表現得無所適從,同時卻自己給自己貼上了“有錢人”的標簽而不愿意從事失地前能接受的工作,或者本身已經開始輕視這樣的工作而造成閑置在家的生活狀態。
第二,文化習俗的改變通常滯后于制度、政策的改革。中國傳統的小農生活習慣及其小農意識并沒有隨改革開放而被改掉,農民依然有“得過且過”、“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慣性思維,這樣的思維在有土地的情況下,對生存沒有危險,因為進城務工人員失業后,可以回到農村,在有土地的情況下,在現有的社會制度下,基本生存不會有問題,可是失地農民是硬性的被城市化了,他們沒有經歷從農民到市民的社會變遷,沒有經歷農村到城鎮的過渡,直接變成市民,有限的能力和見識限制了他們對未來進行長遠規劃。
第三,國家的福利政策成為了他們“不思進取”的后盾。“新農村建設”以及“精準扶貧”,給占有絕對地理優勢和資源的大城市周邊的農民提供了強大的心理依靠,例如低保及各項扶貧款的幫扶,使得這樣的群體沒有基本生存的后顧之憂。
基于這三點原因,他們才敢如此“不思進取”的長期閑置在家生活著,為即將來臨的“貧困危機”埋下了種子。
2 “不事生產”是步入貧困危機的關鍵原因
Anne-Marie在《The Web of Poverty:Psychosocial Perspectives》中,提到了“Working poor”:因家庭參與工作的人少或幾乎沒有,以靠社會救濟過活的貧困問題。因此,失地農民的城市化轉型,首先應考慮的是他們的就業問題。對此,S村村民及其村干部曾經有過多種探索。
第一,村民自建卡車運輸隊。2015年1月4日G市X網報上有報道,“xx區X鎮S村失地農民自購78輛卡車組成運輸隊”,為啟動輕軌總站運輸渣土。這是一種失地后尋求新的生活來源的積極的探索。時至今日,這種探索失敗了,在村落前面的空地上,實際從事渣土運輸的卡車只有2、3輛,而且運輸渣土的頻率不高。據村干部介紹,S村卡車運輸隊由村民自發組織而成,一開始只有2、3戶人家購買卡車進行渣土運輸,利潤較高,很快回籠了本金并且掙了不少錢,其他村民紛紛效仿,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從而組成運輸隊,試圖通過對外運輸進行業務拓展,但是最終失敗,導致了90%的購買卡車的村民虧本。
第二,金融理財、技能培訓、動員外出務工。為了改變村民“不事生產”的狀態,村委組織金融或投資理財人員入村進行培訓與宣傳,希望村民能把資金運作起來,但是許多村民對銀行投資理財并不信任,故此舉失敗。后,村支兩委組織村民進行技能培訓,參加者寥寥無幾。而動員村民外出務工,到沿海一帶工廠打工,村民們表示離家太遠,工作幸苦(一天10小時以上的工作,無獨立臥室),無保險,表示不愿意外出務工。動員村民拾起“老本行”——做小本生意,如販賣農產品,實際上這項工作在征地之前,許多村民一直從事,唯一不同的是,失地前賣的是自家地里的農產品,失地后,需要去批發市場購買再倒賣。但是村民們以辛苦、勞累、掙不了多少錢為由而放棄,故此補貼家用的老本行也擱淺。鑒于村干部的有限資源及其較窄的知識面和較低的能力,目前,村支兩委對失地村民再就業的動員和教育工作處于停滯狀態。
基于以上就業嘗試失敗的問題,調研組著重調查了村民們對未來就業的意愿,參與訪談的村民不約而同的希望此地修成輕軌總站后,優先安排他們在總站工作,比如打掃衛生、檢票等等。就這個問題調研組著重問了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問:如果輕軌總站對工作人員有學歷要求,比如清潔工也要求高中學歷,你們符合嗎?
答:清潔工還要求學歷,只要會做不就行了。
第二問:如果輕軌總站給你們村工人的名額(畢竟這里有幾個村落)不能平均到戶,只能擇優錄取,而你又是被淘汰的那一個,你怎么辦?
80%的青壯勞動力回答:不知道。
第三問:離輕軌總站修好還有2年,為什么不現在就去求職,慢慢積累經驗,尋求一項適合自己的工作?或者為以后能競聘到輕軌總站上班積累經驗?
答:工資低或臟或累或現在不缺錢。
在訪談中,他們有一個共識,如果他們不能就地(輕軌總站)解決工作,是村支兩委的無能。
因為沒有生存的壓力,這些農民對工作的難度、報酬、硬度都有了更高的定位,但是卻不愿意也不能同時提高自己的能力,如運用補償款去“鍍金”,即參加技能培訓或者繼續教育,或就業累積工作經驗,故而出現了高期望的就業愿望與低素質的就業技能的矛盾,這是造成“不事生產”狀態的關鍵因素。
3 “坐吃山空”是步入貧困危機的主要原因
土地補償款實際上是政府給予失地農民就業、生活、住房的一筆啟動資金。按政府的構想,突然失去土地,農民需要一段時間的緩沖期,那么這筆錢可以支撐這些失地農民在緩沖期的生活和就業轉型。但是農民農民的想法與政府的構想出入太大。
3.1 失地后一切后續生活及設施應該由政府承擔
比如,拆遷后飲用水的問題,村干部在尋找鎮政府的幫助無果后,S村村支書直接去省扶貧辦申請資金,打了井才解決了村民的飲用水問題。而駐地工作小組的看法是,實際上,村委集體用地在被征收后有一筆不小的賠償金,這個資金其實可以抽調一部分進行基本建設的,但是村干部和村民認為這些基礎設施應該由政府出錢,寧肯飲用不健康的水,或到外面去買桶裝水也不愿意或不要求村支兩委劃撥集體資金用來打井,政府財政有規劃,不可能在施工地段進行居民基礎設施建設。類似的事情很多,村民和村干部都認為,應該由政府安排他們今后的生活。
這是典型大政府小社會型問題,村民把一切困難的解決寄希望于政府,而村支兩委也沒有起到組織、動員或引導村民“自治”的作用。他們在享受“自治”權利的同時,沒有自力更生的自覺,不愿意承擔“自治”的義務。
3.2 等待回遷房大大降低了家庭經濟壓力
基于住房問題,政府答應修建回遷房,但是至今沒有動工,所以村民才在不影響施工的情況下自己搭建了房屋暫時居住,這些房屋離輕軌總站施工地不到200m,肉眼可見周圍環境糟糕、房屋質量很差,但卻解決了他們的住房問題。失地農民則將補償款存入銀行,用于日常生活所需。這樣沒有購置住房的經濟壓力,導致“坐吃山空”的狀態在S村非常普遍。
S村有幾戶村民把征地賠償款用于購置新房,然后積極地就業,現已入駐城區。這幾家的婦女基本上從事清潔、洗碗等工作,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工資,男性從事工地建筑或運輸(與土地征收前相類似的工作),所掙的錢足夠一家人的生活費用。這些家庭生活壓力比較大,但是他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并且有自己的規劃,積極的參與“城市化”進程,并沒有坐等政府回遷房、坐等賠償款用完后再就業。其他村民見這幾戶入城生活的家庭起早貪黑的工作,覺得太累,不值得,更加不愿意用補償款購置住所。
二者相較,購置商品房后,形成固定資產,對于不善理財的失地農民來說,不會輕易造成大量的經濟損失,陷入“貧困危機”的幾率遠遠小于前者。對于“坐吃山空”的村民,如村干部所估計的那般,再過1年,頂多3年,這些人將陷入赤貧狀態。這種無生活壓力的“坐吃山空”行為將是這個群體步入貧困危機的主要原因。
4 “輕視后代教育”是陷入貧困危機的必然因素
“無文化是貧困的原因之一”。在對三個調研對象(政府駐村工作小組、村支兩委、村民)的訪談中,只有S村村支書談到了失地農民的后代子女的教育問題:
4.1 父母不愿意過多或過早的對教育進行投資
在村子里隨處可見3到6歲的孩子滿地跑。針對這個問題,村支書的說法是:土地被征收前在村子里就有幼兒園,由于父母都要勞作或進城務工,孩子放在家中無人看管,加上費用較低,村民們愿意送孩子進幼兒園。自從三年前該幼兒園被拆遷后,大部分村民就把孩子留在家里,原因是:①覺得城中離家近的私立幼兒園費用較高,而片區管轄的公立幼兒園即鎮上的幼兒園離家太遠,環境又不好(實際上比征地前村落里的幼兒園要好很多);②認為幼兒園學不了什么東西;③大部分男性青壯勞力無所事事,剛好可以帶孩子。基于以上三個原因,S村6歲以下的孩童基本上在家呆著。
4.2 父母自覺不自覺的放棄青少年的教育
調研期間,可見14、15歲左右的青少年在學習時間騎著摩托車不定時的進出村子。針對這種現象,村支書認為是校方和家長對其監管不力造成的。由于家中幾乎是“一夜暴富”,這種暴發戶式的膨脹心理同樣影響了這群孩子。家長樂意帶著補償的心情滿足這群孩子的各種要求:買摩托車,給過多零花錢等。調查組就孩子不上學的現象,抽取了一部分家長進行訪談,這些家長對孩子不上學、到處游玩的現象并無憂慮,同時表示自己文化層次低,無力輔導孩子學業。而村支書認為,家長不負責任,誤其子弟,村支兩委多次開會要求他們送孩子入學,嚴加管教無果,對孩子們的前途表示擔憂,認為這些孩子在父母的示范作用下(懶惰、閑置在家、不積極就業)會成為“貧二代”、“貧三代”,將為社會治安埋下不良的因素。
4.3 中國目前艱難的就業狀況也是失地農民輕視或忽略子女教育的原因之一
S村有幾戶家庭培養出了大學生,調研組設計了村民對這些家庭為孩子投資教育的看法。村民的回答大致分為三種。
第一,不是每個人都能考上大學,我家的孩子不是學習的料,我們也輔導不了孩子的學業,他們混完初中就可以了。
第二,大學生又如何,還不是在替他人打工,工資有時還不如我們修房子(臨工)高。
第三,現在滿街的大學生不都在找工作嗎(待業之中)?
就業體制改革至今,仍然無法完全改變農民對通過高等教育改變家庭經濟狀況或孩子自身命運的傳統觀念,加上高等教育的成本增加、“大學生畢業就失業”的現象比比皆是,使農民不愿意將有限的資金過多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他們的綜合素質看不到高等教育或技能教育對孩子擁有基本的生存技能的重要性,也無法估計到接受過高等教育或技能教育的孩子在通過后期工作經驗的積累和實踐后的晉升空間、享受城市資源的優勢,故而出現了輕視子女教育的狀況。在現代化社會,沒有生產資料(知識、技能)的儲備,使失地農民家庭無法擁有城市化進程中的后繼資源,這個群體必然會步入貧困危機。
5 結束語
S村村民目前的生活狀況不可能受到扶貧辦、社會扶貧組織的關注,因為目前按國家對貧困戶的定義,他們并不是貧困群體,如果這樣的生活狀況在1~3年內沒有得到改變,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樣,他們有極高的幾率陷入貧困危機。
[參考文獻]
[1] Anne-Marie Ambery,The Web of Poverty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s,M the Haworth Press,1998.
[2] Gladwin,Thomas,Poverty,U.S.A.The historical record,M.Little,Brown.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