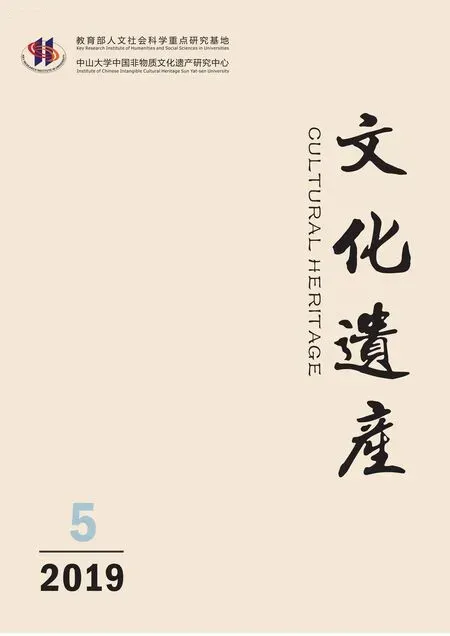規矩、示能和氛圍:民居建筑遺產塑造社會的三個機制*
李 耕
物質空間與人文世界:一個分析框架的提出
建筑空間在社會科學里頻繁承擔的角色是“載體”,是體現了文化關系或社會結構的“容器”。問題在于,人們最常關心的是容器里的內容,而不是容器本身。所以說出現了“對物的遺忘”,或說“物的遺落”——基于建筑社會性的話語與權力分析占據主流,空間的“物質性”(materiality)隱身了。研究者傾向于利用物質性去佐證一些已成定論的認知/意義體系,例如有等級的空間布局體現了宗法制度。同時,出于對過度關注話語、語言、隱喻的后現代理論思潮的一種校正,社會科學近二十年里發生了空間轉向、地志學轉向、物質轉向和本體論轉向等。在這一系列轉向之下,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更多的關注建筑空間的議題,正視物質性和物質在深層次上的能動作用,即不但看到“容器”里的內容,也要看到“容器”本身,以及容器對內容的塑造。換言之,需要讓和物質性有關的經驗事實“進駐”到認知框架中來,以求實現一些社會科學前沿研究所倡導的“本體論”層面上的突破。
臺灣人類學者黃應貴在研究空間問題時,曾提出設問:“空間是否有自己的邏輯?”解答這個問題,他認為有兩種思路,一種認為空間是有普遍結構的獨立存在。他認為這樣極端的態度無法理清空間與其他要素的先驗與優先性關系,又容易忽略主體實踐,違背了空間本來就是人為活動不斷建構的事實。黃應貴還列出了另外一種更廣為接受的觀點,空間具有不可孤立性。空間是行動的媒介與結果,也是行動、思考、生產、控制等的工具,更是思考模式的框架。(1)黃應貴:《空間、力與社會》, 《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筆者認為,強調空間與其他要素的聯系,是合乎社會科學的基本出發點的。但是該思路很容易讓空間被溶解、包容于其他要素的研究里,例如社群等級、宇宙觀、文化分類等等。黃應貴自己也指出,人們太習慣于在物質性空間的基礎上去建構其他性質的空間,太容易將物質空間的研究“化約”為社會文化的研究。(2)黃應貴:《空間、力與社會》,《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
所以難點在于如何處理物質空間與人文世界的距離,既不能靠的太近,又不能離的太遠。靠的太近前者容易被后者融解,物質性的細節、空間本身的性狀,都被架空。離的太遠則研究的焦點會再次迷失。黃應貴認為除了物質性地理形式或人為建構環境本身具有的塑造力外,更重要的是人與物質活動結合運作而產生的新的空間建構所具有的力量,空間建構也是共同構成空間的本體論基礎與性質。這種相互結合、共同構成的途徑可以是宗教活動,可以是族群關系,也可以是消費等等不一而足。(3)黃應貴:《空間、力與社會》, 《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 2期。但是,新的空間建構似乎再次脫離了空間本身,在人與物的交界點上,天平總是傾向于“人”這一側。或者說,問題在于,如何在人與空間的交互作用中,看到空間的物質性對意義闡釋的作用?物質性(尤其在物理性狀層面)的存在與認知體系,與非物質的、敘事性的、共同意義(集體表征)體系,應該如何恰如其分的兩相結合起來?
英國漢學家、人類學家白馥蘭(Francesca Bray)試圖結合上述兩大體系,她在古代中國的住宅與行為規范之間建立起了關聯性。在布迪厄與福柯等人的影響下,白馥蘭提出“一座房子是一個文化模板,在里面居住可以從中學會那個社會特有的根本性知識、技能和價值。這是一個學習手段,一種能將儀式關系、政治關系、宇宙觀轉化為日常的空間經驗的機制。”(4)[英]白馥蘭:《技術、性別、歷史》,吳秀杰、白嵐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3頁。她強調在將日常行為納入道德范式方面,物品與環境擔當的角色,雖悄無聲息卻強大有力。白馥蘭指出,作為社會-技術體系,住宅圖式對社會的塑造遠超物質層面,也是統治階層和普通家庭的道德框架。房屋的物質設計、居家空間實踐的標準化讓家庭遵循共同的社會秩序,尤其在復制父系家長制的宗族組織上,房屋成為國家所希望看到的那種傳播倫理通則的道具。她的論斷里有一個關鍵的橋接就是“身體”,可惜她沒有挖掘身體訓練方面的史料,或者給出對應性的經驗事實佐證。此外限于研究方法——有選擇性的史料分析,她只是將一些判斷和材料并列,雖然整個敘述合情合理,并沒有明確地為自己的論斷提出非常有實證意義的論據。
另一位在人文與建筑領域影響廣博的建筑理論家皮特·瓊斯(Peter Jones)近年出版了專著《建筑與儀式》ArchitectureandRitual,指出空間秩序反映了社會秩序,亦幫助創造社會秩序,因為建筑通過它們自身的組織邏輯能協助保存社會關系上的記憶。瓊斯簡略地指出,環境提供了行為認知上分類的框架,此外也體現了美學傾向;人們在使用環境過程中,環境傳遞的信息既框定了可能性,又暗示了行為軌跡。(5)Jones Peter B., Architecture and Ritual,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p.2-3.瓊斯的著作介紹了諸多建筑以及相關的文化社會信息和日常生活方式,他在方法上不強調證明某些原理,側重于闡釋意義,即研究者要搜集盡可能多的信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所以他也沒有提供一個現成拿來可用的實證研究方法或可以執行的路徑。
藝術人類學早期曾集中于對土著雕刻、壁畫等“物”的研究,其奠基人之一蓋爾曾經提出,在研究藝術品時需要看到“連貫性之軸”(axis of coherence)。(6)Gell Alfred, Art and Agency :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3).筆者理解這個連貫性之軸不僅在藝術品研究中是重要的,也是更廣泛意義上的,包括建筑研究在內的物質研究值得依循的路線。它之所以重要,在于倡導建立主客體之間的聯結脈絡。而所謂連貫性之軸,在布迪厄經典的空間研究中就有所體現:在研究柏柏爾人的房屋時,他通過對普遍存在于各個范疇的結構等式的歸納,在空間/物、社會、超自然等各個領域之間建立起來貫通的相關性。(7)[法]皮埃爾·布迪厄:《實踐感》,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年,第425-444頁。
沿著這條連貫性之軸,從物質本身出發去理解物質性(materiality)本身以及對人文世界的影響,筆者認為需要在次一級的層級上有明確的方法去說明揭示:以物質形式存在的建成環境一直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人類。在認知行為科學方面,已經有大量的研究從各種角度去測量空間如何影響人類的行為和情緒等。這類研究建立在實驗和測量的基礎上,局限在認知和行為上,并且以個體感知為單位。那么在集體的尺度、歷史的跨度上,空間如何塑造文化?又如何在價值觀上影響人?這或許是人類學社會學能夠貢獻的部分。以往相關的人類學研究雖然有很多,但多數是闡釋型的研究,并沒有提出證明上述事實的具體途徑。為了研究建成環境如何在集體的歷史的層次上,從物質性的角度塑造社會文化,本文為研究方便起見,以約束力為刻度,臨時劃分出三個作為分析單位的層次。首先是空間的規矩。包括明確的空間使用命令/禁令,也包括微觀的權力,例如潛移默化地對身體的規訓;其次是環境給人帶來的可能性,例如提供行為路徑,誘發或壓抑一些傾向。借鑒行為生態以及設計學領域的示能(affordance)概念,這種可能性是,環境提供給動物的東西,并且動物可以憑借自己所拾取到的環境信息進行適當的行動。生物體往往順‘勢’而為,也可以看作一種“勢能”。再次是空間的氛圍,氛圍指向的是切身性的身體經驗,存在意義上的綜合主觀感受。三個領域表面上的強迫性是遞減的,但是,影響深度并不必然伴隨強迫性的遞減而遞減。空間氛圍對人們集體意識的影響并不必然比空間規矩的影響小,哪怕這種影響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綜合來看,如果空間是有力與氣的,那么它的“力氣”體現在規矩與規訓,體現在對人類行為的誘導與限制上,它的“氣力”則體現在對體驗的氛圍浸染上。這三個分領域在群體層面和個人層面都是成立的,而且經常以社會事件的發生為媒介,以歷史變遷過程中的復刻與迭代為自身效果的證明。
遵循上述路徑,本文以福州永泰縣寨堡類民居為例——承托了宗族集體生活經驗的典型民居,來說明空間對社會的形塑作用。2017-2018年間,通過采訪有民居使用體驗的老人,試圖在空間與人的交接面上,融合靜態的空間形態分析(傳統建筑學擅長的領域),物質的意義象征體系(傳統人類學擅長的領域),以及流動的日常生活。
莊寨作為民居建筑遺產
莊寨源自福建福州市永泰縣近年來對本地民居-防御建筑群落的命名。多數莊寨名字叫“某某莊”或“某某寨”,也可同時有莊和寨兩個名字,例如青石寨又稱仁和莊。在福建類似的建筑群落還有土樓和土堡,一些建筑學家也傾向于把永泰的莊寨劃入到土堡。上述各類在全國民居譜系內可以都算作寨堡類民居(或稱堡寨式)。莊寨原先并無統一命名,近年在保護工作中出于差異化地域建筑以突出地方特色的考慮,綜合形成“莊寨”這樣一個稱謂。“莊”強調安居,“寨”強調防御,可見莊寨是防御和居住功能并重的。莊寨體量巨大、數量眾多。根據永泰縣古村落古莊寨保護與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村保辦”)的統計,歷史上莊寨總量估算有2000多座,經過匪患、改革后拆建潮,保存較好的莊寨現存146座,其中占地1000平米以上者98座。(8)永泰縣村保辦:《山水奇構 永泰莊寨》, 2015年(非正式出版物),第238頁。這些規模巨大的民居可以容納幾百人共同居住。
在建筑形制上,莊寨和中原院落式民居形態接近。建筑材料以土、木、石為主。和土樓不同,莊寨以木構架承重,邊墻并非承重墻,只是圍護,人們的生活重心在內圈。外墻圍攏多呈幾何方形及不規則多邊形,從而和梅州圍龍屋固定的形制相異,和江西贛州地區土圍子之無定式也有區別。居住結構較密集,每個房間平均7-12平米大小,以木板或竹籬草泥白灰墻相隔。多數層數為兩層,最高可以到四層。每個房間可能是一家五六口人的休憩之所,隔層放雜物。莊寨最鮮明的建筑特色,在于防御體系設計。防御性墻體、跑馬道、碉式角樓、框制斗窗、注水孔等都是為防御外敵入侵而設置,從而與一般民居區別開來。
莊寨的形成,和匪患、山林經濟、宗族以及地理環境都有關系。明代嘉靖后期,福建沿海地區遭受十年倭寇之亂,搶劫財物,掠奪人口,以至“屠城百里無煙,焚舍窮年煙火”。歷史學家鄭振滿指出,倭寇之亂促使族人筑堡自衛,從而強化了聚居宗族的軍事防衛功能;在筑堡風氣流行的同時,民間自衛武裝也發展起來。鄉族武裝引起鄉族械斗,又激化了當地的社會矛盾。上述多重關聯的因素加劇了修筑莊寨土堡和在防御型建筑中居住的必要性。(9)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71頁。到了清代社會較為安定的時期,軍事防御功能退居次要,生活功能居前。歷史學家楊國禎、陳支平還指出,移民開發的歷史對民居建筑和居住習俗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在閩南閩西的交界之處,有限的自然資源塑造了土樓。而在開發較晚的閩中山區之中,還保存著具有中古氣質的土堡與住宅。(10)楊國禎、陳支平:《明清時代福建的土堡》,臺北:臺北國學文獻館1993年,第1-11頁。同時,寨堡類民居的建筑多數是一個家族(也有多個家族合股的案例)合力建造,一方面反映了宗族勢力膨脹,一方面合族而居的建筑又鞏固了家族的內聚力和家族設施的完善。楊國楨、陳支平進一步提煉說,從根本上說,明中葉以后福建宗族勢力和這個時期土堡的建筑一樣,都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而又缺乏一種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的產物。(11)楊國禎、陳支平:《明清時代福建的土堡》,第25-27頁。
隨著人口增加,人們陸續從莊寨中搬遷出來,尤其改革開放后,莊寨逐漸廢棄,絕大多數莊寨鮮有人居住,很多莊寨年久失修損毀傾塌嚴重,頹敗陰森,孩童甚至不敢踏進莊寨大門。2015年起永泰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莊寨保護,成立“永泰縣傳統村落暨古寨堡保護與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2017年3月更名為“永泰縣古村落古莊寨保護與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永泰縣委縣政府每年安排出2000萬財政資金用于莊寨的搶救性保護。在政府引導下,諸多莊寨動員起來,開展大規模的維修。民間最起初的維修動力,源于莊寨作為祖先的遺產,乃是整個家族的象征,倒塌了即“對不起祖先”。在政府發動的保護修繕階段,各莊寨族人是主體,宗族自行動員籌集資金和人力物力,而政府給予政策和資金扶持,并積極聯系社會第三方力量介入,包括專家、媒體和社會融資渠道等等,從而呈現出政府引導、民間動員的良性互動局面。
空間的規矩
在集體生活的傳統民居里,有許多空間的使用規矩。這些規矩首先是出于安全、衛生等公共利益以及基本倫常而生發出來的規約與規訓。木結構房子首先要處理的安全問題是防火問題。在建筑規制上,莊寨均有封火墻以及防火門。掛瓦墻作為防火墻,由多塊瓦片組合。因為具有視覺上的集陣效應,掛瓦墻已經成為莊寨的建筑符號,應用于當代新式莊寨的改造裝飾。和徽派建筑的馬頭墻一樣,掛瓦墻也從防火墻衍生為民居的象征符號。實用設施演變為審美對象。而不管是莊寨以前的住戶,還是現在的莊寨使用者最常掛記的是防火檢查。在目前已經供人參觀的莊寨中,“嚴禁吸煙”是各處最明顯的告示。這些都是木質地的建材屬性必然帶來的行為規訓。
集體、閉合的空間,對人們的作息安排提出了要求,并延伸出守門人、非正式出入口等策略。當人們還在莊寨居住時,大門到夜間九點會統一由負責關門的人員關閉,這就催生了定期歸巢的行動約束。據一些老人回憶,他們如果玩耍晚了,需要鉆莊寨旁側的牛門回家。在密集居住的空間格局中,還有為了不影響他人作息而設立了日間空間使用規矩。例如,午休時間不能在公共空間吵鬧。位于天井和大廳邊上的房間,因在公共交通線附近,午睡要自覺關門。上述規矩是莊寨生活里人人都要尊重的加諸于身體的規約,每個莊寨成員從小要被老人教育的內容,其形成與緊湊房間布局密切相關。身體規訓也在傳遞著公共生活的規范,培育出相處中照顧別人反應和需求的社會交往處理模式。
莊寨的空間單元雖然密集,同時又有很多公共性的物理空間,例如廳堂。這又會產生公共衛生清潔維護之需要。這類家務勞動主要由女性承擔。據老人回憶,女性在過年時會一起用清水清洗各處墻壁。這里需要特別指出,公共房屋的清潔勞動分配,貫穿了宗族公共事務秉持的原則——以“房”和“家庭”為基本單元的輪值制。即每個房派每年輪流做公共衛生、點燈,當年對應的公田收入歸該房每房內部;各個房內部的每個家庭再按照月份輪值。家族內部輪值的分工合作體系,在解放后大規模解體。解放后公共領域不再有規矩明確的分工合作,只是住大廳附近的人要多做些大廳衛生。在公共空間的衛生這個空間與人的交接點上,清潔作為建構性的實踐,既是宗族按照房支與家庭排布、平均主義的社會運轉邏輯的一個具體體現,也是公共空間對居住者的客觀要求,二者缺一不可,以往的研究路徑可能更傾向于強調前者。此處想強調,是公共空間以及密集排布的比鄰而居的空間格局參與制作了這套運轉體系的存在,單純只有宗族的社會體制,并不能必然得出輪流做公共衛生的具體實踐。
在傳統禮制社會當中,空間呈現總是伴隨著隔離的體制。慣常的解讀是,空間反映了權力格局。其實,空間的物理格局會“放大”、在身體上“摹寫”社會原本就有的、性別、輩分上的倫常規矩,讓這些規矩深入到身體發膚,深入到思維圖示里去。口述歷史的工作讓我們發現,隔離制深植在老人的回憶里,這體現在,當應采訪人的請求,回憶莊寨生活時,多位老人最經常主動提起的,就是性別隔離規矩:解放前女的不能在大廳走,東西不能放大廳,不能在廳堂里梳頭,也不能隨意見外面客人,諸如此類。甚至衣物在公共空間中的出現,也有性別的規約。
答:像我們女的都是放腳盆洗,拿去溪邊洗,男的衣服都是裝籃子里,女的都是手拿著。曬衣服還是有區別的,男的衣服都是放竹竿上曬,女的都是在下面架個小竹條,弄個繩子曬,樓上是從來不能曬的。
問:為什么會這樣?
答:都說我們女人的衣服(曬在外面)會丟臉。(12)根據筆者訪談記錄整理。訪談對象:洋尾村村民GZNN,85歲;訪談時間:2017年6月19日;訪談地點:福建省永泰縣洋尾村。
在公開空間、儀式空間等具有展示性質的場合下,女性要自覺避免被置于凝視之下。女性在空間中的身體位置,錨定了女性行動的邊界,也在老人的記憶中留下了刻痕。而且邊界并不以身體的游走為限制,它會擴展到作為身體附屬的衣服,以及衣服在空間中的呈現上。以往傳統的房屋研究,常強調宗族、性別等禮制體現在了房屋空間的布局上。而就像白馥蘭提醒我們的那樣,房屋布局和空間配置,其實也在“訓練”著人們對禮法的認知和默會于心。空間不僅僅是事件發生的背景或布景,它更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行動者角色。居住空間是一套模板,使得人們在每日的灑掃塵除中,重復性的去感知規矩,操練禮制,讓可為/不可為的命令反復地在身體發膚上得以刻寫并灌注到觀念中。老人在提及莊寨生活經驗時,不約而同的都提及性別隔離,說明這套空間排布在他們的認知里,已經是空間生活經驗里最顯著最核心的一個歷史事實,這種事實又與今天講究平等的情況形成強烈反差。而性別隔離之所以能夠浸入到記憶的核心位置,是因為它和空間使用習慣連帶在一起,不管白天黑夜、不分春夏秋冬,每時每刻都在框定著人們的行為舉止。這也是為什么哈布瓦赫在論述集體記憶時,認定它具有物質性和象征的雙重屬性。(13)[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5-414頁。康納頓認為身體通過內化(incorporating)實踐的重復,形成無意識的記憶,并且通過刻寫(inscribing)實踐,將身體行為的時間性轉化為媒介符號的空間性。(14)[美]保羅·康納頓 :《社會如何實踐》,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受訪老人關于性別隔離的日常生活實踐就是一個內化實踐的注腳。而受訪老人在跟筆者講述這些規矩的時候,就是將身體記憶銘刻到口述史這樣的媒介符號的過程。
又比如,莊寨各個房間的排布原則一般為:正廳為禮儀空間,長房獲得正廳附近位置最尊貴的廂房,長房以及長孫要多分一間房屋,各個房派的房屋數目均衡、區位插花分配。這個原則,分明都在提醒人們,長房為尊、同時在利益分配上強調諸子均分的漢人宗族分配等級秩序。不需要明確宣布什么道理,這種空間分布就在“宣示”著在區隔與一體化上的規矩。而宣教在集體尺度上的效果,能在多地修建的新式民居中得到印證。當代新民居因為用地面積等限制,很多還是保持著幾個兄弟共同修建居住的模式。(15)需要說明,之所以保持聚居,主要還是因為宅基地少、風水考量多等原因,無法外擴,所以兄弟成家后在一起住不是完全自愿。如果說莊寨的建筑語言有一套固定的圖示,那么最核心的圖示部分包括正廳居于住宅的核心地位,各個房或核心家庭穿插平均分配其余房間。在稍微具有規模的新民居中,無論建筑材料多么新,修筑的時間多么晚近,這兩個原則都有明確的體現。以永泰的黃姓新居為例,首先在整體結構上,整棟大樓和莊寨采取類似的平面輪廓,四面圍合,中間有天井和大廳,大廳上面不住人。一層廚房的分配按照最長輩分的兄弟分為四家。一層單間也是根據輩分、按照老房子的布局來分,其余樓層的套件則抓鬮。從上述布局來看,多個堂兄弟攜自己核心家庭共居,從長輩分家開始分爨,但故意安排了各個核心家庭的房間彼此交錯雜居,以增加互動,這都是莊寨原有空間布局原則的延續。空間的慣性聯動著身體的慣習在新的空間實踐上得以延續。
空間的示能
空間除了對人類行為進行規訓之外,空間現狀還會對人的行為進行引導,人們的行為并不單純來自社會文化的塑造,也源自對空間的適應、對空間特征的利用。換句話說,空間不但在規范性上塑造人,也在因勢利導的意義上調教人,用示意性的、非強制性的方式來引起主體能量的調動與發揮效用,此即所謂空間的“示能”。
在莊寨里,緊湊居住作為最為突出的空間狀況,不僅僅有配套的行為規范,還會催生相應的社會反應。例如,鄰里親眷發生糾紛時,因居住密集,共享過道、廚房等各類功能空間,爭執很容易被聽見,自然會有兄長或有威望的人來調解。人們對彼此生活的介入程度因為這種密集居住變得非常之高。又如,各家廚房挨在一起,廚房處在日常視野范圍內,強化了鄰里親友之間彼此關照、守望相助的關系。老人回憶說,“誰家煮飯吃差的,要悄悄的,而誰家做好吃的都會分享。” “人們眼看別人家沒米就會贈與對方。”這種行為垂范除了宗族親緣關系的影響之外,也受空間排布的催動。如果不是廚房集中,誰家吃什么,誰能看的到呢?
除了社會行為,人們對莊寨本身的空間使用行為,也在空間提供的條件許可下才會發生。例如還是回到莊寨基本的物理特征即房間稠密,這種示能導致的結果是,在59年、60年人民公社大食堂時期,很多莊寨成為天然的“大食堂”。例如在“愛荊莊”莊寨,據老人稱當時有300人從周圍重新搬入。當大密度的房屋在,人們自然會把公社大食堂的“共爨”帶回到這種可以實現共同伙食的居住空間中來。宗族伙居和集體伙居都共享著同一個鍋里吃飯的集體凝聚要義,只不過從血緣單位變換為地緣政治單位。當個體命運要被再次編織進牢固的人群集合時,不管是集體化,還是再到幾十年后的遺產熱,莊寨總會再次復活。此外,在歷史維度上,每當有群眾集會活動,莊寨都自然而然的成為第一選擇。
大食堂的案例也說明,空間的示能對人直接施加力量,突出反應在功能性對人類行為的定向誘導。例如廳堂因為開敞的空間和中心性的位置,一直保持著功能的恒定,從古到今都在發揮公共儀式和議事地點的功能。這種功能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莊寨自身沒有被徹底拆除,因為廳堂不但是公產,也是紅白喜事的操辦之地。一個廳堂一般一年只能舉辦一次婚禮。“理由是整座住宅當中只有廳才具有住宅坐址帶來的風水力量和祖宗的庇佑,相當于最聚氣的核心,每年頭一次在大廳里舉辦婚禮的那對新人,才能夠得到這份庇佑以及建筑帶來的風水,然而如果再在同一個大廳里舉辦婚禮的話, 祖宗和風水的庇佑都被前一對新人‘得去了’,不夠‘吉利’。”(16)蔡宣皓:《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清中晚期閩東大厝平面形制——以永泰縣愛荊莊與仁和宅為例》,同濟大學2018年碩士學位論文,第56頁。風水是中國文化背景設定下的示能在字面層次上最唾手可及的例子。當廳堂出現在人們面前,人們自然知道怎么去利用這個祖先遺留的儀式空間,甚至要去爭取空間“示意”的“勢”與“能”。
風水的例子還說明,示能也不限于物理的功能性,還涉及到空間的等級和場所的象征意義。傳統社會的士紳、地主、富裕的農民家都會有象征著重視文教和社會地位的書房或書齋,莊寨亦不例外。莊寨往往設置有書齋樓作為讓子弟上私塾的場所。書齋樓一方面是公共空間,同時也享有較高的地位。建國前,高級客人在書齋樓被招待。例如愛荊莊的書齋樓在 1957-1958年曾作為愛荊莊初級社,后來做衛生所。一位因為醫術高明而在當地頗受愛戴的外地醫生,被安排在書齋樓工作居住。這個外地醫生之所以醫術高明也正因為他本身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當地是少有的高級知識分子,所以和書齋樓在文教意義上的社會象征相符。
空間與人的互動也發生在細微之處。某莊寨正廳前面的石頭階梯兩邊有堵頭的條石,被打磨的很光滑。老人說這石頭的質地之所以變得光滑,“是因為這是我們的滑梯啊”。經年累月,條石作為滑梯,被小孩子的身體打摩得光亮。這里的示能,即階梯兩頭條石斜面的形制,誘發了小孩子滑行的動作,繼而在行為的影響下,環境改變了自身的外形,條石變得光滑。示能不僅僅被視覺捕獲,即不僅僅在物理外形上向人們發出訊息,也可以通過人體其他官能,例如嗅覺、聽覺、觸覺等等,進入主體世界。例如建成環境里最常見的一個指標就是局部微觀氣候。南方濕熱的環境下,大門口有過堂風,那里優越的局部小氣候,使得人們喜歡在此地乘涼聚集。但因為處在內外交接的公共區域,就成為家族里男人們,而非女性,在一起聊天、吹拉彈唱的地點。任何一個類似的環境,但凡具備了一定的條件,必定會引起人群的聚集。這也是為什么鄉村建設中,都注重公共空間的營造。背后的邏輯是通過空間來增進社群交往,加強社會向心力。
空間的示能不僅僅是空間物質本身的邀請,往往還源自自然與物質的交接面。在現代化帶來的便利之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對莊寨零部件的利用而生發出來的生活智慧,是超出今人想象的,例如利用陽光照射建筑物角度來計時:
問:過去家里很少有點鐘,三餐煮飯怎么知道什么時間阿?
答:過去歞婆(老嫗的謙稱)看日頭咯,日頭(光)照在走廊第一個臺階,差不多是將近11點,就可以煮午飯了。(17)根據筆者訪談記錄整理。訪談對象:洋尾村村民BFNN,82歲;訪談時間:2017年6月19日;訪談地點:福建省永泰縣洋尾村。
用空間和日照來計時的案例,說明空間是丈量節奏的工具,是時間的刻度,一日例行的軌跡,在細節中我們建立起來空間和時間的聯系。如果把空間僅僅作為制度文化的載體,是無法發現上述生活細節的。我們對空間的感知,遠遠超出了布景或場景這么單一的維度。空間是開展日常生活的重要角色要素。
空間的氛圍
作為環繞主體的周遭環境,空間會直觀的影響主體主觀性的感受。環境心理學對此已經有很多研究,而我們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心理反應所引發的社會后果和背后的文化邏輯。除了心理主義之外,深受現象學影響的建筑理論家們也提出了“場所精神”的概念,將建筑看作人們生存生活的意義的具體化,看作關于意義的解決方法。(18)[挪]諾伯·舒茲:《場所精神:邁向建筑現象學》, 施植明譯, 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年。場所精神在情感與記憶中形成,自然就離不開人的意識和行動,其呈現往往是一種總體氛圍。所以,除了強調空間本身的屬性和塑造能力,有必要從整體上去把握人們對空間的體感與認知。哈布瓦赫已經指出,在記憶的喚起、消除和重構的過程中,建筑扮演重要角色。(19)[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第315-414頁。然而這個參演過程,除了如哈布瓦赫所發現的那樣,建筑是群體認同的象征凝結之外,筆者認為建筑作為一種空間氛圍,和主體感受的互相滲透、互相演繹,并且這些空間氛圍通過圖片、視頻等進入媒介記憶,也是建筑能作為社會交流系統關鍵元素的重要因素。另外,近幾年隨著場景消費的升級,社會學家提出“場景理論”,認為場景不但是一種情勢,也是美學特征,人們會根據場景來協調自身的行為,場景也會影響經濟增長、社會組織形態、擇居偏好、資產估值,以及人們如何在本土真實性中自我表達。(20)[加]丹尼爾·西爾、[美]特里·克拉克:《場景:空間品質如何塑造社會生活》,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所以需要重視氛圍的“生產力”,它不再是一個虛無縹緲的、美學意義上的范疇,而是一股社會生產的力量。
在莊寨被使用的時期,人們對莊寨的普遍印象是“熱鬧”。家族聚居所凝聚起來的旺盛人氣,人與人之間平常密切頻繁的互動,讓年邁的回憶者想起來津津有味。“那個時候好多人住在一起,很熱鬧。”“小孩子會聚集在那個空場(手指正座前的天井)玩,打乒乓球。”這個時期,人們對莊寨的視角,完全是內部視角,莊寨就是自己身體每日感知到的日常生活,歡聲笑語穿插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里。人們對莊寨的感知,是多維度的,滲透在身體發膚里,遠遠超出視覺審視。莊寨在廢棄之后,且在被當作文化遺產予以重視之前,多數已經坍塌空置多年,雜草叢生,梁斷瓦殘,只有一些莊寨的廳堂作為儀式空間得到維護。所以在普遍缺乏莊寨生活經驗的當地的中青年心目中,莊寨給他們最早的印象是“陰森可怕”,“小時候都不敢進去”。除了偶爾的儀式功能空間,多數時間里莊寨都是人們自動遠離的一個廢墟。當莊寨被修繕起來,各個房間里的廢舊雜物被清空,修葺一新的莊寨因為大規模的居住形制又開始引誘起視覺上的黏著。這個階段,多數莊寨圖片都必備一張俯瞰圖或航拍圖,因為只有從上空俯視莊寨,莊寨作為大型民居的尺度和規模才能被最佳程度地呈現。許多莊寨的宣傳圖,還配上了牧牛、老農、油菜花等有田園牧歌想象的襯景。所以這個階段的莊寨,人們的凝視角度,已經從“心驚膽戰地窺探荒廢的老屋”,轉變為帶有距離感的,帶有對田園生活的想象意味的“遙望老家”。莊寨之“美”,被頻繁推到各種媒介。莊寨的場所氛圍也隨著遺產和旅游開發,變得再次“熱鬧”。一些活動開始有意在莊寨舉辦,包括政府的文化展覽、黨課活動、年輕人的市集活動等。莊寨蘊藏了諸多開發利用的可能性,尤其是旅游、文創、生態農業等各方面人與物資的集聚。作為炙手可熱的資源,莊寨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并隨著莊寨保護辦公室的成立進入政府的主導性話語和體制建設中來。
莊寨的空間氛圍,從主體感受層次這一方面來說,經歷了從日常使用中的多維感知到廢棄以及修繕階段的視覺主宰,再到遺產活化階段的再次豐富。從場所性質來說,莊寨經歷了這樣一個嬗變過程:從樸素的大型農宅,到凝重遙遠的廢墟,再到流于景觀化的遺產。場所如果因為意義層次多寡而有“厚度”的話,那么莊寨也經歷了從厚到薄再到中間程度的狀態。在不同的氛圍中,場所本身是流動的,隨著自身條件和外界環境的變化,而生發出不同的引申意義。或者說,物質形態未變的民居,其價值和意義一直在公開的被各種解讀。在不同階段,莊寨的不同部位被放大:先是作為家宅的日用而不知,再是整體被忽略的廢墟一片,唯留廳堂因為功用而赫然醒目;在當代,整體造型被拎到聚光燈下,建筑細節和雕刻裝飾被反復放大、推向前臺。在不同時期的認知中,建筑空間體現了高度的流變性,依附于當時當地的集體記憶和敘事。
空間的氛圍,是由事件推動,也必須經由主體主觀的感受傳達。集體記憶、集體敘事在表達主觀感受上的區別的同時,也借由被遮蔽掉的主觀性感知揭示出“另一個聲部的歷史”,普通人的講述不僅僅能幫我們揭示所謂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他們本身的經歷在呈現事實這個層次上,本身就有非凡的意義。當所有老人回看莊寨都提到“熱鬧“這個關鍵詞時,也有老人對莊寨的回憶是過密勞作而帶來的白茫茫的“空鏡頭”。一個曾在莊寨生活的老嫗,對莊寨生活的印象除了熱鬧,還有密不透風的作息安排所帶來的“空”——過度勞作之下,勞作者面對場所,是一種時間如白駒過隙一般流逝、精力都耗散在具體勞作中的“無感知”。熱鬧經常是和閑暇劃等號的,她作為家庭婦女,恰恰缺少閑暇:
問:那不是很熱鬧嗎?
答:也不熱鬧。
問:晚上不熱鬧嗎?
答:不,你補衣服,我洗衣服,她洗鼎灶……,個個忙做事情。明早如果去做事情,半夜要起來煮飯,喂雞鴨,照顧孩子吃喝……以前非常辛苦。下雨天也沒空,洗鼎灶、桌椅等,一下大雨馬上搬出椅子放在下埕沖。
問:一年365天都在做事情嗎?都沒空攀講?
答:是,除了病痛。去砍柴時一起走,一起攀講一下。(21)根據筆者訪談記錄整理。訪談對象:洋尾村村民GZNN,85歲;訪談時間:2017年6月19日;訪談地點:福建省永泰縣洋尾村。
從我們的訪談可以看出來,家庭婦女所承擔的家務和生產勞動,穿越了白天黑夜,覆蓋了家里家外。今天的莊寨總是通過視覺手法去宣傳“田園牧歌”,而莊寨的日常生活,撐起莊寨日常生活的婦女所做出的經濟和家務貢獻,如果沒有口述歷史的方法進入空間生活的細部,如果沒有對聽覺、觸覺等多維度身體感官對空間氛圍的整體感受的關注,那么這一部分歷史,很容易隨著被大事件奠基的制度研究被淹沒在社會科學宏觀分析的隧道里。這種隧道,就像一個透鏡,把視覺呈現背后的很多基本的東西朦朧處理以至美化。這也是為什么在當前的空間氛圍營造中,莊寨似乎就是傳統美好鄉居的縮影。景觀化的形象不斷疊加,其實并沒有增加厚度,而是流于表面,反復疊加出來的只是單薄的“景觀”,是缺少真實細節支撐的刻板印象。人們不再去想是誰的雙手撐起了寨墻和木梁,不再去想當遺產還是“活著的”房子(而非人們“構想的”意象)的時候,人們如何去打量它的,如何去改變它,它又是如何改變人的。對空間的切身性(embodied)的研究,對空間氛圍給人帶來的身體感知的“軟性”調查,能幫我們拾取視覺主宰之下遺漏的“硬性”信息。
結論
人們太過習慣于透過物質看背后的本質,就如人類學家Webb Keane指出的那樣,西方社會科學有一個傳統,似乎“意義”隱藏在 “事物”背后,把事物當成是意義的喬裝打扮,似乎必須把物質剝除干凈才能見到意義本質。Keane認為對意義的追尋導致在實際生活中至為關鍵的一些領域,例如“行動”、“結果”與“可能性”,在學術語境下顯得不再重要。(22)Webb Keane, “Signs are Not the Garb of Meaning: On the Social Analysis of Material Things”, Materiality, ed. Daniel Miller,(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pp. 182-205.筆者認為,如此本質化的重視“意義”,導致上述抽絲剝繭的工作,似乎和真實世界的邏輯隔著一定距離。事實上,物質本身也在參與著所謂本質原理的形成,是人們的行動前導,也是塑造可能性的重要自變量之一。
建筑空間除了其物質實體的功能性本身,還帶有精神、審美、意識層次的特性,這種特性依附于獨特的社會形態存在,依附于生活與人的記憶存在。但作為物質的空間不能消解于社會文化范疇,它受制于社會安排的同時,本身也有自身的邏輯。兩套邏輯的交叉點,就是空間與人的交接面,不管這種交接是房屋形制和禮制影響下的空間使用規則,還是空間對人們的邀請,還是建筑本身的韻律感和秩序感帶給人的主體感受。在交接面上望進社會歷史的時空,會發現房屋不僅僅是制度的體現,它本身就是再生產社會的制度性安排。
本研究就是在人與空間的交接面上,按照強制性程度的不同,區分出空間的規矩、空間的示能、空間的氛圍三個指向人文世界的“發力點”。永泰莊寨是家族聚居型的大型寨堡式民居。不論是作為家宅使用、還是作為財產分配,以及作為文化遺產、旅游資源和活動場所,在各個時期莊寨對人、記憶、身體和社會文化的生產力、塑造力,都貫穿了上述三個方面的“力”與“氣”。空間的能動性,不意味著單純的強調物對人的支配,也不意味著它是一個浮于表面、沒有時間縱深感的概念,僅僅靠描述就可以證明的單薄的立場。空間與人一直是在具體的、切身性的實踐中,循環往復的交互性的彼此發生作用。空間對人的塑造可以通過固定的空間圖示的機制,進入到人的認知圖示中,并延續世代。我們在對空間的力與氣的提煉與明確認知中,完成的不僅是認識上的更新,還是對日常生活的重新評估,對被視覺中心主義遮蔽掉的社會事實的再次拾取。
傳統的社會科學并不習慣從物質本身去認識物質世界,對物質的意義解讀總是無法脫離人,也沒有看到涉身化經驗的重要性。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幾乎很少討論空間的物質基礎在性質上的差別及其對身體、記憶與社會的改變意義。本體論轉向給物質研究重新提供了伸張物質性的渠道。建筑空間的物料屬性,包括材料、顏色、韌度等等,在很多社科研究中都被過濾掉了,成為建筑學者反復琢磨分析的內容。恰恰是這些物質屬性,給物質以存在意義上的價值,也正是物料的物理屬性,讓物對人的影響和塑造有了支撐和依據。莊寨的例子傳達出空間作為物質,對于社會具有塑造性的力氣。對記憶的形塑、對身體的訓練,不只是文化規約、社會制度在起作用,亦有很多物質本身的邀請、矯正、提醒等等。物質屬性的獲知,需要打開更多的感官。特別聲音、光線等視覺所能捕獲的信息之外的感官細節提供了細微而關鍵的線索。更為通感的身體/空間感官認知會讓更全面的社會事實融進我們對文化邏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