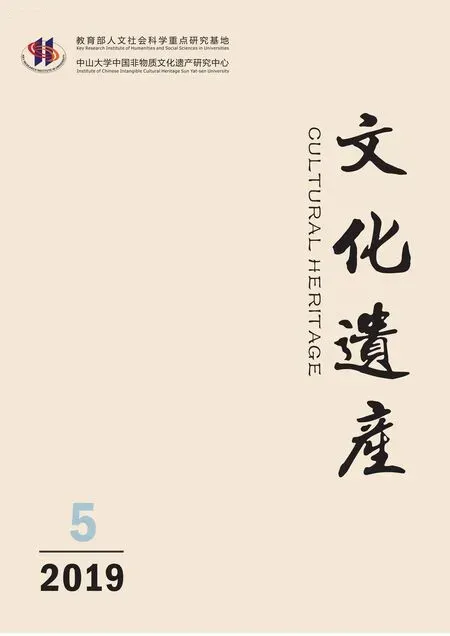非遺保護與傳承的記憶闡釋
——以山東省萊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例*
馬知遙 劉智英
記憶這個概念,首先想到的是人類思維中信息內容的存儲與使用的基本的心理過程。不過,記憶所存儲的內容、這些內容是如何被組織整理的、這種記憶被保存的時間長短,卻遠遠不是用人體自身能力和調節機制就可以解釋的問題,而是一個與外部相關的問題,也就是說,這是個和社會、文化外部框架條件密切相關的問題。莫里斯·哈布瓦赫特別指出記憶有外部維度,指的是對物、風俗、儀式、交往、語言等的記憶,(1)[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0-12頁。積淀在空間、時間、行為、身體和器物等具象中(2)[法]皮埃爾·諾拉:《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黃艷紅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中文版序,第12-13頁。。它是鮮活的,需要借助人(主動性)和物(被動性)進行保存與保護,“等同于想到的”(3)[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與變遷》,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2、31頁。,也就是發生過的事情的知識體量,往往與傳統發生聯系。而“作為地域文化和情感體驗的鮮活載體,通過世襲沉淀、凝聚,展演出地方所孕育的歷史信息、文化內涵、地方關懷和人文情感,具有突出的記憶表征和文化內斂性”(4)周瑋、朱云峰:《近20年城市記憶研究綜述》,《城市問題》2015年第3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就包括在記憶外部維度中。當下,記憶的邊緣在知識無限增長的過程中淹沒,記憶的功能病態地膨脹,這種功能與對記憶失落的焦慮緊密相連。非遺的活態性本應具備一種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當下條件和要求的基本素質,泥沙俱下的大眾文化不斷蠶食、收縮、稀釋、消解甚至自毀有關非遺的記憶,非遺的記憶面臨著破碎、失憶等危險。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搞清楚記憶視角下非遺的時間、空間與傳承主體以及它們背后的意義,通過闡釋時間、空間與傳承主體,希冀為非遺保護與傳承從記憶維度提供一定參考和借鑒。
一、非遺中時間的記憶
談到非遺的記憶,必然繞不開時間。當下的非遺的記憶夾雜在不可預見的未來與臃腫不堪的過去之間,成了我們理解非遺的范疇。對這樣一個信息不斷膨脹的當下擠壓著非遺的記憶,我們只有透過充滿既成事實的過去才能把握。非遺中的時間,既是人生禮俗的時間,又是歲時節令的時間。前者強調記憶的存在性以及有效性節點,涉及到傳承主體人生維度內與非遺產生聯系的重要時刻,相對于個人生命歷程來說,屬于一次性時間。后者是記憶激發的促發節點,屬于反復回歸和規律性現時化時間。
先談人生禮俗的時間。“文化遺產的形成歷史是由一連串的斷裂所決定的”(5)[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與變遷》,潘璐譯,第51頁。,非遺在記憶層面也經歷著各種時間轉折點的斷裂,而這種斷裂以誕生禮、百歲禮、成年禮、婚禮、建房禮、六十大壽禮、葬禮等一次性時間節點在“冷”與“熱”(6)術語最初來自于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德國學者揚·阿斯曼以這種方式為基礎對其發展,“冷”社會指的是思維僵化、穩固的社會,發展變化意識薄弱的社會,“熱”社會是思維活泛、發展變化意識強烈的社會。的社會所顯現,是人的生命歷程層面的歷時性時間。
以萊州市的省級非遺花餑餑制作技藝為例,麥作文化的衍生民間工藝品,造型極具膠東風味,形式多樣,包括圣蟲、月鼓、壽桃、棗餑餑、繭餑餑、巧餑餑等等。筆者發現它是目前萊州市非遺自我造血最好的一個項目,假設其它元素為定量,這里僅從花餑餑相關的時間節點上分析傳承效果的根因。萊州人說到營造房屋,除了擇吉日選良辰,還有最熱鬧也最重要的時刻,那就是房屋上梁、拋梁的時序,而這時會想起各種面制的肥豬拱門、獅子把門、面燕、圣蟲等面塑。結婚的時候,雙方家庭自然會想到要制作花餑餑作為互贈的形式,比如,男方給女方送發面做的二十個面桃,女方留下十個,然后回贈男方龍鳳、鴛鴦、獅子、佛手、金魚、蝴蝶等對數不等面塑。當小孩誕生百歲之時,萊州人多會想到去面塑藝人那里購置一批百歲子,舉行隆重的過百歲儀式(7)萊州當地一種小孩出生一百天求吉納福的儀式,這天會制作一種稱作百歲的面塑,其形兩頭凸出,狀如梭子,俗稱歲子,有長命百歲的寓意。,目前這一儀式十分盛行。據老人回憶很早以前小孩參加科舉時,還會制作面柿子,寓意“中試”之說。雖然人生禮俗涉及到的時間并不像年節周期性循環,卻是絕大多數人生命維度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時間節點。回憶者通過人生維度上這些一次性時間樞紐啟動了所傳承的非遺回憶,進行時間索引式的敘事。這種時間記憶的共象是因為“意義、重要性、值得回憶性等存在于那些一次性時間,特別是例如驟變、變遷、發展和成長或者衰落、下降、惡化等之中”(8)[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第67頁。。記住這些一次性時間,指引了非遺相關意義、重要性事件與值得回憶的記憶。這種記憶術利于培養“只有具有重要意義的過去才會被回憶,而只有被回憶的過去才具有重要意義(9)[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第73頁。”的潛意識。而這種潛意識利于長久持續性地保護與傳承非遺。
萊州花餑餑通過時間不僅回憶到人生禮俗有關的記憶。另一方面,在時間記憶上,還能想到十分明確的傳統節日類非遺。傳統節日類非遺的時間作用是通過回憶作用于節日時間之內的整合力,從時間軸上多個節日的時間節點(有的非遺集中于某一個節日),借助后顧性記憶,把不共時的記憶拼合與建構到自我之中,去持續性地對過去的經驗進行具體化、現時化呈現。非遺的保護與傳承,現時化的時間元素在里面功不可沒。說到春節,圣蟲、棗餑餑、小餑餑成為整個年節的記憶關鍵詞;正月十五,繭餑餑必不可少;二月二,打囤時會擺上圣蟲;三月三,新媳婦回娘家需要帶面燕;談起七夕節,當地人自然而然地回憶起用餑餑磕(萊州當地人念ka)子磕制巧餑餑的場景;中秋節,人們會想到做月糕、月鼓,祭月賞月的場面等等,諸如此類。“偉大的日子喚起偉大的記憶。對某些時刻而言,光輝的記憶理所當然。”(10)[法]皮埃爾·諾拉:《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黃艷紅等譯,第106頁。傳統節日雖然談不上“偉大”,但絕對是“光輝”的。它“是中國人生活情感和愿望的共同表達”,要么我們的年輕人已沒有了“節日記憶”(11)馮驥才:《節日的情懷是不變的》,人民網,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5/0116/c87423-26395923.html,訪問日期:2015年1月16日。,要么我們的年輕人即使有“節日記憶”,已不純粹。情人節涵化著七夕節,萬圣節影響著中元節,圣誕節沖擊著春節。我們的非遺,我們傳統節日的記憶本已趨向淡漠,還經受著外來信息占據與分流著固有存量的記憶空間。于是,傳統節日的時間節點回憶本身是承載文化習俗與情感的凝結性結構的一部分,通過周期性循環往復獲得時代性位移從而再次辨認,使得不共時的傳統節日記憶與當下頻繁互動而常憶常新,從而被當做共同文化因素得到集體的認同。與此同時,非遺時間記憶稍縱即逝,記住非遺不僅靠正月初一、七月初七等眾所周知的時間,還要給時間一些時間,即假日給了節日以時間,傳統節日的時間節點需要人們花時間,花心思去回味、體悟。這也就是為何馮驥才先生要強調“節日不放假必然直接消解了節日文化,放假則是恢復節日傳統的首要條件。”(12)馮驥才:《我們為什么要過傳統節日》,搜狐網, http://www.sohu.com/a/277486704_743805,訪問日期:2018年11月23日。
綜合考量,通過這些“共同棲居的、被墾殖、精確度量和控制的”(13)[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第81頁。人生禮俗與傳統節日中的非遺時間,面塑在時間中以回憶的方式多次召回,在時間節點的助力、激活與維系下不斷獲得匡正、反芻與加強,此時時間是有意義的,有情感的,一定程度上強化、彌補與保鮮了非遺記憶。這種時間節點對非遺保護與傳承的強化力不僅超越了時間本身,也跨越了空間,即使是生活于外地的萊州人,在某一時間并不在原有生境,每逢春節、十五等時間節點,時間作為索引,亦會產生每逢佳節倍思“遺”的現象。這類人會購置一批花餑餑,這也是一些花餑餑作坊、工廠一部分營業額來自于旅居外地的本地人現象的原因。萊州花餑餑隨著時間節點的關注成為記憶熱點,花餑餑越受重視,社會的資源就越加傾靠,形成良性循環。
時間依靠“重復的壓力”來強化我們的記憶。比如,萊州市市級東海神廟祭祀活動。自西漢以來,萊州市民眾圍繞著海神崇拜形成的一種特有的海神文化。每年正月十八、四月初三、六月十三與十月初三村民會舉行隆重的祭拜儀式,這時的日子最初僅是代數意義上的空洞數字,依靠上千年的重復在當地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懷舊情結。東海神廟祭祀活動最初是帝王祭海的儀式,自秦皇、漢武到清光緒十六年(1890)最后一次帝王祭海,共81次。由時間激發的祭海記憶被植入到聲音、身體、面部表情、肢體動作、舞蹈、旋律和儀式行為中。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每次慶典內部的時間次序得到了確定,樂人演奏曲調的前后必須依照時序規定,連神前桌椅器皿擺放的時序都要按規矩來。與此同時,每次慶典都與之前的關聯慶典聯系到了一起。這樣,每次慶典都依照著同樣的時序來不斷地重復自己,就像設計學領域二方連續的花紋總是以不斷重復的圖案呈現那樣。東海祭祀儀式依托重復的指涉方式,定期回憶組織形式,從而重復著相關性的慶典,利于儀式本身構建統一體,提供規范性和定型性的行動指南,培養了儀式感。而且,它更重要的意義是歷史時間現時化為一個不共時的事件,并給予部分更新與替換,不僅僅一直遵循完全相同的規范進行,避免文化失寵。具體表現是,隨著祭祀儀式逐漸演化成凝結性結構的一部分,對非遺時間記憶的回憶并未缺少機動性,表現在保持與模仿,同樣表現在回憶與闡釋上。民間對這四大海廟祭祀日子基于回憶基礎上又進行新的闡釋,“正月十八,海廟萬樹芽始發,春風百帆遍天涯;四月初三,春潮如煙,百魚上灘;六月十三,求雨祭天,雷公閃電;十月初三,秋風肥蟹到海邊,斜陽魚蝦滿船歸”(14)劉巨峰主編:《煙臺區域文化通覽·萊州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8頁。。正是這種時間記憶在定型性與自主性的兩極之間擺渡形成了現實層面的非遺保護與傳承。祭祀儀式作為時間記憶的組織形式有序地進行,鞏固了認同知識的保護和傳承,并由此保證了文化意義上認同的再生產。這種以時間來記住非遺的作用從其它方面皆有所表現。從地方上看,就可以解讀為何會常常看到某某年畫節,第五屆某某打糍粑節等效仿盛行,從國家層面上,就明晰了為何要把本無意義的每年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的時間設置為自然與文化遺產日。
非遺的記憶要想被回憶召回,就需要一個擁有完整節點的時間模型,一個特定時間使其現時化。不管對非遺時間的記憶是具體或模糊,保護和傳承非遺,就要記住非遺這些時間,維系、存儲、豐滿、激活非遺重要時間節點。“誰若還在今天期望明天,就要保護昨天,讓它不致消失。”(15)[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第24頁。把這些“不合時宜”的時間以不斷重復與現時化的方式激活、召回或強化非遺的指向性記憶,實現永恒的重演,成為引以為榮的時間。對非遺的時間記憶,以一種有時稍顯模糊的熱情眷戀著那些凝結著人民之靈魂的時刻,眷戀著那些濃縮和表達出集體意識的歲月。
二、非遺中空間的記憶
時空關聯是記憶的常量之一,總是在具體時空下去促發一些記憶結晶點。記憶在時間和空間搭建的框架或提供的線索中被喚醒,圍繞著我及我的所屬物展開非遺物化或擴展化。空間,作為一個中性的、去符號化的具有可替代性和可自由支配性的范疇(16)[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與變遷》,潘璐譯,第346頁。。它是抽象化的數據堆砌與均質化的淺層體驗,側重實證,是人文主義失落的編碼性符號(17)[美]段義孚:《戀地情結:對環境感知、態度與價值》,志丞、劉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405-406頁。。而“地點和物體定義了空間”,并且“地點和物體都是價值的中心”(18)[美]段義孚:《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王志標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3頁。,因此,地點與物體相較于空間除了涵蓋其物質性,還具備了非物質性。非遺所采用空間核心術語:文化場所“不僅是單純的物質空間,而且承載了人們認知空間的歷史、經驗、情感、意義和符號”,(19)程世丹:《當代城市場所營造理論與方法研究》,重慶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所以,更契合地點與物體的概念與范疇,基于此,對非遺中的空間記憶本文遂采用對地點與物體的記憶。
地點是非遺記憶不斷反芻化的重要樞紐點。雖然,地點如同時間一樣,它“并不擁有內在記憶,但是它們對于文化回憶空間的建構卻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因為它們能夠通過把回憶固定在某一地點的土地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證實,它們還體現了一種持久的延續,這種持久性比起個人的和甚至以人造物為具體形態的時代的文化的短暫回憶來說都更加長久”(20)[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與變遷》,潘璐譯,第344頁。。也即是說,地點本身可以成為記憶的重要助產士,是一個存放美好回憶和輝煌成就的檔案館,甚至可能擁有一種超出于人的記憶之外的記憶。
作為地理意義上的地點與非遺記憶的依托性關系,在現實中出現兩種情況。其一,地點所承載的記憶實則是地點中所生存的人的記憶,地點與非遺并不存在唯一的指向性。所有此時地點并不成為促成與助長非遺記憶的基石,并不助于根本上維系其生存發展。比如,筆者采訪呂村年畫傳承人張同杰時,張師傅說過“后莊頭繩割(念ga)的,南李紙扎的,呂村紙畫的,城子埠做鞭的”(21)張同杰藝人的錄音整理。采訪人:劉智英,被訪人:張同杰,采訪時間:2018年12月18日,采訪地點:呂村張同杰家中。,而目前只有呂村年畫還依然活態傳承,其它村落的標志性文化早已消失。這里地點對非遺記憶遺忘的阻礙裨益不大。其二,萊州人一說到麻渠村,首先會回憶那是制作大糖的地方,說到呂村就是年畫,說到沙河鎮就是草辮發源地,從這里可以看出地點在某些非遺記憶維系上只能“錦上添花”卻做不到“雪中送炭”。
即使這樣,作為記住非遺的記憶核心要點——地點——用來從非遺記憶的地點回到回憶地點這一步來說,仍然十分重要。它一定程度上充當著非遺記憶的防腐劑,內含著靈活意識的束縛。而且,有的非遺與地點記憶息息相關,甚至至關重要。譬如,以萊州市民間文學類非遺為例,文峰山傳說、望兒山傳說、優游山下乾隆帝傳說、臥牛石傳說、神仙洞傳說等。此時流動的記憶在此地表現出深厚的“戀地情結”,優于文本等一系列固化的儲藏方式,貯藏記憶的特定地點成為非遺記憶最好的保鮮劑,稍縱即逝的語言的恒久保險單。地點記憶在記住非遺的強弱性來自于非遺本身的強弱性。非遺的“內在體驗越是薄弱,它就越是需要外部支撐和存在的有形標志物,這一存在唯有通過這些標志物才能繼續”(22)[法]皮埃爾·諾拉:《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黃艷紅等譯,第13頁。。民間文學最初同時也是最重要的載體是語言,而語言記憶僅憑個人的記憶力,本身就易出現混亂與遺忘的現象。這時,地點就充當了一個逝去的、脆弱的過去不容置疑的見證。地點記憶在文峰山、望兒山等抑或是感激的地點,抑或是崇敬的地點,發揮著獨特的回憶功能。這種記憶術把一份扎根于特定地點的遺產重新從記憶的后臺搬上舞臺,通過對這方領土的執著思索、談論與書寫等方式,完成一系列追念性演出,呈現出此地沉淀著的精神、理智與情趣,重燃沉寂著的文明與思想,整理層疊著的過往與歷史,為文峰山、望兒山等地注入一份特殊的價值,暗示著它的古老與意義,使其升值。對這些地點,甚至附會些標志性人物(如乾隆帝在優游山的傳說,趙匡胤在萊州的傳說等)的回憶,亦是把光輝的主題限定于土地這種獨一無二的形象中,心境隨著土地的深刻而深刻,非遺記憶走出不明確的地帶,成就一個明確而鮮明的形象,由此引發人們對其地點的“深度體驗”,強化了地方性認同,利于保護與傳承非遺。
再說物體。民眾的戀地情結里蘊含著與物質界的親密關系,他們依賴于物質,同時也蘊含著物體本身作為記憶與永續希望的一種存在方式。人總是被或日常或具有更多私人意義的物所包圍,這些物物化了諸如實用性、美觀性與舒適性的地方性知識。它們反映著人自身,讓他回憶起自己的經驗、自己的知識體系等。于是,物體的記憶總是充當了迅速而決定性的流逝意識與對當下確切意義的焦慮的結合物。尤其是非遺中包含的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對它的記憶有形形色色的表現物,以最微不足道的遺跡、最細微的見證物,到最宏大、崇高的物體,從最莊嚴的到最簡陋的皆而有之,賦予它潛在記憶性的榮譽。
這里以萊州市縣級非遺平里店鎮麻渠村大糖為例,說明物體的記憶對非遺保護傳承的重要作用。麻渠大糖是傳統的糖果,出現于四五百年前,是麻渠人冬閑時節主要的生活來源,更是當地重要的文化記憶。麻渠大糖口感酥軟松脆,麥芽糖的醇香和芝麻粒的油香混合在一起,風味獨特。麻渠大糖制作前后需要備料、發芽、研磨、攪拌、過濾、煮沸、沉淀、熬制、燙板、捧頭、拔糖、搓挺、上氣、上芝麻、拉盤子、撐圓、涼糖等十幾道工序,每天從早上三點一直忙到晚上十點左右,每人各守一攤,各負其責。
如此多的工序,如此長的制作時間,自然少不了繁多的工具。而這些工具,據筆者田野調查發現,相當一部分面臨著被迫更替。其一,麻渠大糖屬于行商,早年間走街串巷,離不開叫賣張羅。最初是鑼鼓,隨著發展演變成了方言味道的吆喝聲“大糖、大糖,麻渠大糖,又脆又甜,真香真好吃”。科技的進步,吆喝聲錄入了電音喇叭,循環播放,而如今城市文明建設的需要,麻渠大糖兜售時不能吆喝,只能噤聲。其二,所有由松木、楊木材質制成的器皿皆要換成2.0mm晶鋼材質的器皿,據多位制糖師傅反映,這種替換先不說制糖師傅能不能勝任,單單對大糖的精華——口味就是毀滅性打擊。與此同時,材料的變更,帶來火候的難以掌控,以及在熬制過程失去了原有木香的沁入,很難做出原有味道的大糖。其三,熬糖稀工具也變了,過去作頭和二把刀(一種稱謂,相當于糖坊主與副糖坊主)領著大家集體用木锨攪拌、翻轉進行煎熬,如今木锨替換為電動攪拌機,這種替換是熟人社會的熱火朝天替換為一位師傅依偎在機器旁落寞的獨守。其四,燃燒材料因為林業局的介入,由最初的松木變成煤炭。而最近環境保護部門又提倡所有煤炭統一變成環保煤炭,不僅僅提高成本,而且火候難以掌握,這些都慢慢消解著本已風雨飄揚的麻渠大糖。除此之外,還有交通工具,碾磨工具、大糖本身等的替換。這些替換確實有些是為了非遺更好傳承做出的改進,也取得一定的效果。而有的改良就是“新形勢,舊傳統”的大環境下,一種新的必然優于舊的思維對非遺進行的臆斷。這才會出現在非遺保護與傳承中,一些現代化、機械化的工具替代了傳統的工具,反而傳承效果大不如以前的現象。
從表層上看,流水線的批量作業、標準化的配置與冷冰冰的技術鍛造出的等價事物替代了麻渠大糖的原始老物件。從記憶維度上看,無形中強化了傳統衰微的潛意識,消解著制糖師傅對其手藝的情感,蠶食了物件背后的象征性。這種替換隔離了傳承人與麻渠大糖十分脆弱、難以感知和描述的傳統文化記憶的聯系,切斷了傳承人與那些已經凋謝的鏡像之間無法根除的切身眷戀感。而最終這種替代與切斷會帶走它所鑲嵌于物體的麻渠大糖的記憶。由點及面,這里不僅指涉于麻渠大糖,在所有非遺的傳統物體中,它們的印痕可能來自于那些令人敬畏的遙遠的故事,它們的形制可能是祖先民間智慧適應自然的觀念。每當傳承人進行實踐、表演、交流時,這些與傳承人并置于一起的老物件會在回憶的力量下重新化成保護與傳承非遺的注解。段義孚先生曾說過“某個人所擁有的物品是他人格的延伸,貶低了那些附屬物的價值就等于削減了他的人生價值”(23)[美]段義孚:《戀地情結:對環境感知、態度與價值》,志丞、劉蘇譯,第147頁。。各種保護與傳承口號與政策不斷推行,基于合情合理合法的維度下進行改善、限制與替換,實則是改善、限制與替換傳承人對自身文化的自信與依戀的記憶。傳承人所持有的物體,那些已經有了情感,有了意義的物體,就像一本古老家譜,里面有傳承人的父親、祖父與兄弟姐妹。如若不去保留這些傳承人的物體,意識到記憶對傳承人的重要性,保護與傳承的口號越響,踐行越多,反而愈發加劇傳承人無能為力的悲鳴度,愈發營造傳承人當下舉目無“親”的落寞感。這也就是制糖師傅孫聰彬為何說出這番感嘆的原因,“就這么回事吧,愛吃趕緊吃把,這些老把式(伙計)干不動了,這些老家什兒(物件)都換了,三兩年說不定麻渠大糖就真成了個念想了。我說這句話的時候,麻渠二村的孫師傅還說‘你真樂觀,照著這也不要用,那也不敢使(的形勢),說不定明兒就沒了’。唉!就是這么個形勢。”(24)藝人孫聰彬錄音整理。采訪人:劉智英,被訪人:孫聰彬,采訪時間,2018年12月23日早四時,采訪地點:麻渠村孫聰彬塘坊。
三、非遺中傳承主體的記憶
誠然,對非遺中時空關聯的記憶重視與再認識對非遺保護與傳承大有裨益,但對非遺記憶起到奠基作用的“記憶之所”實際上是傳承主體——個體與集體。他或他們是非遺記憶的被動持有者也是主動激發者,充當過去的代言人和未來的傳遞者。隨著不斷地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非遺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已喪失了原先所擁有的無可替代性與理所當然性,出現了諸多替代傳統指涉的等價事物,鑲嵌在記憶中的傳統根基面臨著覆寫、消除、蠶食。要想對尚存于傳統的余溫、緘默的習俗和對先人的重復中的經驗的記憶趨向自動消失、落寞、被塵封或遺忘的頹勢得到緩解、擺脫,甚至扭轉,從記憶視角上看,僅關注非遺中時空關聯的記憶是不完整的、碎片的、斷裂的以及不深刻的,對于非遺的個體與集體記憶再認識尤為必要。記憶的個體與集體層面,“從個人角度上看,記憶是一個聚合體,產生于個人對林林總總的群體記憶的分有,從群體的角度上看,記憶是一個分配問題,是群體在其內部,即在其成員中分配的一種知識”(25)[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第29頁。。個體作為一個容納了不同團體、群體的集體記憶的場所,容納了來自不同群體的集體記憶以及個體與之每每獨特的關聯,表現出的個體與各種集體記憶之間獨特的關聯方式,個體與集體在記憶層面上相互共生。這里以非遺的個體記憶為例闡釋非遺中傳承主體的記憶。
非遺的個體記憶層面既可以作為記憶的主動激發者又可以作為被動持有者。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說:“‘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種思想。’每一個人都必須為自己辯護。”(26)[英]湯因比:《湯因比論湯因比——湯因比與厄本對話錄》,王少如、沈曉紅譯,上海:三聯書店1989 年,第180 頁。每一份個體的記憶,都是一份獨一無二的人性檔案。這份人性在非遺的每個傳承人上表現為個人生活、情感經歷、語言特性、心靈歷程、個性心理、社會關系、身心狀況乃至記憶方式等。不過并不是所有人的記憶對非遺保護與傳承同樣重要,這也是為何會選定非遺傳承人以及不同級別認定于記憶維度上的意義。它的完整而深刻的認識是對非遺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更加持久而深刻的保護與傳承,保護與傳承的方式也因個體記憶的深刻而銘刻著人本意識。
這里以萊州市縣級非遺海草房苫蓋技藝為例。海草房,是現存膠東半島的稀世民居。海草房以山東的榮成、萊州居多,整棟房屋深褐色中帶著灰白色調,墻體由青灰色的花崗巖和清水磚石壘砌而成,格子門,雕欞窗,極具地方特色。而萊州的海草房不同于榮成海草房敦厚而更加的精美,這種精美體現在做梢上。苫匠會將海草像屋山外面探出一截,披到山墻上,并將漁網蓋到上邊,屋梢與山墻連為一體,有魚鱗梢、板凳面子梢等多種樣式。屋梢與屋頂苫海草的地方留下一瓦寬的瓦溝,這樣不僅雨水能順瓦溝流下,最主要便于貓在瓦溝中走動,防止麻雀在海草邊上啄窩損壞海草(27)張景通:《海草房》,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67頁。,因此,當地人稱這種設計叫做“貓道”。再有區別體現為割檐,在苫屋前后檐上放置八九公分的小瓦,瓦頭為滴水瓦,好的苫匠苫出來的瓦與海草相接的地方如快刀割過一般,樣式美觀、適用。苫房技藝的整個過程,必需經過“捋、壓、拍、刷”四道工序,在四道工序中的操作中還要做到“實、勻、緊、平”缺一不可。所以,曾經的海草房是萊州沿海地區對家的一種記憶。可是當下,十年前連片的海草房聚落群,如今已然所剩不多。一部分或是屋主離世或是隨兒女遠居他鄉,已是人去屋空,長久的不維護屋面背陰處會生長出一層綠色苔蘚,伴有成簇的瓣尖紅色的瓦松,俗稱“山老婆指甲”,對其屋頂損毀嚴重,風雨飄搖;一部分是因為屋頂上的大葉藻(苫蓋海草房的原材料)許久未維修有些地方已經殘破,當地人在原有海草屋頂的基礎上包上幾層塑料膜繼而噴上厚厚的水泥,最后再蓋上一整塊厚厚的苫布,做了退而求其次的維護,其實這種海草房外觀已經破壞,也屬名存實亡了;還有相當一部分直接推倒重蓋為新式紅瓦房。
形成上述保護與傳承窘境的原因多種,比如,近海養殖的出現,海洋環境的變化,導致作為海草房的大葉苔、二道苔等原材料已面臨絕跡。而保護與傳承最大的困難是隨著苫草技藝后續無人,苫匠的年事已高,出現保護與傳承斷層,海草房變得岌岌可危。筆者最初拜訪在籍的兩位海草房苫蓋的苫匠,其中一位筆者去的時候已離世多年,另一位也因為年事已高,聽力退化,加之老人識字水平不高,使得無法交流。隨后,又通過多方渠道和七八個依然有海草房存在的村子進行走訪,發現目前對海草苫蓋技藝依然能完整回憶的有朱流村苫匠史經伯、張發山,河套村苫匠王家輝,海廟于家村張景通等村民。而這些老苫匠或老居民通過筆者的調研,發現雖然已離開了原有的成長環境或改造了原有的生存環境,依然能夠較為清晰地回憶起整個苫蓋的過程、要點、實用工具、禁忌、海草房的變遷以及發源地等一系列問題。這里海草房的記憶不可抗拒地被歷史所攫取,這使得人本身成為記憶的一個場所,一個隨身攜帶著非遺的“記憶包”。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往往利用參照框架來記錄和尋回回憶,當有關的非遺進行解釋時所必需的坐標不存在抑或無法符合當下需求時,隱藏在人的身體知識本身的記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個體記憶使得已經死去的遺物依然具有充滿矛盾的生命力,而這種生命力是一種夾雜著歸屬感和疏離感的情緒塑造出來的。內在呼喚著外在,精神空間的私有在某個時刻轉為相對的共有。
同樣,我們通過對傳承人個人記憶的了解,能形成一種換位思維。能讓我們保護與傳承者更多的了解到傳承人真實心理構圖。其一,實際了解后,發現這些老苫匠和老居民,相比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希冀,對現代化住房的向往與認同,遠抵消掉了世輩棲居于海草房的留念。非遺保護與傳承的大勢沒有錯,同樣誰也不能剝奪活生生的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權力,對其個人記憶的深刻認識與關切會讓保護與傳承政策與方法推行的更順暢親切、更真實全面、更落地化與更有溫度。其二,會對可以供人類繼續發展的文化基礎認識上更豐滿。英國歷史學家、哲學家西奧多·澤爾丁如是說:“我關注每一個個體,因為我意識到了人的無限多樣性,我要避免掩蓋了每個人獨一無二的特征的那種僵硬的分類法……”(28)[英]西奧多·澤爾丁:《情感的歷史》,劉庸安、賀和風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1頁。。其三,能抽離出一種崇高的榜樣,通過媒體、不同行業、領域的人不斷地去對呂村年畫第七代市級傳承人張同杰老師的采訪與調查,張同杰老人重新煥發了對自己手藝的自信心與熱情。張同杰藝人說。
你知道嗎?沒有你們這么多人不斷地來關注,我早干不下去了,你們關注我,不一定就給我錢啊,給我東西啊,你們的關注就能讓我更有干勁兒,不叫(叫意為:因為)你們,(我)早不畫了,你說我兒女都有出息,我又不缺這三瓜兒兩棗的賣畫錢,(你們對我的關注,使得)我知道國家重視,國家都重視的東西,能錯嗎?那我只要能動能行,我就畫下去,不能對不起國家的重視嘛,你說是不?(29)張同杰藝人的錄音整理。采訪人:劉智英,被訪人:張同杰,采訪時間:2018年12月18日,采訪地點:呂村張同杰家中。
這種個人記憶的關懷,對于構建文化自信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日積月累地蕩滌文化自輕的落寞心理,潛移默化地強化文化虔誠的內在結構,更大程度上強化了傳承人去細心保存本就眷戀或捍衛著那些棲居于自身的記憶。對個人記憶的關注勢頭會無形中助力榜樣的形成,而這種榜樣的抽離使得手藝人成為文化名人,自身物質和精神上都得到滿足,同樣,也會形成一種引導與風向標。這也是傳承主體為何在一定情境下是被動持有者的原由,成為記憶的促發源,手藝人關于手藝的個人記憶的內傾性因其榜樣的榮譽起到如地點、物體等紀念碑的功用,被范圍化的外傾,引導著、帶動著一批新生力量。
四、余論
綜上所述,文化記憶附著在一些客觀外化物上,而文化意義則以某些固定形式被包裹其中。非遺如果要被保護與傳承好,那么它必須具有一個具體的形式,這種形式或是具體的人,或是具體的時間或是具體的空間,而保護與傳承的效果往往與這些具體形式的含量成正相關。在記憶維度下,被經歷的時間、被喚醒的空間與傳承人(個體與集體)是非遺的指南與索引,同樣,也會為當下非遺保護與傳承提供參考。當下,保護與傳承良好的非遺,對時間、空間與傳承人記憶維度的重視,會助益、匡正、穩固甚至創新保護與傳承措施。至于,舉步維艱的非遺項目,對非遺時間、空間與傳承人記憶的關注不僅僅完成“臨終關懷”,而且可能形成一種新的傳承方式。這種新的非遺保護與傳承方式要求去記住隱藏在時間序列的行為和習慣的交往,隱藏在棲居生活的土地,隱藏在傳承無聲的物體,隱藏在集體或個體身體的知識與經驗,繼而深層次培養對時間、地方、物體與傳承主體的情感、象征、功能的覺醒與決心。最終,形成一種潤物無聲的視角來保護與傳承非遺,一種本能反射性的地方性學識。這會使得岌岌可危的非遺形成一種非常穩固的特性,甚至即使在社會和政治現實的對立面依然保存下來,成為“與現實對立的回憶”,如臨界語境中十年浩劫的文革。這些非遺時間、空間與傳承人的記憶投影于現實中標志著非遺可感知、可控制、可預見,內傾性的理解引導著保護與傳承的外傾向,意味著甄選、關切和個人對某些記憶內容的青睞。這些附加值使得對非遺的記憶成為文化記憶的一種系統的記憶鏈,形成一種秩序與規制,一個想象的記憶建筑物,一個思想的地形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