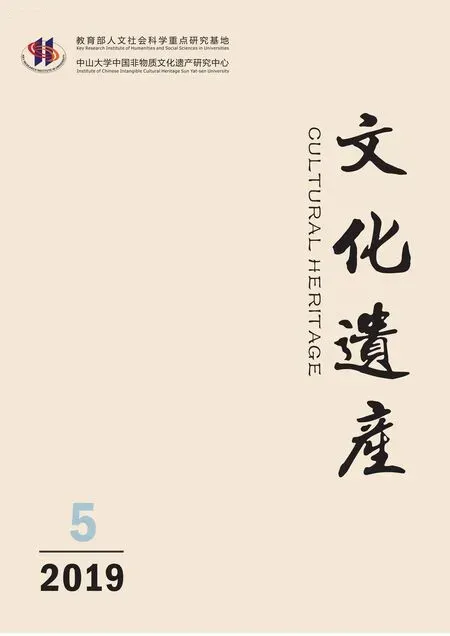“誅”“玉”與“德”:王權的神話歷史建構
——《墨子》非攻說新釋
吳玉萍
墨家創始人生活在戰國時代的戰亂之中,針對諸侯國之間以攻伐為常態的不良世風,提出一種稱作“非攻”的反戰和非暴力思想,引出后代思想史上持久的回響,至今仍然有其余波。(1)當代學者討論墨子的“非攻”多將其視為國別之間和平相處的思想來源,是一種經世致用說,如董志鐵的《“兼愛”“非攻”的理想訴求與新中國的外交路線與實踐》(載《重慶理工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李建國的《墨子的經世思想及其現代意義》(載任守景主編:《墨子研究論叢》(八),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第525-543頁。)、周磊的《和諧社會建設的墨學淵源》(載《棗莊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等文章中都宣揚了非攻對于當下和平外交、和諧建國的重要性。
需要辨析的是,墨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反對一切武力攻伐,而是反對濫用武力的現象。判斷是否濫用武力,就看是否符合“義”的原則。這樣的一種區分正義之戰和不義戰爭的情況,本是我國第一部編年史《春秋》的“大義”所在,即使在今日的聯合國大會上依然能夠看到相關國家之間在激烈辯論。所不同的是,今天裁斷是否正義,有國際法和日內瓦公約一類的公認文書在。墨子的時代要判斷戰爭是“義”還是“不義”,并沒有一部世人所公認的法律文書,只有訴諸于大家公認的一種神話信仰資源——神圣天命的原則。這種神圣天命原則,就是來自君權神授的政治神話,通常表現為王權、國家神話。
在周代以來的文獻中,華夏國家建構其政治文化的正統系譜,一般都習慣用虞夏商周四代(有時合成“虞夏”為一代,則虞夏商周為三代)的圣王歷史來說明為什么改朝換代的武力攻伐不能算是犯上作亂,而是合法的替天行道舉動,稱“誅”而不稱“弒”。比如有關周武王伐紂一事,算不算以下犯上的“弒君”之罪呢?《孟子·梁惠王下》說得非常明確:“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2)(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680頁。同一個事件,用“誅”這個詞表示,殺伐便是完全合法的,因為是代表天意和天命的;用“弒”這個詞表示,殺伐君主便是彌天大罪。用《墨子》的非攻論話語來表達,那就變成了另一種說法:稱“誅”不稱“弒”或“殺”,如同天或鬼神本身執行“誅”一樣(3)如《明鬼下第三十一》中的“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殺、至若此其憯遫也”;《魯問第四十九》中的“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亓不至乎?”“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等。。墨子的這種“誅”為“殺”用,不但突出了其非攻論的合理性,也將不屬于殺伐的正義戰爭同殺伐區別清楚了,而且墨子將正義戰爭稱為“誅”,這一點他與儒家完全一致,區別僅在于墨子是為了宣揚義,孔子則是為了宣揚仁。
一、從“誅”到“非攻”的神話歷史建構
《非攻》篇記述的墨子反駁好攻伐之君的原話,共計三段:第一段講夏禹誅三苗;第二段講商湯誅夏桀;第三段講周武王誅殷紂王。
第一段:夏禹誅三苗。
今遝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于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巳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4)(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閑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45-147頁。本文所引《墨子》原文皆出自此版本,后文所引僅標注篇目、頁碼,省去出版社及出版年月。
在這段話中,墨子先用了一系列的反常現象來說明三苗的失德與失序,相反他為了增添禹征有苗的合法性,則派用了一系列的象征神權的神話符號為其保駕護航。首先是高陽命玄宮。高陽何許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5)(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4頁。司馬遷筆下的高陽是一個有高德的人,是一個四方都聽命于他的圣人。而關于高陽的出生,還有更為神話的一說,《搜神記》卷十四:“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之于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四手足,是為蒙雙氏。”(6)(晉)干寶編著,馬銀琴、周廣榮譯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50頁。可見高陽本身就是一個神話人物。既然高陽是一個有圣德的神君,他與禹同受天命,那就是君權神授的典型。
其次便是大禹親握的“天之瑞令”。瑞,《說文》云:“以玉為信也”,作為神權最高最好的象征物,玉的神圣性不言而喻。從紅山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齊家文化等文化期的用玉,到商周的“六器”(7)《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62頁。,再到秦始皇象征最高權力的玉璽,以玉禮神的傳統從未斷裂,玉成為宗教中溝通人神的重要媒介。再以文獻記載為例,《說文解字》“玉”部就有125個之多;《詩經》中除了單獨的“玉”之外,還有“硅”“璧”“璋”“瓏”“璐”“瑤”“瑰”等一大批跟玉有關的文字符號;《山海經》中大量的產玉之山、食玉膏的出現等,種種現象都表明了玉的無上神圣性。除了象征神權賦予的圣物,神明的伴隨也彰顯了大禹誅有苗的合法性。如下文的“人面鳥身”神。人面鳥身神即為東方的句芒,而他“若瑾以侍”即為拿著另一個圣物“珪”伴隨左右,“若瑾”疑為“奉珪”之誤(8)此處解釋詳參《墨子·非攻下》,第146頁。。珪,玉器的一種。《類篇·玉部》中解釋:“珪,瑞玉也”,同樣也象征著神圣性的王權。神人加圣物,使得禹即將伐有苗的行為不僅合法,而且承載著天命,更顯神圣。在大禹戰勝有苗之后,墨子還特意用了一段文字同有苗掌權時的國家狀況進行對比,四時合調、民神和諧的畫面給“誅”的正義性增加了說服力。
第二段:商湯誅夏桀。
遝至乎夏王桀,天有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谷焦死,鬼呼國,鸖鳴十夕余。天乃命湯于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閑西北之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9)《墨子·非攻下》,第147-149頁。
在這段話中,墨子用了同樣的手法。首先用反常的現象表明夏桀的殘暴,而為了增添商湯誅夏桀的合法性,將商湯的行為說成是“受天之命”,這就為這場戰爭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礎。同大禹伐有苗一樣,商湯誅桀同樣有神庇佑,而且還為他打了頭陣。護湯的神靈即為祝融。祝融,傳說中的火神,《呂氏春秋·審分覽·勿躬》載:“祝融,神名。帝嚳時的火官,后尊為火神,命為祝融。”商湯滅夏桀成功后,墨子同樣用了一段對比性文字來說明商的合法性。
第三段:周武王誅殷紂王。
遝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10)《墨子·非攻下》,第147-149頁。
周武王誅殷紂王是墨子著墨最多的一場戰爭,其動用的神話母題也是最多的。開始敘述之前,如出一轍,墨子用大量的筆墨來凸顯商王紂的暴虐所帶來的宇宙失序和民生凋敝,即便妖鬼也感受到了紂的荒唐和野蠻。說完非正常現象后,墨子借用神話因子來證明周文王誅殷的合法性。一開始,墨子用了“銜珪”的“赤烏”來告知周文王天命其伐殷國,這就為周文王誅紂定下了合理合法的基調。對于這里的“赤烏銜珪”,《墨子閑詁》中的解釋是:
畢云:“烏,《太平御覽》引作‘雀’。‘珪’,初學記引作‘書’”。詒讓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尚書中候》云:“周文王為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王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宋書·符瑞志》同。《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云云,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丹書文同,與此異。以上諸書,並作銜書,與《初學記》同。《呂氏春秋·應同篇》云“文王之時,赤烏銜丹書,集之周社”,亦與此書“降岐社”事同,疑皆一事,而傳聞緣飾不免詭異耳。(11)(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閑詁》,第150-151頁。
據經學家們考證,降在岐社的赤烏銜的是丹書,而墨子卻將其改為“珪”。“珪”在前文夏禹誅三苗中已經有出現,是一種顯圣物,墨子棄書用珪,無疑是想說明赤烏是帶著天的神圣的旨意來的,它所說的話也是上天的意思,這就是“受命于天”。隨著銜珪赤烏的到來,周文王的受命于天儀式順利完成。接下來便是一系列的祥瑞之兆。首先是泰顛來賓,即久不入世的太公亦來為文王出謀劃策;其次是河出綠圖。綠圖經常跟洛書并稱,《易·系辭傳》里說:“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這里的圣人就是伏羲,這使得書和圖更具有了神性。《禮緯·含文嘉》中說:“伏羲德洽天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淮南子·俶真訓》中也說:“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可見綠圖是一個極好的象征,能變相告訴世人周文王將是一個至德之人,他治理國家必將繁榮興盛。最后是地出乘黃。同河出綠圖一樣,地出乘黃也是將有圣君出現的預兆。如《宋書·符瑞志》中說:“帝舜即位,地出乘黃之馬”;劉賡的《稽瑞》引《孫氏瑞應圖》也記載了“王者德御四方,車服有度,秣馬不過所乘,則地出乘黃”。除了祥瑞之兆外,武王在攻伐之時,天還賜了“黃鳥之旗”,黃色乃帝王所用之色,完全符合受命于天的神話敘事。文王誅紂后,一派盛象,天下歸心。
以上三場戰前戰后的分析讓我們看出,墨子借用了一系列的神話母題論說了戰爭的合理性,成功論證了“若以此三圣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的命題。墨子對夏禹誅三苗、商湯誅夏桀以及周武王誅殷紂王的敘述,政治傾向性很明確,完全是一次類似于洪水亂災之后的撥亂反正行為。需要追問的是:墨子講述此事是原創還是因襲?如果是因襲,那么墨子對于事件的敘述有沒有刪減,或者說有無增加神話成分?如果有的話,那么墨子這種“再創作”的特色,就是一種墨家建構,完全符合神話歷史建構的特點。
首先是大禹誅三苗,較為詳盡的是《書·大禹謨》中的記載: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勛。”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栗,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12)(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37頁。——《書·大禹謨》
除此之外,《韓非子·五蠹第四十九》、《太平御覽》卷四引《金匱》等典籍均記載了三苗的失德以及禹跟三苗之間的戰爭,我們可以看出墨子的敘述增添了很多神話因素。首先是渲染有苗氏掌權時的天地混亂、四時失調;其次是動用神人和圣物來說明大禹行為的合法與神圣性。相反,其他典籍中記載的最多的是關于“德”的問題,即大禹有德,三苗失德,這是影響戰爭勝利甚至是否開展戰爭的前提,德行豐厚,甚至能不戰而勝。
其次是商湯誅夏桀。同大禹誅三苗一樣,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則詳實地記載了商湯誅夏桀的整個過程:
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女眾庶,來,女悉聽朕言。匪臺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于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于有娀之虛,桀奔于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嵏,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于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13)(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24-125頁。
此外,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也簡單概括了湯滅夏桀一事。不過司馬氏的“秉筆直書”跟墨子所言完全不一,并未有如《墨子》文本中諸多神話母體的加入,但也突出強調了德的重要性。
最后是周武王誅殷紂王。《史記·周本紀》對于戰爭的描述頗為詳盡: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14)(漢)司馬遷:《史記》,第157-162頁。
武王伐紂中最有名的便是牧野之戰,除《史記》外,《逸周書》也有比較全面的記載,雖然這兩本史書中沒有墨子提到的那些神話,但是也強調了兩點,一是德,二是受命于天。值得注意的是,周武王在滅商紂王時,商紂王的周身焚玉值得關注。《逸周書》中說“商王紂取天智玉琰,身厚以自焚”;(15)黃懷信等撰:《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73頁。《史記》中說“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不僅商紂王臨死不忘攜玉,即便周武王也是對寶玉情有獨鐘:“武王乃裨于千人求之,四千庶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這里隱約可見玉與王權、玉與德、德與受命于天等都有著神秘的聯系。這里留待后文詳析。
通過以上不同文本對夏商周三代最著名的三次攻伐歷史事件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墨子論說其非攻思想時,對歷史記載進行了取舍,通過神話性的再創作,使之成為體現天命神話的正義戰爭代表。那么,究竟司馬遷這些人所記載的歷史是不是就是真正的歷史呢?顧頡剛在《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自序一中說到:“只有司馬遷和崔述,他們考信于《六藝》;凡《六藝》所沒有的,他們都付之不聞不問。這確是一個簡便的對付方法。但《六藝》以外的東西并不曾因他們的不聞不問而失其存在,既經有了這些東西,難道研究歷史的人可以閉了眼睛不看嗎?況且就是《六藝》里的材料也何嘗都是信史,它哪里可以做一個審查史料的精密的標準呢?所以他們的不信百家之言而信《六藝》,乃是打破了大范圍的偶像而崇奉小范圍的偶像,打破了小勢力的偶像而崇奉大勢力的偶像,只掙得‘以五十步笑百步’的資格罷了。”(16)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自序一》,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頁。可見,司馬遷的創作也未必就是完全遵照歷史原目,只能是接近歷史,也屬于一種神話歷史。只是跟墨子的神話性再創作相比,墨子建構的歷史要更為神話化了。
綜述之,在書寫歷史的體制內,沒有真正的歷史存在,有的只是神話歷史般的建構。這就需要我們在重讀經典時,必須以神話歷史的眼光切入,只有這樣,才能讀出作者創作文本的真意和要意。
二、玉、德與受命于天
墨子通過夏商周三代三大戰役的神話性再創作,完成了對“誅”的神話歷史建構,在墨子的建構之中,他用到了諸多神話母體,而所有的神話母體又都說明了一個問題,即攻伐是受命于天的行為。能受命于天的前提是“務德”“有德”,一旦德行夠厚,不動干戈,都能戰勝,如禹“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強調德的重要性,這跟司馬遷等人記載的又有了吻合。
德作為一個關鍵詞,先秦諸子均有過闡述,如莊子“在為他的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命名時都曾用‘德’這一概念”,“單獨使用的‘德’字更多達140多處,與‘道’連言的‘道德’一詞在外雜篇共出現了16次”。(17)葉舒憲:《莊子的文化解析》,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24-625頁。老子的《道德經》更不用說,書的名字就含有“德”,“《道德經》中‘德’出現了30多次,‘道’則有60次。這種一比二的比例也大致保持在《莊子》中”。(18)葉舒憲:《莊子的文化解析》,第624-625頁。孔子更是將“德”跟“仁”并舉,視為最核心的理念之一。
那么墨子提倡德跟儒道兩家是否一樣呢?他的“德”內核是什么?先看看《墨子》文本中提到的“德”:
“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大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溪陜者速涸,逝淺者速竭,磽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19)《墨子·親士》,第6-7頁。
“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20)《墨子·法儀》,第22頁。
“故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宮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21)《墨子·尚賢上》,第46-47頁。
“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為馬然。’”(22)《墨子·非攻下》,第154頁。
很明顯,墨子口中所謂的“德”是圣人的一種品質,只有擁有這種品質才能夠威懾四方,統治天下。這樣看來墨子的“德”跟儒家有接近的一面,即行德是得天下的不二法寶。“‘德’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概念,是同倫理道德與政治密不可分的,其對于今天的影響仍在。法治和德治屬于制度體系的不同層面,二者并行不悖,這是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但從字源上看,‘德’字的甲骨文字形最初就是表示行得正,那么有德的人就是受命于天的。”(23)葉舒憲:《圖說中華文明發生史》,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5年,第303頁。除了字源學上的依據,“在青銅器銘文中,被世襲傳遞的‘德’的總根源來自上帝,即‘天’。……如劉華夏與其他一些學者已經觀察到的那樣,‘命’也載有‘先天稟賦的德性’之意,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德’與‘命’常常通用。更明白地說,在西周早期銘文中,周王從先祖繼承下來的由上帝或天降臨的‘正德’,已經變形為‘天命’。”(24)[美]艾蘭:《水之道與德之端:中國早期哲學思想的本喻》,張海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23頁。然有德之人雖是受命于天,但要讓人去相信君權是神授的,要想使君權合法且長久,還必須有“受命”的儀式,即通神的媒介和象征神權的圣物做支撐,這樣才能構成一整套的君權神授的神話敘事。恰如《墨子》中夏商周三次戰役中,大禹、商湯、周武王都是有德之人,然而光有德還不行,要使戰爭更加合理,必須加入“受命于天”的儀式,否則即便如“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的回答仍是:“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墨子在構建的關于三次戰役的神話歷史中,提到了天受命的途徑,夏禹誅三苗中是“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商湯誅夏桀中是“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閑西北之隅’”;周武王誅殷紂王中是“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由此可見,天命的傳達離不開神人、圣物、神獸(鳥),具體到上述三戰中傳達天命的就是句芒、祝融、赤烏、瑞、瑾、珪。
以神人傳達天命、授予神意,這很容易理解,因為神人是天的使者。而神獸同樣具有通神的作用。從《墨子》中武王誅紂時的“赤烏銜珪”到《詩經·商頌》中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再有“鳳鳴岐山”“飛熊入夢”等,所有這些神話母題中都是由神獸充當天命的使者、通神的媒介。(25)關于神獸作為天命使者的文章,詳參葉舒憲《圖說中華文明發生史》第十章《鳳鳴岐山》,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5年,第272-316頁。墨子在《非攻》中所述夏商周三代神話歷史依據,講到的這種天命傳達到人間的方式,其實中國民間今天還繼續著這樣領受天命和神意的傳統,只不過形式上有所改變或者說傳達的媒介有了更改,神人不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專門的神職人員,代表天命的玉器也被神職人員手中的法器所取代。
以臺灣為例,臺灣的原住民沒有文字,然而他的歷史并未就此中斷或消失,因為有著特殊職業群體的存在,那就是口傳史官,他們不僅有著一定的知識,而且還能溝通神靈,這就使得他們的敘事離不開神話,所言即為神意。“在原始部族中,掌握歷史知識的人,往往需要具備一定的神圣性,能與天地精靈溝通,傳頌祖先的故事。因此,口傳歷史中‘史官制度’圍繞著原住民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他們代表了一個部落文化精華的累積與醞釀,更是與自然溝通時重要的中介。”(26)康德民:《原住民口傳史官制度》,葉舒憲、陳器文主編《寶島諸神:臺灣的神話歷史古層》,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年,第59頁。在臺灣,除了口傳史官有這樣的神能外,還有一種神明的代言人,那就是童乩。“童乩是在臺灣的民間信仰中,最通俗的靈媒者,乃‘神靈附體,代宣神諭者。其本質為薩滿(Shaman)’,主要扮演神人溝通的橋梁,可代表神明直接與人對話,但也有須透過桌頭翻譯者,從問病、解運到請火、祈安,無所不能。”(27)劉還月:《臺灣民間信仰小百科·靈媒卷》,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第85頁。應當說,童乩比口傳史官更為直接,因為有神靈直接附體,童乩所言就是神在說話。
除了臺灣,大陸的漢民族和少數民族中也都有這種神職人員的存在。漢民族有一種風俗,即為死去的人“關房”,也就是問死者在地下的境況。通常會由女性承擔此神職。筆者曾親身經歷過此儀式。整個過程很簡單,開始該女性躺在床上,過了一段時間后,被詢問的死者開始附體,然后開始說話,一旦在地下過得不好的,上來先是一頓痛哭,訴說自己在下面如何如何遭罪,然后讓生者為其蓋紙坊、燒紙錢。通常生者會質疑一下這個死者代言人是不是靈驗,測試的方式就是問附體的人子孫的姓名、有幾個孩子等問題,如果回答得對,那便是靈驗的。少數民族中此類中介者更多,如彝族的臘摩、珞巴族的米劑等。
上述神人、神獸的使者身份很容易理解,需要解釋的是玉與德以及圣王(人)有何關系?象征天命的圣物為何是玉?關于玉與德之間聯系,典籍中記載很多:
“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解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忮,潔之方也。”(28)桂馥:《說文解字注》,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第12頁。(許慎《說文解字》)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踐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29)(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694頁。(《禮記·聘義》)
“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30)(清)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815頁。(《管子·水地》)
如上所述,玉很明顯就是德的物化形態。“需要明確的是,‘德’原本不是屬于人的,而是來自天的。只有深入領會到古人講的‘天’是神話觀念,方能夠舉一反三,意識到‘天命’‘天子’‘天德’等無一不是神話思維傳統的派生觀念。”(31)葉舒憲:《圖說中華文明發生史》,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5年,第306頁。如此看來,德、天、玉三者的關系變得明朗起來,德來自于天,德的物化形態是玉,那么玉就成了天的象征物,也是天命的具象化符號。因此墨子在構建三次戰役的神話歷史時會大量派用玉禮器來象征天命的神圣。而這也為“巫以玉事神”、史前文化中的唯玉為葬、獻祭儀式中“六器”等古老命題找到了解釋源頭。玉是通天通神的圣物,只有圣物才能用來事神,而且玉既然能夠通神那便能幫助死者升天,所以作為禮器出現在祭祀等儀式中就不足為怪。
玉與德、天命、神權之間的關系表明玉崇拜在華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玉崇拜在中國甚至可以稱為“玉教”。(32)詳參葉舒憲:《玉教——中國的國教》,《世界漢學》2012年第1期。然而玉崇拜不光是文獻中有證明,來自考古學的第四重證據也能提供說明。以距今4000年左右的龍山文化為例。“制玉技術的繁榮和提高是龍山文化手工業的又一突出成就。其中以西朱封墓地出土的玉器最具代表性,一組精美的玉頭(冠)飾,分別由鏤孔鑲嵌綠松石的玉牌和玉桿兩部分組成,通長23厘米,其精美程度,為龍山文化所僅見。與玉冠飾同出的還有玉鉞、四孔玉刀和玉簪等。日照兩城鎮遺址發現1件雙面刻有纖細獸面紋圖案的玉圭,玉質呈墨綠色,通體磨光,長17.8厘米,厚0.6—0.85厘米,如此精制玉器顯然已非實用器,而應成為禮器。此外在其他遺址中也出土有玉器,主要種類包括鉞、牙壁、小型聯壁、鳥、鐲、鏃形器等。其中丹土、兩城鎮、三里河等遺址發現的相對較集中。龍山文化目前雖然出土的玉器總量不很多,但從中反映出的工藝水平卻相當之高。當時的玉器工匠已經能夠通過對玉料的切割、磨制、雕刻和鉆孔等技術來加工出工藝復雜的玉制品,其制玉技術已經相當發達和成熟。”(3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605-607頁。圖片取自本書607頁圖6-42.(如下圖1所示)
同屬龍山文化、距今約4500年之久的陶寺遺址中,其挖出的墓葬使用的大量玉器也象征著墓主的權勢與身份,尤其是2002年挖掘出的M22,“墓主尸骨上殘留有綠松石片、綠松石珠、貨貝等46件隨葬品。棺外還有隨葬品72件(套),其中彩繪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漆木器25件(不包括6件玉石鉞的漆木柄)、骨鏃8組、紅彩草編物2件、一劈兩半的豬20扇(即10頭豬),豬下頜骨1件等。”(3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第573頁。除了龍山文化以外,紅山文化、良渚文化、二里頭文化等,這些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先民們用他們的智慧和工藝向我們再現了玉崇拜的深遠脈絡。
綜上所述,玉、德、受命于天三者的關系經過多重證據的證明,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得到了呈現。如果用編碼理論分析,先秦典籍中的玉與德或者玉與天命的記載,如墨子的“禹親把天之瑞令”;孔子的“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和“君子必佩玉”;老子的“圣人被褐懷玉”以及孟子的“金聲而玉振之”等,當屬文化傳統的三級編碼,一級編碼則是由出土玉禮器顯出的玉崇拜。這樣看來,不管儒墨之間有多大的思想差異,墨子和孔子,在某種層面上講,分享著共同的信仰之根,即文化大傳統中對于玉的圣化與神化。
結語
墨子為了宣揚夏商周三次改朝換代的攻伐是正義之戰,在歷史敘事中增加了神話母題,所有的神話母體又都說明了一個問題,即攻伐是受命于天的行為。受命于天的前提是“務德”、“有德”,因此墨子又強調“德”,認為有德的人是承接天命的首要條件。為了將天命傳達到人間,他建構了一個神靈、圣物、神獸作為天人溝通的媒介物,攜象征天命的顯圣物玉瑾、玉圭、玉瑞等,通過天命神、神攜物、物賜人這三個環節,順利完成了由天命傳達的整套儀式,于此也建構出了“誅”的神話歷史。從“誅”到“非攻”,神話鑄就了墨子成為宣揚正義的不朽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