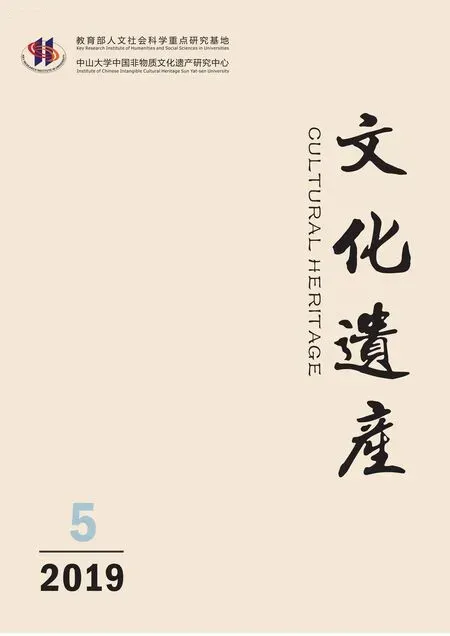“越人好事因成俗”:廣州蒲澗節(鄭仙誕)傳統民俗活動源流述論*
趙曉濤
一、引言
廣州市白云山舊有著名景點“蒲澗濂泉”, 唐宋以來即成為一方旅游勝地,騷人墨客留下諸多吟詠作品。因安期生飛升成仙傳說產生于該地,故附近一帶建有菖蒲觀、鄭仙祠等祭祀場所。廣州蒲澗節(鄭仙誕)傳統民俗活動,正是以安期生(在后世被稱為鄭仙)于白云山蒲澗飛升成仙這一歷經千年的傳說為核心因子發展衍變而來(1)烏丙安:《中國民間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5-222頁。。
白云山風景區管理局近年以鄭仙傳說為由頭,再造消失多年的“鄭仙誕”(蒲澗節)這一地方傳統民俗活動,引發輿論報道和學界關注。然而對于這一民俗活動存在的諸多歷史問題,一直以來缺乏比較全面深入的梳理考證。
就筆者目前所見,學界關于鄭仙誕(蒲澗節)的研究成果,僅有徐燕琳《從鄭仙誕到廣州重陽登高——兼談傳統民俗的現代化演變》一文(2)徐燕琳:《從鄭仙誕到廣州重陽登高——兼談傳統民俗的現代化演變》,《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該文對鄭仙誕的來歷及演變作了較為簡略的梳理,將廣州傳統的鄭仙誕(白云誕)節俗到重陽登白云山,視為傳統民俗現代化演變過程中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例,指出這個融合、轉變的事例過程是民俗活動與社會經濟文化密切關系的反映。由于該文的落腳點是放在傳統民俗的現代化演變上,因此對鄭仙誕源流的梳理考辨尚不夠全面深入。此外,朱鋼《“安期生”考》、紀宗安等《安期生在白云山蹤跡的辨析》(3)朱鋼:《“安期生”考》,《文化遺產》2008年第1期;紀宗安、王紹增:《安期生在白云山蹤跡的辨析》,《嶺南文史》1995第1期。等文,借助文獻資料和口頭傳說,對安期生其人其事作了梳理辨析,其中朱文相對更加深入細致,并在辨析安期生與鄭安期的區別過程中引述了一些記載蒲澗節(鄭仙誕)的文獻材料以作為證據,但亦未對蒲澗節(鄭仙誕)源流作全面深入的梳理考辨。本文即著力于對這一廣州地方傳統民俗活動之形成及其流變作全面深入的梳理考察。
從目前存世的文獻記載來看,廣州蒲澗節會在兩宋之前缺乏明確記載,目前僅能綜合《廣東考古輯要》輯南朝宋沈懷遠撰《南越志》“菖蒲澗,昔交州刺史陸允之所開也。澗中多九節菖蒲,世傳安期生采菖蒲服食之,以七月二十五日于此上升。郡人每歲是日往澗中沐浴,以祈霞舉”,和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七引《南越志》“(東晉)太元中,襄陽羅支累石澗側,容百許人坐,游之者以為洗心之域”兩處記載來判定:在東晉太元年間至南朝宋前期即有蒲澗節會之雛形,其時主要限于當地民眾自發產生的祈求長生不死、祛病除疫的民間信仰表達形態。限于相關文獻記載的缺失,此后直至隋唐五代蒲澗節會情況無法獲知,實為一大憾事。而根據現有各種文獻材料,蒲澗節會從價值觀念、行為習慣到儀式制度之三位一體正式形成要到宋代。
二、蒲澗節在宋代之正式形成
南宋人洪適在《張運知廣州制》一文中指出:“二廣之區,五羊最大,藥洲蒲澗,民有嬉游之風”(4)《盤洲文集》卷二二,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第7頁。。方信孺《南海百詠·菖蒲觀覺真寺》“千載仙居已渺茫,道山佛屋自相望。春花秋草年年事,卻作游人歌舞場”,以及劉克莊《蒲澗寺》“欲采菖蒲無覓處,且隨簫鼓樂新年”等詩句可為蒲澗之地“民有嬉游之風”的佐證。葛長庚(白玉蟾)詞句“年年蒲澗會”(《霜天曉角·綠凈堂》)指明這一長盛不衰的地方民俗事象,是廣州城除五羊傳說的悠久、阛阓十萬人家的繁華等地域特征外,值得夸揚于世的一點者。
宋代廣州官吏民眾有一年兩次游蒲澗的習俗:農歷正月二十五為蒲澗節;七月二十五為安期生飛升日(后稱鄭仙誕)。方信孺《南海百詠·菖蒲觀覺真寺》詩前小序“郡人歲以正月之二十五日為蒲澗節,帥使而下傾城來游”,小序并引《南征錄》“正月二十五日乃劉王生日,七月二十五日乃安期上升”(5)按:小序所引《南征錄》一書已佚,且不知作者何人,所提“劉王”和方氏《南海百詠·劉王花塢》當為五代十國時期南漢之同一國主,限于相關史料文獻線索缺失,無法判定出是哪位國主,存疑待考。。經查尋,可知宋代曾為官嶺南的外來文人士大夫,從個人切身體驗出發對春秋兩季的蒲澗節各有詩(詞)書寫(今存作品中書寫春季蒲澗節的相對較多),為后世留下了一批珍貴生動的歷史記錄。
關于初春的蒲澗節,從北宋時期蔣之奇《蒲澗》、郭祥正《蒲澗奉呈蔣帥待制》,至南宋時期洪適《番禺調笑·蒲澗》、楊萬里《和鞏釆若游蒲澗》、趙汝鐩《續蒲澗行》等文學作品皆有程度不一的生動描繪。關于秋季的蒲澗節,則僅存南宋時期如曾豐《七月二十五日為廣州蒲澗節鞏帥相招坐上默營兩詩》、楊萬里《游蒲澗呈周帥蔡漕張舶》、蔡戡《和楊廷秀游蒲澗之什》、劉克莊《水調歌頭·又題蒲澗寺》等文學作品有書寫,另如劉克莊的詩句“俗情重蒲飲”(《即事十首》其三)高度概括了當時本地民眾看重采菖蒲造酒飲用這一民俗活動(6)據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三“白云山”條記載秋季蒲澗節:“宋時郡守嘗醵士大夫往游,謂之鰲頭會云。”按“鰲頭”一作“遨頭”,此處指廣州本地最高軍政長官知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當源于“獨占鰲頭”之義,宋人常以姓字冠于“帥”字前作為某位廣州知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的省稱。而從宋代秋季的蒲澗節又被稱作“鰲頭會”來看,足以認定宋代廣州蒲澗節會雖以民眾為參與主體,卻有地方主官帶領僚從與民同樂這層比較濃厚的官方色彩(宋人有與劉克莊《水調歌頭·又題蒲澗寺》“斫鯨鲙,脯麟肉。越人好事因成俗。擁遨頭如云士女,山南山北”類似的成都等地官民游樂情形記載,限于篇幅,茲不具引)。。限于本文篇幅,以上文學作品玆不具引,詳細分析請見筆者相關文章(7)紀德君、曾大興主編:《廣府文化》第四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258-269頁。。
綜合分析這些有關的文學作品,可見當時該地民眾物質生活較為富足,嬉游娛樂等精神生活好尚亦較為普遍,社會呈現較為安適狀態。亦可印證自北宋慶歷以還,宋代士大夫在詩文中創造的開放而富有人情味的共樂境界,“突破了唐人亭臺詩文呈現的幽賞自適的狹小視野,使文士游賞之趣和地方官愛民之志在眾樂層面得到統一”,“對‘眾樂’的追尋將山林之趣與民庶之樂融而為一,匯成博大鬧熱的審美新質。此中樂境與傳統的避世之樂不同,無疑有著‘樂在社會、合乎人倫的世俗性、現實性’(程杰《詩可以樂———北宋詩文革新中‘樂’主題的發展》)”(8)王啟瑋:《論北宋慶歷士大夫詩文中的“眾樂”書寫》,《文學遺產》2017年第3期。另按:此段引文中所引程杰一文,參見《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以致無論郭祥正、洪適、楊萬里、趙汝鐩、方信孺,都以文學作品特別是以“傾城”一詞來形容蒲澗節官民共樂之盛大場面,充分體現出當時蒲澗節民“規”官“隨”之獨特耦合關系。
三、宋代之后蒲澗節的傳承流變
宋代之后,蒲澗節會代代相傳(值得注意的是,正月二十五的初春蒲澗節在宋代后突然消逝不傳,個中原因尚待考索),限于筆者見聞,未見元代文獻對蒲澗節作明確記載(9)按:據《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卷之十九)中法令規定漢人、南人不得聚眾田獵和迎神賽會,元人完顏納丹纂《通制條格》卷二七“供神軍器”條記載元代民間各廟宇中供神用的鞭、筒、槍、刀、弓箭、鑼鼓等物也均在被禁用之列,則不排除蒲澗節活動在元代有中斷舉辦之可能。,到明代蒲澗節未見有新的記載。
進入清代,嶺南文化強勢崛起,有關蒲澗節(鄭仙誕)的文獻記載比宋代更為多樣,內容更為詳實,且不同于宋代的是記載者主要為廣府本地文人士大夫。在其他神誕名目的影響下,“鄭仙誕”這一指稱約定俗成,正式取代蒲澗節(鰲頭會)指稱,并沿用至今。
清代蒲澗節(鄭仙誕)除延續千年一直存在的核心儀式內容,其民間信仰的內涵更加豐富,民俗活動的色彩更加濃烈,特別是祭拜與娛樂的結合更加緊密,并形成兼具累積沉淀型和合流變形型的類型特點。
1.鄭仙誕民俗活動在傳承演變中的累積沉淀與合流變形
清中葉番禺陳夢照《游白云山記》記敘自己于壬申(按:嘉慶十七年即1812年)孟秋中旬十六,攜弟從師游白云山的經歷,“(倚山)樓側為安期巖,傳為安期生嘗修煉于此。……自初旬以來,求福者無窮,男婦老幼雜沓而來,山林中有塵囂象矣”,“亭午往安期巖求福者益眾,人唱馬嘶”(10)(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陳建華主編《廣州大典》據清光緒十七年上海著易堂鉛印本影印,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213冊,第33頁。。鐘啟韶《七月二十日夜寄緗庭》:“年年七月賽安期,蒲澗濂泉恣流眄……大兒昨日看山回,……艷說今年盛游屐,畫榼籃輿雜朝晚”(11)(清)鐘啟韶:《聽鐘樓詩鈔》卷四,《廣州大典》據清道光十年刻本影印,第450冊,第576頁。,可見蒲澗節臨近前,上白云山的游人已是人頭洶涌,節日氛圍可謂呼之欲出。
此外,如清人崔弼、陳際清《白云越秀二山合志》卷三十七《志仙釋》謂:“安期之巖,每歲七月二十四日,香煙載道,裙屐滿山。而蕭岡、塘下諸鄉,畫龍虎之旗,載犀兕之鼓,千百人香案在前,乘馬在后,扮彩色以相隨,舁仙輿而疾走。絲竹之聲,與溪聲競作;沉檀之煙,與云煙并湊。以視驪山之宮,其相去又何如也”,并感嘆“嗟乎盛哉,今人稱此會為鄭仙誕,實踵宋時鰲頭會云”,可見當時的鄭仙誕已發展成為有抬神巡游活動的神誕(即民間所稱“出會”或“會景”)。 借用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公共場所的行為:聚會的社會組織》中提出的公共場所和半公共場所有關行為理論(12)[美]歐文·戈夫曼:《公共場所的行為:聚會的社會組織》,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0頁、第25頁、第83頁。,鄭仙誕這種神誕活動發生于公共場所和半公共場所,參與者之間無疑是“有焦點的互動”,而鄭仙便是人際互動的“焦點”,其獨特標識意義更加突顯。
同書卷二《志山》“安期巖”條下記載“每年七月二十五日飛升之辰,游人千百為群,茶亭酒館隘塞山中。自七夕后,籖冊、珓桮、檀煙、蕭焰,壹郁巖際。山間熱鬧,他處所無”(13)(清)崔弼、陳際清:《白云越秀二山合志》,《廣州大典》據清道光二十九年樓西別墅刻本影印,第222冊,第263頁、第32頁。。此種形、聲、色、味具足之熱鬧場景,可謂“民眾借神靈的名義來達到娛神和自娛的雙重目的”,“神誕成了廣州民眾名副其實的狂歡節”(14)楊秋:《近代廣州風尚習俗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65頁。,那些初來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將廣州這類民間祭祀活動稱作“最張揚的集體表演”(15)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62頁。。據此,可見當時廣州地方民俗具有公共參與性與儀式表演性,和自宋代以來廣州民間社會旺盛的活力及文化創造力。
素有清后期嶺南風土百科全書之稱的《嶺南雜事詩鈔》,其中即收錄有作者陳坤《游白云》七絕一首:“西風吹入白云秋,蒲澗尋仙作勝游。一事教人忘不得,在山泉水最清流”,后有陳坤自注:“廣州相傳,安期生以七月二十五日升仙,屆時士女多為蒲澗之游。蒲澗在白云山下,泉味清冽,游人必汲以煎茶”(16)(清)陳坤著、吳永章箋證:《嶺南雜事詩鈔箋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9頁。另按:清道光《廣東通志·風俗》卷九五有記載與陳坤自注相似。,大埔鐘兆霖《廣州竹枝詞》:“清宵賭酒白云陲,七月天涼月出遲。九節菖蒲儂采得,焚香膜拜鄭仙祠”(17)何文廣:《廣州竹枝詞選》,《嶺南文史》1983年第3期。,則可見其時鄭仙誕除采蒲、進香習俗,一般廣府民眾對于煎茶、賭酒可謂各有所愛。光緒初年番禺林象鑾《羊城竹枝詞》(其四)“鄭仙昨日進神香,水汲葫蘆滌不祥。香欖松貓干豆腐,白云風物贈街坊”(18)龔伯洪:《廣州古今竹枝詞精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4頁。,當時鄭仙誕期間廣府民眾遵循給鄭仙進香,用葫蘆汲水來滌除身上的“不祥”,將香欖、松貓、干豆腐這些“白云風物”分贈街坊四鄰的習俗。
至于光緒年間布衣南海人梁綺石《羊城竹枝詞》:“鄭仙遺跡鶴舒臺,貴第人家簇簇來。虔備迦南香禮佛,暗中祈子占高魁”(19)《廣州竹枝詞選》,《嶺南文史》1983年第3期。,則就連祈求科舉考試中得高第,也成為廣府鄭仙誕民間信仰之新增內容,而非如古時漢人各地一般流行的禮拜文昌帝君風氣,鄭仙誕民間信仰在廣府本地之“獨領風騷”由此更可見一斑。且鄭仙雖本屬道教神仙,但梁氏的書寫無意計較于此,“禮佛”一語在此既可見當時祭拜神仙與禮佛所拜禮的對象雖不同,然在燒香膜拜儀式上大同小異,亦可見即便是當時“貴第人家”,燒香膜拜神靈并非出于對某一特定宗教的皈依,而只是為求得心理慰藉。
順德鄧方《羊城雜詠》:“五更秋露下精藍,小北門前策曉驂。聽說燒香多韻事,黃綢袱被鄭仙巖。”(20)鐘山、潘超、孫忠銓編:《廣東竹枝詞》,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1頁。另據《后續嶺南即事》四集“羊城佳話(四時詩)”(十六首之十)謂:“南人多是好神仙,八夜拈香廟里眠。又約明朝須起早,白云靈應在山巔。”詩后附注:“粵俗:每逢七月二十四日城隍與鄭仙誕,先晚睡城隍廟地,謂之打地氣,明早往白云山。”(21)按:此詩作者不詳,《后續嶺南即事》又題“《嶺南即事雜詠》”(輯者未見著錄),《廣州大典》據清粵東學院前守經堂刻本影印,第504冊,第447頁。可見作為其時民間信仰,廣府民眾在拜省城中的城隍崇拜與拜省城外的鄭仙崇拜之間,已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連動效應。
今人吳永章在為晚清陳坤《游白云》一詩所作箋證,其中引民國時期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廣東》卷七“廣州歲時紀”條記述“游白云”來由與盛況的一段文字為證:
七月二十四日,俗稱鄭仙誕,鄭仙即安期仙,飛升于省城東門外白云山,祠宇在焉,曰鄭仙巖,又曰云巖。禮神者往慶祝之,謂之游白云。并順道游覽附近諸名勝,……有流連數日始返者。惟游玩者終不及禮佛者之盛,雖婦女亦間關跋涉,趨往禮佛。……俗以曾游白云者,身體必加強健,故趨之若鶩。又俗以凡游白云,至少必二三年繼續往之,甚有每年必往參禮者。(22)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8頁。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民國成立前),隨著“西風東漸”,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在內的維新變法人士乃至革命知識分子大力倡導社會文明新風,幾度沖擊民間祭祀,但在一些地方社會如廣州鄭仙誕等不少民間信仰根深蒂固。如據1906年7月20日《東方報》報道:廣州西關多寶街有個姓梁的年輕人,平時迷信于鬼神之說。這一年,他準備在鄭仙誕期間騎馬前往白云山拜神,但在練習騎馬時不慎摔傷,兩天后去世。其父母雖痛不欲生,然而當有人談及這是為拜神所害時,他們卻不敢有任何怨言。這個真實事例,正如民俗學者楊秋所指出的“他們(按:指其父母)不敢對神靈有所埋怨,證明神靈對他們有威懾力。”(23)《近代廣州風尚習俗研究》,第142頁。
直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的“黃金十年”,雖然中間發生世界性經濟危機等外在不利事件,鄭仙誕民間信仰依然不為所動。在1934年《人言周刊》上曹夷群所采寫的“鄭仙誕”通訊報道:“他(按:指安期生)究竟是哪一個朝代的人,生前有什么功績在社會,值得人們這樣信仰、崇拜,我們完全不知道”,“今年鄭仙的誕期又到了,盡管不景氣的氛圍籠罩著社會,盡管有許多人在唉聲喊苦,但這個香會是不能不舉行”,“聽說今年的香客,比往年更多。這是什么緣故,我們完全不明白”(24)《人言周刊》1934年第1卷第33期。。分析這些報道,可以見出盡管當時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受到當時整個世界經濟危機的波及,經濟不景氣、民眾多困苦,卻并未對蒲澗節會民俗活動產生任何不利影響,正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表征。在一些廣東人中流行的俗語“有心游白云,無意識鄭仙”(25)《民間故事:鄭仙的故事》(作者失名),《小朋友》雜志1931年第470期。可為佐證。
曹夷群對其時鄭仙誕活動的通訊報道相當詳實,留下了一份難得的歷史記錄。過錄部分如下:
最熱不過的,是二十三、四兩天。有錢的人,一早雇了汽車到白云山去。汽車的價錢很貴,往時給值一元,現在非十元八元不辦,有時還愁雇沒有。野雞車的生意很好,他們藉了這一個機緣,發了一筆洋財。總計起來,每一輛汽車,每天至少有百多塊錢的收入。公共汽車的生意也不壞,……每一輛車里,都裝滿了人;有的擠不進去,站在外面的踏板上。一條沙河路,整日整夜,盡是人的潮、車的潮……
……沿路兩旁都是一些蓋著蓬棚的食物攤,賣的大都是雪糕、汽水、面飯……山前山后的各條大路小路,滿是人頭……近鄭仙祠的地方,人是愈更擁擠。
夜里的世界更加好看了。……日間上山的香客,大都沒有回去;他們在山上過夜,這叫做“打地氣”。……男人們希望發財,也得打一夜地氣不可。……有的用幾塊錢向和尚租了一間房子,在那里喝酒打麻雀。食攤也開了夜市,生意很好,直到夜半十二點方才收場。還有一些投機的人,臨時在山上開設賭場和煙館,引誘香客去賭錢和吸鴉片。(26)《人言周刊》1934年第1卷第33期。
抗戰勝利后,據1947年《粵聲》雜志“白云改觀:能仁鄭仙遺跡無存,山上林木亦遭劫運”條報道:
俗傳昨八日為鄭安期采藥升仙日,女士每于是日游玩白云山,查昨日白云山上游人雖比戰前略減,但沙河先烈道上車水馬龍,裙屣蹁躚,冷落白云,頓呈熱鬧,沿途茶寮酒家及臨時擺賣小販,無不利市三倍,來往沙河公共車雖增加車輛,亦擠得水泄不通,一般游客,乃改乘野雞車或三輪車前往。野雞車一送索價七八萬元,三輪車從先烈路至山腳二萬元。(27)《粵聲》1947年第2期。
從以上兩則報道和其他材料中,不難見出鄭仙誕具有的娛樂性和消費性。而其娛樂性和消費性,則統攝于廣州地域范圍內跨越社會性別、階級和族群差異之宗教性的基礎上。禮拜鄭仙、商業集市和民眾娛樂,成為當時鄭仙誕的三重社會功能。
2.“祈子”觀念、行為習慣和儀式制度在鄭仙誕中的突顯
在傳統中國的民間信仰中,信仰物質的東西勝于信仰精神的東西,即使是信仰精神的東西,也必須是物質化了的精神。傳統中國是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因此勞動力的增殖(“添丁”)成為增加家庭財富的重要手段,進而形成“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和重男輕女的生育觀。鄭仙誕民間信仰習俗內涵的增添,其中最突出者莫過于如當地民眾為“祈子”而前往致祭。這一習俗大約形成于明末清初之際,“嶺南三大家”之一的陳恭尹《安期巖重修記》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故老相傳,安期巖饒竹石古木,其神最著。間者數用兵,禱祀不至,而樵人斧斤尋之,濯然無復存者。
去年夏,郡人某某避雨巖下,顧瞻叢莽,有神頹然,丹堊淋瀝,仰首倚石壁立。數人者,相與揖而祈子,逾年悉驗,乃醵金為屋其旁,置僧以朝夕香水。領是工者十有二人,未畢而產男者七,有逾耄無子而驟產者。既落成,要余及梁藥亭往,俾為記以巉諸石。
…………
(安期巖)安期生仙人所托,殆不謬者。既還,遂為之記。(28)《獨漉堂文集》卷五,《廣州大典》據清康熙年間陳氏晚成堂刻本影印,第438冊,第640頁。按:同屬明末清初的浙江平湖人陸葇《游白云山記》記載他游安期巖,見巖構小屋“中一室設安期先生像,椽棟之上扁額無馀隙,越人祈嗣于先生者有驗也”,可為佐證。又按:據《尺岡草堂遺文》卷二記載,同治庚午年(1870)番禺陳璞應主持重修鄭仙巖的一山僧之請作《重修鄭仙巖記》,可見鄭仙巖(安期巖)多次重修,且與僧人亦有一定關系(此點頗堪玩味)。
在明末清初王朝鼎革、社會動蕩、兵亂殺戮,造成人口在短期內銳減、生產遭受空前破壞這一時代背景下,廣州本地民人在安期巖向安期生神像作揖祈子,碰巧應驗,于是建造起方便祭祀的屋室。對安期生的祭拜這一舊有民間信仰,由此一具有神異色彩的偶發事件,開始增添“祈子”的民間習俗內容。同為“嶺南三大家”的梁佩蘭(號藥亭)、陳恭尹信服本地民人為“祈子”祭拜安期生的靈驗,特別是經陳恭尹撰文加以記錄傳播(按:陳文特別強調“產男”),為這一民間信仰在廣府地方社會更加深入人心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當時地方士人力量與民間信仰互動的一個典型事例。
“嶺南三大家”之首的屈大均則有《自蒲澗至廉泉洞尋鄭仙鶴舒臺作》詩作涉及這一習俗內容:
七月廿四廿三日,廣人傾都東門出。菖蒲澗中漱寒泉,共尋鄭公煉丹室。
傳聞此日鶴舒翼,安期上仙就仙職。……玉舄何年留阜亭,蒲花紫茸含秋馨。
越人祈子每雙乳,高禖此地惟仙靈。……錦幡爭答白花男,珍果競懷紅粉婦。
仙人拇跡履紛紛,觸破苔痕生白云。生兒我欲生高士,似我迷花不事君。(29)陳永正:《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286頁。
從詩中可見蒲澗節(鄭仙誕)已增加當地民眾為“祈子”致祭、鄭仙替代自遠古以來的“高禖”神主掌生育之儀式活動內容,有將本地民眾日常世界之基本需求融為一體的演變趨向。
對蒲澗節(鄭仙誕)新增“祈子”內容,并為本土廣大民眾所信服接受,作為本土文化精英的“嶺南三大家”在自覺不自覺中扮演了現代傳播學中所說的“意見領袖”這一重要角色。現代傳播學認為,“意見領袖”是信息傳播過程中最活躍的部分,他們較多地接觸媒介,并將信息傳播給社會中不活躍的部分,后者在“意見領袖”的影響或指導下獲得信息。(30)戴元光、金冠軍:《傳播學通論》,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80-182頁。同時需注意的是,“意見領袖”的這種主導性作用是基于長久以來安期生在廣州所具有的信眾基礎。
直至光緒初年,順德廖荻莊《羊城竹枝詞》(其一):“為拜仙祠禮鄭翁,紛紛游女出城東”(31)《廣州古今竹枝詞精選》,第45頁。,香山張日昕《羊城竹枝詞》(其二):“白云山下早秋天,逐隊拈香禮鄭仙。兩鬢太松風太緊,烏絲細綰翠花鈿”,番禺林象鑾《羊城竹枝詞》(其六):“蒲澗濂泉夕照邊,白云山上鎖秋煙。兒家別有心中事,不拜觀音拜鄭仙”(32)《廣州古今竹枝詞精選》,第54頁。等,可見當時廣府女子因祈生子嗣而禮拜鄭仙風氣之盛,甚至超過在其他地區普遍流行的佛教觀音菩薩信仰。廣府民眾按照自己的情感和生活經驗,對于不同的偶像崇拜都以“誠則靈——靈則誠”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標準加以接受或淘汰,“民眾對神仙的本意不甚了解也不求深解。他們重視的是其神性,這種神性能幫助自己解決生活中的具體的、實際的問題”(33)李遠國等:《道教與民間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9頁。。
及至民國時期30年代,如上述曹夷群的通訊報道亦述及廣府女子因祈子而虔誠禮拜鄭仙風氣:
到祠里去拜鄭仙的,要費了很多力氣才給你擠進去;尤其是那些年老婦人、摩登少女……好像擠不進去拜一拜鄭仙,她們是很不情愿的!祠里全給那白色的煙氣彌漫著,對面不易見人,眼睛張不開,眼淚掛在頰上,幾乎咳不出氣。為了是虔誠來拜菩薩,他(她)完全不覺得怎樣的難過!
……日間上山的香客,大都沒有回去;他們在山上過夜,這叫做“打地氣”。女人家要想得子,在山上打了一夜地氣,回去就可以懷孕。……因此每晚在山上“打地氣”的人,是有幾千人。山上的白云寺、能仁寺、濂泉寺……都是給這些“打地氣”的香客住滿了。他(她)們橫七豎八都躺在佛堂大殿的地上。寺外也滿躺著人。……
分析上述對“打地氣”的細致描述,既可見當時廣州社會風氣比較開放的一面,亦可見在當時一些社會民眾精神深處,仍頑固殘存著“野合”求子這種在兩千年前上古人類中非常流行的帶有原始宗教色彩之性行為觀念,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新舊道德倫理觀念的奇異雜糅及其行為特征。
3.鄭仙誕民間信仰與官方管理之間的合作與沖突
民間宗教信仰因其強大、穩固的社會吸引力和號召力,歷來為統治集團所關注。“如何區別、對待它們,涉及敬神的選擇和規格,涉及意識形態的內容和導向,涉及社會治安和社會經濟生活。”(35)漆俠:《遼宋西夏金代通史:宗教風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3頁。蒲澗節(鄭仙誕)一直未被納入地方官府的正統祀典中,介于正統祀典與民間“淫祀”之間,不具備壓迫、強制性質,本身政治色彩相對較為淡薄。
直至晚清,由廣府女子因祈生子嗣而禮拜鄭仙之風氣,發展出平時為封建禮教所束縛的青年男女,趁此難得機會出城游玩散心,更有有心人借此機會暗中尋覓佳偶。如據周獻南所作《竹枝詞》“相逢爭作白云游,貪看名花不雇兜。妾自下時郎自上,怪他一步一回頭”,由此可知對于當時的青年男女特別是女性而言,參與鄭仙誕之目的并非完全是燒香拜神之類信仰。(36)《近代廣州風尚習俗研究》,第165頁。晚清一些官紳似乎看出女性參與鄭仙誕不僅為酬神、拜神,同時包含希求獲得一些個體行動上的有限自由,因此他們三番五次反對女性外出祀神。如清末番禺縣錢縣令就曾下告示,嚴禁女性前往白云山燒香,理由自然是僵化、保守的封建禮教倫理。(37)按:《申報》1901年9月2日第11版隨報附張對此有報道,并在報道中全文照登該告示,參見《近代廣州風尚習俗研究》第184頁。這種官方管理,只是對鄭仙誕的信眾人群范圍有所約束、限制,并未給鄭仙誕信仰造成任何實質上的不利影響。真正開始給鄭仙誕這類民間信仰帶來生存危機的,是源于晚清社會內部自上而下的現代化運動。如在康有為等人的建議下,戊戌變法期間出臺《詔各省府廳州縣設立學校》敕令規定:“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地方官曉諭民間,一律改為學堂,以節糜費而隆教育”,一時間嚴重沖擊了部分民間祠祀信仰。
辛亥革命后,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和一般民眾的生活習俗在部分程度上除舊布新。民國初年的廣東軍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政策措施,如“禁神誕、禁燒衣、禁打醮……”,軍政府警察廳廳長陳景華雷厲風行,每逢神誕誕日前后三日關閉廟門,并派警察監守,不許民眾參拜,對違反之人進行嚴懲(38)《近代廣州風尚習俗研究》,第194頁。,在官方和民眾間制造了緊張的對立關系。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為推進社會整合、加強社會控制,曾頒布一系列關于風俗改良的法令,特別是著力杜絕假宗教之名而行迷信營利活動之實。在此前的大革命運動各地搗毀神祠、破除迷信的基礎上,1928年9月內政部頒布《廢除卜筮星相巫覡堪輿辦法》。廣州市政府積極響應,但除廣州市風俗改革委員會力主其事外,甚少見有其他民間社團參與其事,以致成效不甚理想。10月國民政府頒布《神祠存廢標準》,要求各地禁止“男女進香朝山,各寺廟之抽箋禮懺,設道場放焰口等陋俗”等。1929年10月,國民政府內政部制訂并呈請行政院批準《風俗調查表式》(后定名《風俗調查綱要》 和《淫祠邪祀調查表》),明確規定淫祠邪祀標準,同時規定“凡正式宗教與先哲名人、或捍患御侮、或特殊發明有功社會及有關善良風俗者概不在內”,以使民眾進一步分清淫祠邪祀與正當的宗教廟宇及紀念神祠的區別。11 月內政部頒布《神祠存廢標準令》,規定應行保存之神祠標準有二:一曰先哲類,二曰宗教類。應行廢除之神祠標準亦有二:一曰古神類,即古代之科學未明,在歷史上相沿崇奉之神,至今覺其毫無意義者,包括日月星辰之神、山川土地之神等。二曰淫祠類,附會宗教,藉神斂錢,或依附木偶,或沿襲齊東野語者,包括送子娘娘、財神、二郎、瘟神、玄壇、時遷廟、狐仙廟等。為將正當的道教活動與迷信區別開來,1930年2月廣州市社會局提出《關于辦理破除迷信案》,內容包括法壇神像限用各該宗教有正經可考之先賢,不得陳設神怪偶像等。1930 年3 月國民政府內政部公布《取締經營迷信物品業辦法》。許多地方在取締淫祠邪祀后,有關這類祠廟的賽會活動即被廢止。
我們知道,迷信與民間宗教信仰關系向來比較復雜,在某些地方交叉重疊和相通互融,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就給界定和區別它們帶來了困難,以致各地方當局在查禁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執行標準寬嚴不一、出現偏差等問題。依照當時政府部門所定標準,鄭仙誕屬于應行保存者,可謂涉險過關。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這一系列行政強制措施,是否矯枉過正姑且不論,無疑會對蒲澗節(鄭仙誕)的傳承構成外在壓制和強力沖擊。當然這些嚴禁措施只是行于一時,并不能動搖蒲澗節(鄭仙誕)這類有著深厚傳統文化土壤和民眾廣泛認同心理的民間信仰活動之內在根基。畢竟在基層民間宗教信仰的生活中,如不通過自發的“軟性權力”(Soft Power),作為“強制權力”(Hard Power)的行政權力很難在屬于個人精神世界的信仰領域起作用。顧頡剛、容肇祖、李景漢等當時一批深入民間進行調查的學者,因此批評“南京國民政府通過破除迷信運動展示的對現代文明的追求,從根本上漠視了構成本民族面貌真正基礎的民眾文化;民眾文化不僅有其內在的自足邏輯,而且充滿了原生態的活力”(39)李俊領:《天變與日常:近代社會轉型中的華北泰山信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31頁。參見嚴昌洪:《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風俗調查與改良活動述論》,《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
雖然此后在地方政治勢力間的博弈中,廣州地方政權有關管理政策及其執行幾經變動,蒲澗節(鄭仙誕)仍然保持慣性、相沿不斷,成為一種地域性和世代性兼具的民眾群體文化記憶和身份認同。仍以上述曹夷群的通訊報道為例,就涉及地方政府當局的管理舉措:
過了中元節,離香會的時期就不遠。……同時廣州的當局,恐發生意外的危險,就在這幾天派了大隊武裝的軍警,駐扎在山上,保護香客。當局對于地方的治安,盡了相當的保護職責。(40)《人言周刊》第1卷第33期。按:《粵聲》雜志“白云改觀”條有抗戰勝利后的類似報道。
可見民國初年廣東軍政府與社會民眾在民間信仰活動上的尖銳矛盾已不復存在,1934年廣東的主政者是廣東人對其治績評價比較高的本地軍閥陳濟棠,而陳濟棠平時對求仙拜佛頗為熱心,對本地古老文化傳統持比較尊重的態度。在陳濟棠的影響下,廣州地方當局不僅沒有采取嚴禁民間信仰活動的措施,反而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幫助、保護措施,確保不致生亂。這些幫助、保護措施,直至抗戰勝利后仍被地方當局沿用不廢。
新中國建立后,社會形態發生巨大變革,因其中混雜的迷信成分有悖于唯物論、無神論等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以致民間信仰在總體上被視為迷信活動而受到嚴格控制,蒲澗節(鄭仙誕)一度中斷多年。據龔伯洪和徐燕琳等人的文章介紹,鄭仙誕于上個世紀50年代仍有,60年代消失,80年代初復現,但在80年代末被重陽節白云山登高活動所取代。
進入21世紀,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蓬勃興起,全國大量民間宗教信仰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身份重新進入國家體制的視域中。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民間人士的倡議下,自2012年起廣州市白云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局積極介入,恢復舉辦每年一度的鄭仙誕活動,并在鄭仙巖景點入口處修建牌坊,安置鄭安期“懸壺濟世”大型雕塑和故事浮雕群等。在此過程中,鄭仙誕先后被列入白云區、廣州市兩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些舉措旨在努力繼承鄭仙誕民俗活動中的勸善濟世等積極因素、拋棄愚昧迷信等消極因素,激活當代廣州民眾對于這一本土傳統節俗的文化記憶和身份認同,并嘗試將傳統文化空間與現代都市社會進行有機對接,從而實現一定程度上的創造性轉化。
四、余論
綜合以上分析,毋庸諱言,首先廣州蒲澗節(鄭仙誕)作為傳統中國歷史背景下的一種地方民間祭祀信仰,自誕生以來便與本土道教關系密不可分,在千百余年來的傳承演變中不可能不帶有一定迷信成分。其傳承演變所產生的超自然、超人間異己支配力量,在歷代信眾中始終沒有發展成為超越世俗功利社會生活經驗的永恒之純精神性信仰(如黑格爾講的自由宗教,又稱絕對宗教)。
其次,從當今流行的場所文化認同理論來看,場所文化認同的三個關鍵性要素,在蒲澗節(鄭仙誕)民俗活動中完全具備,即:菖蒲觀、鄭仙祠等古跡建筑作為“物質環境”的認知認同,士民集體出游嬉樂作為“行為”的參與認同,和祭拜祈愿作為情感與意義表達的體驗認同。如果說菖蒲觀、鄭仙祠等古跡建筑屬于物質實體形態層面,安期生升仙傳說屬于精神價值觀念層面,則蒲澗節(鄭仙誕)屬于綰結前兩者的地域風俗制度層面,三者共同構成一幀自宋代以來廣州民間信仰節俗生活的全息立體影像(41)按:此處借鑒參考殷學國、蔣述卓《古籍整理與現代學術演進關系分析》(《學術研究》2016年第9期)一文關于文物、古跡,口述、傳說和史籍文獻“三者”的說法。。
最后,需要特別加以指出的是,自宋代以來廣州蒲澗節(鄭仙誕)民俗活動不僅同樣體現端午、重陽等全國性一般民間節俗所具有的全生避害、人神(仙)祭祀、飲食節物、競技娛樂與家庭人倫五大要素,并建構起了一個廣州本地獨有的民間節俗小傳統;而且因其宗教性、娛樂性和消費性三大方面兼備且突出,自宋代以來便成為頗能體現廣州城市公共生活的一個重要節日,和廣州士民群體傳承發揚的一份記憶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