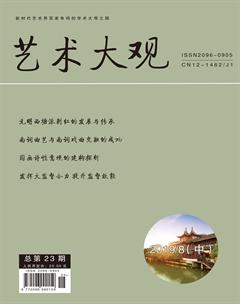張若虛《春江花月夜》賞析
初唐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內涵深刻,情感誠摯。《唐詩評選》以為此詩“句句翻新,千條一縷。以動古今人心脾,靈愚共感”。意思是說這首詩句句都有新意,古往今來,無論是什么人讀到它都為之深深感動并引起共鳴。這首詩表達出宇宙蒼莽,個人渺小的哀傷,也有表達思念情懷的繾綣悲涼境界,說出了大多數人的心聲,使人為之動容。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
開篇詩歌即將視線投入到無限廣闊的海平面,看那一輪明月與潮水一齊激蕩,一齊誕生。意境高遠,眼界開闊的同時,動態的美感應運而生,眼前猶現明月自海上緩緩而升的壯闊景象,月華隨著波濤一瀉千里。視線由遠及近,江流宛轉,圍繞著江渚的芳草,月色下的花林猶如灑下一片霜雪。月色照耀下,空中感覺不到白霜飛舞。汀上的白沙在月光照耀中越顯澄明,也仿佛不易看清。波光、月華、飛霜、沙汀,都是極其明亮空靈的色彩。有遠近的順序,動靜的結合,色彩的交相輝映、視覺觸覺的共同感知,詩寫到這里不僅是在廣闊的平面視野上,也是在開曠的立體空間里,營造出一番悠遠澄澈的意境。
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詩人站在江邊,在如此靜謐而空靈的景色下,思緒宛轉飄飛,面對眼前之美景,不禁聯想并詰問宇宙的開端:那么是誰第一個見到江月,江月又是什么時候初次照耀世人?這是難以回答的問題,但是體現的卻是詩人廣闊的宇宙意識。將自己置于無限的宇宙空間,不免生出個體的渺茫。正如蘇軾的“羨長江之無窮,哀吾生之須臾”。在天人對比之下,會生出生命有限的遺憾與哀慟,但是作者后一句說道“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足以見到詩的格調并非是面對浩瀚宇宙與渺茫人生的傷感失落,而是一種客觀理性,去看待生命與時間,個人生命雖是滄海一粟,但人生代代無窮無盡,正如時間永恒。詩人并沒有因為宇宙的寥廓,個體生命的渺小而頓生出太過繁重的隱憂,而是多了一份爽朗與理性思考,江月無窮,歷史無垠,無所預期未來何人何事,只這眼前之景是實在的,一江春水無語東流。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愿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
《唐詩評選》中所說的新,在這一段中體現出來。詩人站在江邊,思緒馳騁,忽然想到,是誰家的游子仍然漂泊在外,使得樓上的妻子望著明月憂愁?月滿西樓,徐徐地照上思婦的妝臺,令思婦滿懷惆悵,相思難遣。這里詩人雖以思婦的口吻,敘述對游子的相思之意,卻能將思婦的動作和心理刻畫得細膩入微。詩中樓上徘徊的不只是月光,更是思婦因心中相思難遣而憂慮徘徊。月光照在思婦的妝鏡臺,而不是照在其他地方,更是別有深意,容易使人有“曉鏡但愁云鬢改”的聯想,又體現出思婦對青春易逝的擔憂,加深了詩詞中思念之情的濃度。以至于這種情感濃重到“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到最后吐露出誓言一般的表白“此時相望不相聞,愿逐月華流照君”。
傳統的游子思婦的題材,詩人加以獨特的構思:借思婦的口吻書寫離情別緒。并且深切地將思婦的心境生動細膩地描繪出來,月與人共徘徊,情與景相交融,虛與實相模糊。起承轉合之間,角色轉換,過渡自然。因此我們仿佛覺得不僅是思婦心中言,亦表現作者胸中語。
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詩人的思緒由遠處的思婦回到現實之境。流水落花,春事將盡,可憐自己仍然漂泊在外。江水復又東去,落月復又西斜,而自己的歸途仍然無限遙遠。不知道今夜月圓,又有哪些游子乘著茫茫月色踏上歸路?“我”的一片相思,猶如這茫茫月色,落滿江樹,搖搖曳曳……“江水”“落月”“江樹”營造出一個澄澈清明的境界,將原本惱人紛繁的思鄉別緒,化為滿樹光輝,搖落散去。
詩是緊扣題目的,春、江、花、月、夜,每一字都寫得出彩。詩中所表達的情感,有宇宙廣闊的蒼茫,人生無限的憧憬,游子思婦的繾綣,思鄉難歸的惆悵。但是詩的意境并非沉重灰暗的傷感色調,相反,明月、花林、流霜、白沙、芳甸等意象,營造出的是明朗澄澈的意境。同是思考與詰問宇宙,我們也并沒有讀到譬如: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無奈和悲憤。更多的是讀到一種平和超脫,是詩人立于世俗高度,俯視宇宙人生,感受到:時空如此寥廓,人生亦是代代不絕,所謂的契闊無常,思念難遣,也是人生的常態。所以獨立江邊,詩人思考何人初見江月、江月何時初照、何人扁舟漂泊、何處相思高樓,“對于每一個問題,他得到的仿佛是一個更神秘的更幽默的微笑”。
張若虛(660-720?),與陳子昂所處的時代相同。正處于初唐武后時期。這個時代是一個及其紛繁多彩的時代。政治上開化,經濟上對外交流頻繁,因此文化上亦是胡漢交融,異彩紛呈。經由高宗,武后大搞“南選”,創立科舉,士人通過科舉,走上政治的道路,參與國家政權。另一方面,國家對外開疆擴土,軍心豪邁高漲,不少的文人愿意身先士卒,一馬當先,這一方面體現在詩歌上即為初唐邊塞詩的興起。因此,這是一個建功立業的時代,是一個追求理想,實現自我價值的時代。在這一時代中,文人的面貌與社會高漲、自由、豪邁的風氣相一致,表現出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盡管個人生命有限,并且要漂泊離鄉,知識分子們也愿意在這樣的時代中拋卻兒女情長,一展拳腳。所以我們說,《春江花月夜》中擺脫不了離別思緒,宦游之愁,但在詩人理性的思考與通達的釋懷中,更看到積極灑脫的情感基調。
作者簡介:周艷華(1970.7-),女,黑龍江依安人,中學高級教師,大學本科,齊齊哈爾市第八中學,主要從事高中語文教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