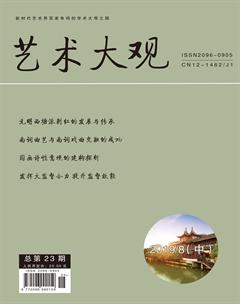從霍普特曼《織工們》中看人像展覽式戲劇結構中人物的刻畫
摘要:人像展覽式的戲劇往往是很難把握的,既要刻畫每一個人物,又要把握整體結構布局。本文就將以劇作家霍普特曼的作品《織工們》為例,分析該類型戲劇作品中人物的刻畫。
關鍵詞:霍普特曼;人物刻畫;人像展覽式
霍普特曼的《織工們》是以西里西亞工人起義為素材并結合他的生活所創作出的一部五幕劇作。他用自己爺爺的經歷加上社會問題的反應,創作了這部具有情感的作品,他不僅僅是單純的抨擊現實、反對壓迫,更是對織工這類人物形象進行刻畫。劇中出現的人物超過40個,塑造的是一組組的群像式人物,每個人物身上都帶有“織工”的印記。
一、人物分析
第一幕發生在彼得斯瓦道的德賴西格家,描繪了織工們向資本家德賴西格上交布匹和領取工資時受盡欺壓盤剝的情景。“這里的很多織工看上去都很相像,目光呆滯,面相苦澀沉悶,胸腹干癟,骨瘦如柴,也許是由于在織布機旁坐的太久的緣故,膝蓋都直不起來,有的像書生,有的像小學老師。”霍普特曼在第一幕開場時的舞臺提示中,用真實、細膩的筆觸,寫出了織工們的外貌特征和生存現狀,為戲劇作品奠定了基調,為后面織工們的反抗做了鋪墊。
在資本家德雷西格先生的眼中,織工只是他生產的工具,織工的生死與他們無關,他們把名聲、金錢比織工的生命還重要。在小男孩暈倒時,第一反應是自己的名聲,當聽到小孩低語說他肚子餓時 ,他的臉一下子變得蒼白,并趕緊以聽不清為由搪塞過去,從側面刻畫了德雷西格的冷漠,充分暴露了他假慈悲真剝削的嘴臉 ,第一幕展示了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為織工起來斗爭做了鋪墊。
資本家不斷地壓迫織工們,織工們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以德雷西格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用工作機會威脅織工,甚至降低酬勞,而其對抗力量織工們卻力量薄弱,無法與其抗衡,故他們只能忍氣吞聲,即使被不斷的壓迫也只能服從。
“織婦甲走近德雷西格身邊,小心地拍掉他大衣上的灰塵,有點奉承地說,您可能碰到什么臟東西了,衣服沾了些灰。”織婦甲只能討好屈服來保全那少得可憐的酬勞,她迫不得已的奉承、別無選擇地討好,這個織婦的形象是萬千織工們中的一個,她代表了織工中的一類人。如果說織婦迫于生計而低頭,那么露西,則與之完全不同,露西是醒悟之人。
在露西在與老希爾塞爭吵中的大段獨白中,看到了一個在極度貧窮環境中堅韌母親的形象。她在希爾塞家中連最起碼的溫飽都無法滿足,尤其是連孩子們的生活都無法保證,身為一名母親,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放棄一起,“雙腳都流血”只為乞討干凈的奶去救孩子一命,而“狄特累希家的人卻泡在美酒和牛奶里洗澡”,在這樣的長時間的不公平中,身為母親的露西再也無法忍耐,她選擇了反抗,加入織工們的反抗隊伍。
老希爾塞的一生都以織布工作度過,他習慣了被壓迫、安于現狀,他信賴耶穌、是忠誠的信徒,他已經被年復一年的織布工作所壓迫,沒有了精神和方向,他是被資產階級所同化的的人,他不能也不敢反抗,猶如螞蟻一般小心翼翼地生活,連說話都不敢出聲“噓……小聲一點!不要再說這種褻瀆神靈的話了!”漫長的、艱苦的生活并沒有喚醒他,反而變得麻木、膽小。當聽到織工們起義的消息時,他是不相信的;當小孫女拿到一把值錢的鑰匙時,他生怕惹上什么麻煩,想要趕緊把鑰匙給警察。他認為起義是瘋狂的、錯誤的,他把織工的工作看作自己的職責,他認為起義是瘋狂的事情“我絕對不會和你們一起去瘋的!”并且坦然接受生活的不公正“這里是仁慈的天父安置我的地方!我們要盡我們的職責留在這個地方!”緊抓的“織布”是他的救命稻草,織布是他精神的支柱,織布卻躲不過子彈,他死在了織布機上。一個老人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織布機,他也同樣是千千萬的織工中的一名,“撲倒在織布機上”是他最后的掙扎,它終將生命獻給了“織布”。
二、總結
作者霍普特曼的爺爺也是一名織工,他老希爾塞的原型便有他爺爺的影子,霍普特曼曾在獻給父親的劇本前言中寫道:“我的祖父年輕時也是個窮織工,像這兒描繪地座在織機后面的織工一樣,此劇就是脫胎于您所口述的關于我祖父的那些故事。”[1]這樣的開放式的結尾,留給觀劇者更大的思考,他沒有評判某種制度或者某個人,同時也沒有寫出這場反抗活動的成敗,他只是將每個人的生存狀態和所面臨的選擇展現出來,霍普特曼將思考留給觀眾。劇中的人物是大眾的縮影,他們都是真實的、源于生活的。《織工們》的戲劇場景開闊,生活片段的記錄式的生動再現將織工們簡單、直白的描繪出來,整個戲劇隨著起義的進行而不斷推向高潮,而織工們生存狀況讓觀眾看到了舞臺上正在進行著得到真實的社會。
《織工們》的時間跨度較短,發生的地點產生五次變化,人物眾多,展現的是織工們起義的一個階段。織工是一群人物,是織工這個階層中的全部人的代表。霍普特曼并不是要謳歌這些下層階級,“當人們看他的戲或讀他的劇本,并且感到自己是處于劇本所描寫的情節當中時,他們會覺得需要新鮮空氣,并且會提出將來如何消除這些苦難的問題” [2]劇中的人物是推動戲劇情節發展的關鍵,霍普特曼將織工們的形象刻畫地淋漓盡致,就如同生活一般的真實,雖說是人像展覽式的織工群像,但卻被霍普特曼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將織工們的生活寫活了,這次起義,不僅僅是劇本的情節,更是生活的縮影。
參考文獻:
[1]霍普特曼,著.霍普特曼戲劇兩種[M].韓世鐘,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2]張杰.吉哈特·霍普特曼的柏林戲劇[J].文藝研究,2016(4):95-103.
作者簡介:史欣冉(1999-),女,山東省泰安肥城市,山東藝術學院戲劇學院戲劇學專業2017級在讀本科,主要從事戲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