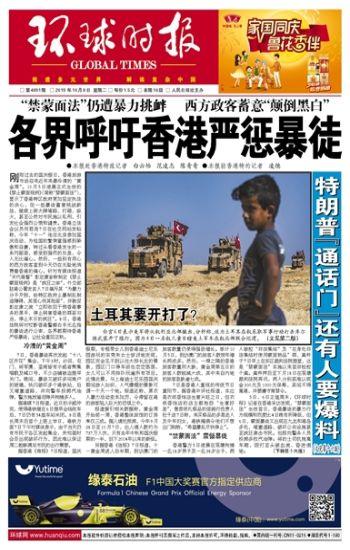互聯網如何打破“偏見閉環”(觀察家)
史安斌
21世紀蓬勃興起的前沿科技,將人類傳播帶入了“智慧媒體時代”。借助于手機等隨身媒體,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無時不有”“無遠弗屆”,加拿大思想家麥克盧漢在半個世紀前暢想的“地球村”已然成為觸手可及的現實。
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2016年的美國大選和英國“脫歐”公投標志著人類進入了“后真相時代”。從傳播學的視角來分析,“后真相”的泛濫與智媒的興盛存在著直接關聯。社交平臺在新聞傳播的核心地位日趨凸顯,各類碎片化的虛假信息、流言蜚語、軼事緋聞呈現病毒式傳播的趨勢。相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體,網民們更愿意依賴一個個“部落化小圈子”獲得資訊,分享觀點。然而由于“圈內人”擁有相似的價值觀,致使他們每天得到的訊息經由了“立場的過濾”,與之觀點相左的理念逐漸消弭于無形。加之“沉默螺旋”“寒蟬效應”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益發凸顯,人們為了留在“朋友圈”內,忌憚于發表不同的意見,否則就要面臨要么“退群”要么“被請出”的結局。更有甚者,社交媒體所具有的“回聲室”“過濾氣泡”等負面效應加劇了共識的撕裂,形成了各式各樣“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見閉環”,阻斷了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間的有效溝通,使憤懣、敵對、仇恨情緒乃至于暴力行為蔓延于線上線下,把互聯網變成了“分裂網”,也把昔日自我標榜為“民主燈塔”的“合眾國”和“聯合王國”變成了黨爭不休、罵聲不絕的“分裂國”。
造成“后真相”大行其道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各類智媒平臺所依賴的算法推薦。借用英國啟蒙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的比喻,這種“算法利維坦”借助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的蓬勃興起而擴張為一種新的霸權。算法成了上帝制造的“技術神祇”,方便人們在浩瀚的數據海洋中恣意遨游。但與此同時,算法還是由人類來編創與運作,也就具備了半神半獸、善惡兼備的雙面效應。它在為個體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時,有可能操控乃至吞噬整個人類社會。
美國學者的研究顯示,臉書等社交平臺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用戶的社交網絡。這不僅基于其所擁有的朋友數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間交流的頻率和類型。社交平臺通過關注用戶的朋友圈和興趣愛好,通過推送機制強化其社區歸屬感。顯然,傳統主流媒體不僅思考“受眾對什么感興趣”,還會考慮“受眾應該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樣的新聞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臺的把關機制則不是基于公共利益,其首要考慮的是“對用戶來說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現不僅僅是信息傳播主體的轉變,更是把關標準的轉變,而基于個體價值的“過濾氣泡”機制則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偏見閉環”,也使得“算法利維坦”的隱性操縱變得更加順暢和便利。失去了有效的跨文化對話和溝通,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鑒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人類又一次瀕臨“文明沖突”或“新冷戰”的邊緣。
如何擺脫當前由于“算法利維坦”和“信息閉環”所導致的跨文化傳播困局,實現費孝通先生暢想的從“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與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媒在技術和機制上進行完善和修正之外,說到底還是要靠提升人類自身的跨文化傳播素養。首先,無論是信息發布者、社交平臺運營者還是用戶都應當像對待自身文化那樣,尊重其他種類的文化價值觀,不應使用語言或符碼來有意貶低“他者”,打破“偏見閉環”對個體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傳播者應當客觀、真實地認識和再現外部世界。誠然,不同文化對“真實”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謂“真實”也是一種社會與文化建構。即便如此,在跨文化傳播當中,傳播者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誤導和欺騙受眾。
再次,社交平臺應建立適當機制鼓勵不同文化背景的傳播者——尤其是那些來自弱勢群體的傳播者——表達他們的意見。無論他們的言論是否受到大多數人的歡迎或拒斥,我們都應該確保每個人擁有平等的“傳播權”,有效防止“算法利維坦”對個體和社群的操控。
最后,傳播者應當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最大限度地包容和汲取各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觀。換言之,跨文化傳播所強調的是各種不同文化的“交集”,最大限度地彌合差異與分歧。上述四項基本原則都是為了實現跨文化傳播的宗旨——不同社群與族群的和平共處、交流互鑒。孔子在兩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觀點,都精辟地闡明了跨文化傳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這種“和而不同”思想的影響之下,中華文明海納百川、包羅萬象,形成了世界文明當中最有活力的一支,至今仍然綿延不絕。正是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國的政府部門、互聯網企業和廣大網民應當為破解智媒時代的“算法利維坦”和“偏見閉環”所造成的跨文化傳播困局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
(作者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