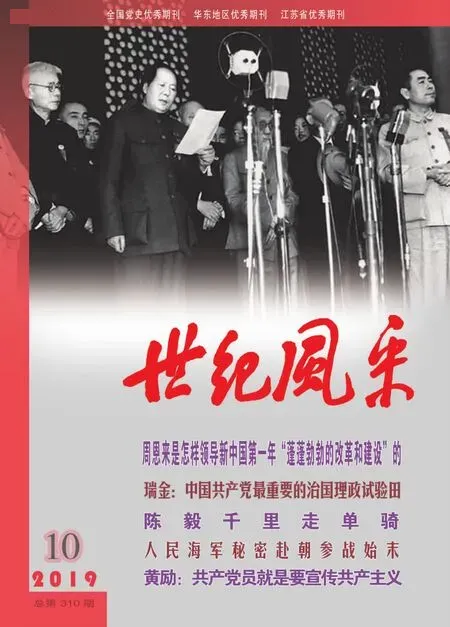魯迅病逝及葬禮紀實
吳雪晴

安葬魯迅時,上海各界為魯迅送靈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中國現代史上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的心臟永遠地停止了跳動。魯迅的逝世,在當時引起極大的震動,上海也為他舉辦了一場聲勢浩大而肅穆莊嚴的葬禮。
病情加重立遺囑
魯迅的身體本來就不好,1935年的下半年,病情開始惡化。魯迅病情惡化的原因,主要是過重刺激和長期勞累所致。1935年3月,魯迅的戰友瞿秋白在福建游擊區被國民黨軍隊逮捕,魯迅多方設法營救,原準備發起公開營救的抗議運動,但未能實現。瞿秋白犧牲后,魯迅在很長一個時期悲痛不已,身體受到打擊。他為了紀念戰友,仍扶病編輯亡友的譯文,出版了兩冊《海上述林》。1935年8月,著名共產黨人方志敏在南昌被國民黨政府殺害。在犧牲前,方志敏將自己在獄中的文稿《可愛的中國》等托人輾轉送到魯迅手中,希望魯迅通過關系將它轉交中共中央。雖然魯迅不認識方志敏,但他從這些文稿中看到方志敏對革命事業、對祖國、對人民的一顆赤誠的心,想方設法將烈士的文稿轉交給了中共地下組織。得知方志敏犧牲的消息后,魯迅義憤填膺,這更加損傷了他的身體。
為了魯迅的健康,他的許多親友勸他住院治療,或轉地療養,或到國外治療。他的朋友、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還轉達了蘇聯的邀請:請魯迅到蘇聯游歷并療養。魯迅為了留在國內更好地同敵人戰斗,一一加以婉拒。他對前來勸說的茅盾說:“疲勞總不免是有的,但還不至于像你們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說‘輕傷不下火線’嗎?等我覺得實在支持不下去的時候,再談轉地療養吧!”
1936年初,在嚴寒的氣候中,魯迅的病情加重,肩膀和兩肋開始疼痛,氣喘,發燒。魯迅的親屬和幾個好友瞞著他由史沫特萊請了一位美國醫生進行檢查。醫生對魯迅病情嚴重的程度十分吃驚。他驚訝地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了。魯迅對醫生的這一“判決”十分從容,他認為醫生再高明,也一定沒學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處方,所以也沒有請美國醫生繼續治療。
對于死亡的即將來臨,魯迅十分鎮定,他要利用極為有限的時間抓緊工作。同時,對身后之事也做了一些考慮。在病中,他寫下了隨筆《死》一文,刊于《中天》雜志1936年第2期。在文中,魯迅寫道:“……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都不寬恕。”魯迅還為自己擬了七條遺囑: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情;四、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但不可以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和他接近。
巨星隕落神州驚
1936年10月17日,魯迅的病情突然加重。這天上午,他在住所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邨9號寓內繼續撰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以紀念剛去世不久的章太炎。午后,他獨自外出拜訪日本友人,天黑時才回家。晚上,魯迅的胞弟周建人來,兩人談至夜11時,其中商談了魯迅搬家一事。
周建人走后,魯迅即上床就寢。大約是由于白天過分勞累和外出受風寒的緣故,他心情煩躁,久久不能入眠。10月18日凌晨三時半,魯迅氣喘加劇,繼而咳嗽,他彎曲著身體,雙手抱腳而坐,十分痛苦。晨6時30左右,魯迅支撐著給日本友人內山完造寫一短信,通知他“不能踐十點鐘的約”,并請他速請醫生。信送出不一會兒,內山完造和日本醫生須藤趕來,幫其注射服藥。但魯迅病情仍未有好轉。
在18日的一整天里,雖然有醫生全力搶救,但魯迅的病情仍不斷加劇。他躺在床上,喘息不止,呼吸困難,說話也困難。上午,當天的報紙來后,魯迅仍掙扎地戴上眼鏡,將報上《譯文》的廣告細細瀏覽一遍才放下,這是他最后一次接觸文字。之后,魯迅就一直處于時而清醒、時而昏迷的狀態。19日凌晨5時許,魯迅的病情突然惡化,氣喘加劇,呼吸急促,經注射兩劑強心針后,仍然無效。至5時25分,死神終于奪走了年僅55歲的一代文豪。

魯迅
魯迅去世后,悲痛欲絕的許廣平與周建人等即商議葬事安排。許廣平派內山書店的一位店員去通知胡風。胡風趕到魯迅寓所后,許廣平要胡風做記錄,記下送訃告的地名、人名。不一會兒,得到噩耗的馮雪峰、宋慶齡等人趕來吊唁。馮雪峰與許廣平、周建人、宋慶齡等人商量,決定出殯事宜由萬國殯儀館承辦,并提出魯迅是一代文化偉人,在殯儀館只是讓群眾吊唁,瞻仰遺容,不要西式、宗教的儀式。他們還擬定了治喪委員會名單,關于這個名單,從現有的史料來看,有四個版本。第一個,1936年10月19日上海《大晚報》發表的《魯迅先生訃告》中13人: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沈鈞儒、曹靖華、史沫特萊、茅盾、胡愈之、胡風、許壽裳、周建人、周作人;1936年10月20日,上海各報(包括《大美報》)刊登《訃告》中為8人:馬相伯、宋慶齡、蔡元培、內山完造、沈鈞儒、茅盾、史沫特萊、蕭參(蕭三);同一天,日本報紙《日日新聞》刊登的是8人:宋慶齡、蔡元培、毛澤東、斯梅達列夫人(史沫特萊)、內山完造、沈鈞儒、茅盾、蕭參(蕭三);在上海魯迅紀念館收藏的馮雪峰用鉛筆擬的名單為9人:蔡元培、馬相伯、宋慶齡、毛澤東、內山完造、史沫特萊、沈鈞儒、茅盾、蕭參(蕭三)。現在看來,10月19日《大美報》的13人名單肯定是錯的,它竟然包括了與魯迅素有嫌隙的二弟周作人,明顯是《大美報》想當然。其他幾個版本一是8人一是9人,核心問題是是否有毛澤東,究竟哪個名單是真實的,還需史學家們進一步研究。
魯迅逝世的消息在上海文化界迅速傳開,沈鈞儒、夏丐尊、巴金、趙家璧、孟十還、柯靈、黃源、蕭軍等魯迅的朋友、學生紛紛趕到魯迅寓所吊唁。當時國際上流行為名人遺容做石膏模型的傳統,受家屬之邀,日本雕塑家奧田杏花趕來,用一塊軟體石膏,為魯迅做面部石膏模型。下午2時,得到消息的上海明星電影公司派歐陽予倩、程步高、姚萃農、王士珍(攝影師)等人,來到魯迅寓所,拍下魯迅臥室鏡頭。此后,明星公司又拍攝了萬國殯儀館吊唁和萬國公墓安葬情況,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下午3時,由內山完造聯系安排,萬國殯儀館的“克里斯”黑色柩車開入大陸新邨,用白布裹好魯迅遺體,放入靈車中的銅棺運回殯儀館。
魯迅的逝世,不僅在上海,在全中國,甚至在外國文學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19日當晚,上海《大晚報》就刊出訃告。第二天,上海各報都刊登了訃告和治喪委員會的名單,各界人士紛紛發來唁函、唁電。為了悼念這位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遠在陜北的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連續發出三份電報,一份發給許廣平,對魯迅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一份發給南京國民政府;還有一份《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中共中央表示:“本黨與蘇維埃政府及全蘇區人民,尤為我中華民族失去最偉大的文學家、熱忱追求光明的導師、獻身于抗日救國的非凡領袖、共產主義蘇維埃運動之親愛的戰友而同聲哀悼。”指出魯迅“做了中華民族一切忠實兒女的模范,做了一個為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為世界和平而奮斗的文人模范……他喚起了無數的人們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著青年們使他們成為像他一樣的革命戰士,他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績”。
各界人士的悼念
10月20日、21日兩天和22日上午,是各界人士吊唁、瞻仰魯迅遺容時間。
19日晚,胡風、黃源、雨田、蕭軍、周文等5人在萬國殯儀館為魯迅遺體守夜。悲痛的蕭軍一直跪在魯迅的靈前,直到夜深人靜也不肯起來。20日上午9時,各界瞻仰遺容和吊唁開始。在殯儀館的門前拱門上方掛著“魯迅先生喪儀”的白色橫幅,門首設簽到處。靈堂四壁懸掛各界人士所送挽聯、挽詞。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的挽詞為:“魯迅先生不死,中華民族永生。”遠在日本不能歸國的郭沫若送來的挽詞為:“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隕淚;欽誦二心,憾無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蔡元培的挽聯為:“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茅盾當時正在家鄉桐鄉烏鎮,接到魯迅逝世的電報后立即出發去上海,但因痔瘡發作,疼痛不能行走,只得請夫人孔德沚代表他前去吊唁。郁達夫時在福州,10月19日得知魯迅逝世的消息后,連夜致電許廣平表示哀悼。翌日乘海船赴上海,在船上作《對于魯迅死的感想》,表示:“魯迅雖死,精神當與中華民族永在。”終于在22日趕上了瞻仰魯迅遺容,參加了葬禮。曹聚仁的挽聯為:“文苑苦蕭條,一卒彷徨獨荷戟;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余春。”
魯迅的靈柩原停放在殯儀館二樓的二號房間內,因吊唁的人太多,房間狹小,20日上午10時許移至一樓的禮堂內。靈堂正中掛著魯迅遺像,四周堆滿花籃,中間安放著蔡元培、何香凝等各界人士獻的花圈。靈桌上另置一張魯迅的小照片,為沙飛所攝魯迅在木刻展上與青年木刻家交談抽煙的情景。遺像兩邊供著兩瓶鮮花,上面插著兩張紙條,寫著:“魯迅老師千古,十二個青年敬獻。”下面放著一張由木刻家力群所作的木刻《魯迅像》,這是魯迅生前最滿意的一張作品。靈桌上放著魯迅生前用的一本稿紙,一個筆架,一瓶墨水和一支鋼筆等文具用品。禮堂門框上掛著由草明等16位青年作家合獻的中間有五角星的軛形鮮花拱門。門首綴以鮮花和布額,以世界語文字及拉丁字書就的兩幅巨大布額懸掛兩側;法電工人讀書班所獻的松柏牌坊,上書“失我良師”四個大字。靈堂里窗戶都垂著絨簾,燈光黝暗,氣氛肅穆。
靈桌前橫置著魯迅的遺體,與靈桌稍有距離,以供瞻仰遺容者繞遺體而過。魯迅遺體身著咖啡色綢袍,覆蓋深色綿綢被,止及胸際。他兩頰廋削,樸素莊嚴之至,就像勞累了一天后正在沉睡。許廣平手書的挽辭《魯迅夫子》放在靈床前。
來吊唁的人絡繹不絕,宋慶齡、何香凝、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以及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均親來吊唁。來得最多的是青年學生,他們大多讀過魯迅的作品,對魯迅充滿敬仰之情。據統計,20日一天前來吊唁者有團體102個,其中學校團體就有50多個,吊客5298人。21日,前來吊唁的人更多,團體增加到80多個。吊唁的人們在魯迅的遺容前站著,垂下了頭,眼眶里溢出了熱淚……
21日下午3時至4時,殯儀館為魯迅進行大殮。大殮時,在場者有許廣平、周海嬰、周建人夫婦及女兒、宋慶齡、胡愈之、內山完造、鄭振鐸、池田幸子以及治喪職員共30多人。所有人向魯迅遺體行三鞠躬禮,許廣平悲極伏地痛哭失聲,其他人也為之落淚。殯儀館職員為魯迅更衣,魯迅身著白紡綢襯衫褲,咖啡色薄棉袍,白襪、白底黑鞋,外裹咖啡色棉衾,上覆緋色面子湖色夾里之彩繡錦緞被。然后由許廣平、周海嬰扶首,周建人及女兒扶足,安置于棺內。棺為深紅色楠木棺槨,西式制作,四周有銅環,上加內蓋,半系玻璃,露出首部,供人瞻仰。22日上午,前來與魯迅做最后告別的群眾更多,殯儀館內擠滿了人,門外的馬路上更是人山人海。

宋慶齡、許廣平和海嬰在魯迅葬禮上
在吊唁期間,治喪委員會每日收到國內外大量的唁電、唁函,其中來自國外的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日本改造社、大阪《每日新聞》社、朝鮮京城大學,以及一些國際文學界知名人士。
沉痛、肅穆的葬禮
魯迅的墓地,選在上海西郊的萬國公墓。1936年10月22日下午13時50分,在膠州路上的萬國殯儀館,為魯迅舉行了“啟靈祭”。家屬、親友和治喪委員會成員等30多人肅立致哀,向靈柩三鞠躬,殯儀館工作人員將外層棺蓋封嚴。接著,由黃源、蕭軍、歐陽山、聶紺弩、胡風、巴金、張天翼等人扶靈柩出禮堂,移置柩車內,執紼者隨柩而行。
14時30分,送殯隊伍開始出發,原定的路線是經過上海的繁華地段,但由于租界當局和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的反對,只好改為沿膠州路、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地豐路(今烏魯木齊北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到虹橋路。走在最前面的,是由一批作家簽名的白布橫幅,額題“魯迅先生殯儀”六個大字為張天翼手書,由作家蔣牧良、歐陽山執掌。后為樂隊,幾十名樂手吹奏哀樂。然后為一長列人,手持各界人士送的花圈、挽聯。緊接著的是歌詠隊,唱著由冼星海、麥新等創作的悼念魯迅的歌曲。在送葬的隊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魯迅的遺像,它是由畫家司徒喬畫在一塊大白布上,其形象剛毅、堅定、栩栩如生。畫像后為魯迅的兩位侄女(周建人的女兒)恭扶的魯迅遺照,再后是靈車。許廣平、周海嬰、周建人、宋慶齡、蔡元培等人,分乘四輛汽車緊隨其后。女作家草明和雨田陪伴著悲傷的許廣平。由于海嬰年幼,不諳世事,一如往日那樣天真活潑,但有人問起他時,他回答說:“爸爸睡了,他在休息。”在場的草明事后回憶說,這個稚嫩的孩童道出了一個真理,那就是魯迅先生沒有死,他永遠活在人民的心里,活在親人和朋友們的心里!
租界當局和國民黨政府派出大批巡捕和警察對送葬隊伍進行監視。但是,沿途仍有數不清的民眾加入送葬隊伍,使隊伍從出發時的6000余人很快擴大到幾萬人。他們代表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心愿,來送別自己的導師、戰士,向黑暗統治進行示威。一路上,不斷有人散發紀念魯迅的傳單,高呼“繼承魯迅先生遺志,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
16時30分,送葬隊伍抵達萬國公墓,在禮堂前舉行了追悼會。蔡元培主持禮儀,沈鈞儒致悼詞,介紹魯迅的生平及成就。宋慶齡、內山完造、胡愈之等發表演講,批評國民黨政府迫害魯迅。在三鞠躬、默哀、挽歌聲中,救國會的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將一面白底黑字“民族魂”旗幟(“民族魂”三字為沈鈞儒手書),覆蓋在棺木上,移置東首墓地,徐徐安置穴中,蓋上石板、土。頓時,萬國公墓上空響起無數人的痛哭聲和斷斷續續的《安息歌》的歌聲。
對于魯迅的逝世,最傷心的當數許廣平女士。在魯迅安葬后,上海報紙上刊登的許廣平所寫的哀詞,就表達了她對魯迅的深厚感情。許廣平寫道:“悲哀的霧團籠罩了一切,我們對你的死,有什么話說。你曾對我說:‘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曉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娛樂,總是工作,死的前一日還在執筆。如今——希望我們大眾鍥而不舍,跟著你的足跡。”
關于喪事的幾個問題
魯迅喪事籌辦過程中,有幾件事情特別值得一提。
第一,魯迅逝世后,各界人士送來大量的挽聯、花圈,這其中絕大多數是魯迅的好友與戰友,但也有少數魯迅生前曾經批判過的人,有的甚至是敵人。魯迅逝世前曾撰文痛批過徐懋庸。得知魯迅逝世的消息后,徐異常悲痛,他認為他始終把魯迅視為革命的朋友,是魯迅誤會了他,魯迅總有一天會諒解他的。現在魯迅逝世,這個機會再也不會有了,于是自撰挽聯:“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他本想將挽聯親自送到殯儀館,但有朋友擔心他去了會遭到吊唁群眾怒視,他便托曹聚仁的夫人將挽聯帶到殯儀館。最后,徐懋庸鼓足勇氣,還是去了殯儀館,在魯迅的遺體前默哀了一分鐘。曾和魯迅進行過論戰的周揚、夏衍等人,獲知魯迅逝世的消息后,也感到十分悲痛。因魯迅的家和殯儀館都有國民黨特務監視,他們不能親去吊唁,故派沙汀、艾蕪代表他們去向魯迅的遺體致哀。
對于魯迅的逝世,國民黨要人表現出復雜的心態。上海市長吳鐵城到靈堂致哀,并送了花圈。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也給魯迅送了挽聯:“一代高文樹新幟,千秋孤痛托遺言。”
第二,喪事活動中的重大問題,都由馮雪峰代表中共黨組織與治喪委員會、許廣平等人協商,治喪辦事處由胡風負責。胡風是魯迅生前最信任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在葬禮中決定喪事程序,如群眾瞻仰遺體的時間安排、靈前守靈人的名單等。蕭軍實際上做了葬禮活動的“總指揮”,黃源、雨田、周文、孟十還為“靈前司事”。魯迅生前的最后幾年在上海沒有固定工作,一直靠稿酬度日。雖然魯迅稿酬不薄,但開銷也大,沒有多少積蓄。再加上根據遺囑又不收禮,故殯儀館費用、購買墓地等經費,原由沈鈞儒表示由救國會負擔。據胡風回憶,救國會后因種種原因沒有出錢。喪葬所需經費二三千元(其中魯迅墓穴價格為580元)全由許廣平負擔,其來源是魯迅生前被蔡元培聘請到中央研究院任職的薪水(魯迅并未就職,但蔡元培薪水照發,以此方式資助魯迅),這筆錢魯迅一分未動,全部存起來了。這次被許廣平用在了魯迅的喪事上。魯迅的棺木是宋慶齡、孔德沚、王蘊如(周建人的夫人)陪同許廣平去挑選的,跑了幾家棺木店后由許廣平選中一款900元的西洋式棺木,此款為宋慶齡所出,因此魯迅棺木實際上為宋慶齡所贈。魯迅的墓地由沈鈞儒聯系,他對公墓負責人說,死者是了不起的偉人,故不講迷信求風水,墓地四周要留有空地,以便千秋后代舉行悼念活動。
魯迅的墓碑簡陋:墳墓只是個小小土堆,后面樹一塊梯型水泥墓碑,高71.2厘米,頂寬31.5厘米,底寬58厘米。碑的上部鑲著高38厘米、寬25厘米的瓷制魯迅像,下部刻著橫寫的“魯迅先生之墓”字樣,字體幼稚而工整,乃是當時僅7歲的周海嬰所寫。為這事,馮雪峰曾安慰許廣平:將來等革命勝利后,我們一定為周先生舉行一次隆重的國葬。1947年9月,魯迅的墓地進行了擴建,面積達到64平方米,用花崗石圍成正方形,墓槨后是野山式圓頂墓碑。碑面嵌有高66厘米、寬60厘米的黑石塊,上面鑲著橢圓形的瓷質魯迅像,像下橫寫著“魯迅先生之墓”六個大字,下面還有兩行小字:“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紹興”“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卒于上海”,均為陰文金字。此碑文為魯迅的胞弟周建人書寫。1956年,有關方面舉行隆重儀式,將魯迅靈柩從萬國公墓遷葬上海虹口公園,并在墓前塑高2.1米魯迅銅像。他左手執書,右手擱在椅子的扶手上,面容堅毅而親切,目光深邃,炯炯有神,體現了魯迅的精神風貌。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了“魯迅先生之墓”六個大字,被刻在一塊高1米、寬0.8米的花崗石上,遠遠望去,雄健有力,金光閃爍。

魯迅出殯,巴金、胡風等16人抬棺
第三,關于魯迅逝世的病因,當時一直認為是死于肺結核。1984年2月22日,上海魯迅紀念館邀集部分我國著名的肺科、放射科專家,對魯迅生前所攝的最后一張X光片(1936年6月15日拍),以及魯迅的病歷,進行了研究。最后專家一致認為,魯迅的肺結核病屬中等程度,這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左側肺大泡破裂,使氣體進入胸膜腔,引起自發性氣胸,壓迫肺和心臟而死亡。這個結論公布后,國內曾有人懷疑魯迅的日本醫生須藤故意誤診和處置不當,甚至有可能暗害魯迅,引發了一場風波。但絕大多數魯迅研究專家和魯迅之子周海嬰表示,在當時的醫學條件下和須藤醫生的醫療經驗來看,須藤醫生的治療沒有大的問題,尚無證據證明須藤暗害魯迅,這才平息了一場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