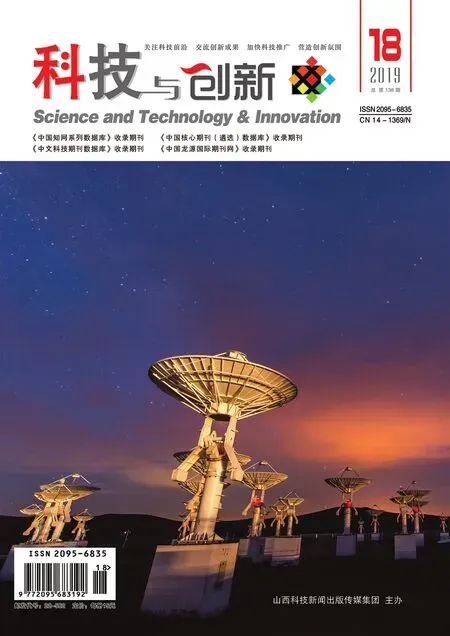基于SIR模型的人群集聚恐慌心理傳播研究*
李秋香,謝瀟然
基于SIR模型的人群集聚恐慌心理傳播研究*
李秋香,謝瀟然
(浙江財經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人群集聚恐慌是踩踏事故發生人員傷亡的主要原因。嘗試將傳染病SIR模型應用于人群集聚恐慌心理的傳播研究,深入挖掘人群集聚恐慌心理傳播的內在機理,并據此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以期降低人群集聚風險和減少事故損失。
疾病傳染模型;人群集聚;恐慌心理;風險管理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外大型賽事活動、群眾性公共活動數量日益增加,規模也在不斷擴大。群體性公共活動一般具有活動場所公開、空間結構特殊、參與人群密度大等特點,一旦發生意外,極易發生群傷的人群擁擠踩踏事故,這是城市群體性活動可能遭遇的諸多突發事件中預防難度最大、破壞性最強的傷亡事故之一[1]。近年來,世界各個國家均發生過影響惡劣、死傷嚴重的擁擠踩踏事故,不僅給人們帶來慘痛的回憶,也對社會秩序和城市形象產生重要的影響。2015年新年前夕,上海外灘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擁擠踩踏事故,造成了多人傷亡的跨年慘劇[2]。中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將面臨著大人流帶來的群體性突發事件風險的嚴峻考驗,類似踩踏事故的城市公共安全問題還會再次出現。及早排查并認真分析人群集聚各種風險發生的特點、規律和發展趨勢,對從根源防范、規避、降低和控制風險具有重要的意義。
1 國內外研究現狀
近年來,城市群體性踩踏事故不斷發生,引起了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人群集聚是擁擠踩踏事故中人員傷亡的主要原因,是指在人群密度高到行人難以移動時,擁擠力在人群傳播和集聚的現象,目前國內外學者們主要從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網絡輿情、主體博弈等視角對踩踏事件的內涵、特征、起因、發展過程進行研究。研究表明,人群密度大、產生群集現象是事故發生的直接原因。任常興等基于事故分析方法,通過定義“群集指數”來表征人群高度聚集量,詳細分析了影響公共場所人群擁擠踩踏事故的多種安全因素,并指出該類事故以人群高度聚集為條件,因此要加強人群密度管控。寇麗平[3]研究結果同樣得出群集現象是導致群體性擠踏事件的直接原因,并指出恐慌的出現和擴散是造成大量死亡的心理原因,因此建議開展對公眾的安全教育,訓練能在緊急情況下快速、科學反應的人員隊伍。張青松等[4]借助風險理論、人群行為科學理論和事故突變理論提出了人群擁擠踩踏事故風險包括“自由移動—滯留—擁擠—踩踏”四階段的理論模型,對人群聚集相關事故形成演變規律作了初步探索。ALBERT等通過廣泛的文獻調研發現外界社會環境是群體性踩踏事件初始引發的最顯著影響因素。 最新研究表明,人們的從眾心態則是這一惡性群體性事件爆發的深層次原因。劉澤照等[5]采用基于加權平均算子的模糊數學方法得到踩踏風險評價的結果,并以上海“12·31”踩踏事件為例進行綜合分析。
綜合國內外關于人群擁擠踩踏事故的文獻發現,多個領域學者圍繞密集場所人員動態和規律開展了大量研究,為緊急情況下的人員安全管理提供了科學依據,但缺乏對突發事故下個體心理規律的研究資料。情緒對人的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激動情緒和恐慌情緒是影響聚集人群行為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立足于人群的心理因素,嘗試從動態化的角度探究人群的心理變化對疏散結果的影響,將經典的傳染病SIR模型應用于人群擁擠恐慌心理傳播研究,闡釋人群擁擠受恐慌心理影響的規律,并在此基礎上制定科學的風險應急防范策略。
2 基于疾病傳播模型的人群集聚行為研究
2.1 傳染病模型與人群擁擠恐慌心理傳播
SIR模型是傳染病模型中最經典的模型,其中S表示易感者,I表示感染者,R表示移出者。模型中把傳染病流行范圍內的人群分成三類:S類,易感者(Susceptible),指未得病者,但缺乏免疫能力,與感病者接觸后容易受到感染;I類,感病者(Infective),指染上傳染病的人,它可以傳播給S類成員;R類,移出者(Removal),指被隔離,或因病愈而具有免疫力的人從而退出該系統。
在人群集聚突發擁擠的過程,部分人會迅速產生恐慌心理,周邊群體受從眾行為影響也會產生恐慌,并以一定概率繼續傳播至外圍。同時,另一部分人心理素質較強并能繼續保持鎮定,則不會受其感染和繼續傳播。對比兩者的傳播過程可以發現具有相同的傳播機制:在SIR模型中,已感染者(I)可以將病毒傳染給易感染者(S),相當于人群擁擠中恐慌人群會將恐慌心理傳染給心理素質較差的人群,而心理素質較強并能不受傳染的人相當于移出者(R);已感染者不會將病毒傳染給具有免疫力的易感染者或已病愈的已感染者,相當于人群擁擠中恐慌人群不會將恐慌心理傳染給心理素質強的人以及解除擁擠狀態的人;易感染者被治愈后會獲得免疫力,相當于人群擁擠中恐慌人群脫離擁擠后將不會受到該次集聚事故對其身體繼續擁擠的影響。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用傳染病SIR模型對人群集聚的恐慌心理傳播進行研究。
2.2 模型構建
假設某一時間節點、某一固定場所的總人數為。根據SIR模型可將其分為三種狀態:易感狀態、傳播狀態和免疫狀態,分別對應在時刻接收到傳染信息的人群()、受到感染的人群()、接收到傳染信息但不會被感染的人群()。這三類人群在易感狀態、傳播狀態和免疫狀態之間的轉換不僅依賴于自身的狀態,也受到周圍人群所處狀態的影響。假設初始時刻易感者、傳播者、免疫者的比例分別為0,0,0>0,且有()+()+()= 1。
人群中不受恐慌影響的移出者數量應為:

SIR基礎模型用微分方程組表示如下:
其中,傳播系數是指單位時間內心理恐慌的個人將恐慌心理傳染給正常人群的數量比例,治愈系數是指單位時間內心理恐慌人群脫離恐慌狀態的數量比例。
3 結果分析
為了更好地觀察人群擁擠中恐慌心理隨時間變化的規律,本文在MATLAB平臺上進行仿真,通過設定一組符合實際情況的參數值來觀察三種人群隨時間變化的狀況,以驗證理論的正確性。由于初始狀態下傳播人群所占比例較小,因此設(0)=0.02,而易感人群的比例較大,設(0)=0.98,(0)=10,傳播系數為=0.8,治愈系數為=0.3。仿真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各狀態人群所占比例的變化趨勢圖
從圖1中可以看出,易感狀態()隨時間遞減,表明其受到人群集聚恐慌心理轉化為傳播狀態,易感狀態人群不斷減少;傳播狀態()隨時間變化,先增加后減少,由最初的20%左右增加到50%左右,呈現出大量的恐慌人群態勢,最后降為0,表明事件發生過后,秩序恢復正常。
3.1 傳播參數a的影響分析
當傳播參數改變時,不同狀體人群所占比的變化如圖2所示。從圖2中可以看出,當=3時,()的增加和下降相較于=1時更快,且更早獲得峰值,其比例更大;當=3時,()的下降速率相較于=1時更大,且更早獲得峰值,其比例也更小。由此可見,在人群集聚恐慌心理傳播過程中,值越高,即其他人群對易感人群的敏感度越高,更容易受到恐慌心理的影響,擁擠程度更加嚴重,同時易感人群數目下降的速度也更快。在實際情景中,傳播參數的值與事故發生地環境結構、空間設計等固有屬性有密切關系。在公共場所的進出口或封閉空間中人群集聚的地方,應當進行科學規劃、合理設計。
3.2 治愈參數b的影響分析
當治愈參數改變時,不同狀體人群所占比的變化如圖3所示。從圖3中可以看出,當=0.1時,()的增加和下降相較于=0.3時更快,且更慢獲得峰值,其比例也更大,下降到一個穩定值所需時間也明顯更長;當=0.1時,()的下降率相較于=0.3更大且更早到達低值。由此可見,恐慌心理傳播過程中,值越低,即擁擠人群的治愈率越低,擁擠消散的速度越慢、難度越高,擁擠程度更加嚴重,同時易感人群數目下降的速度也更快。在實際情景中,治愈參數的值與事故發生管理策略、引導疏散有密切關系。在易出現人群集聚風險的地方,應做好風險評估和應急疏散預案。

圖2 不同傳播參數下各狀態人群所占比例的變化趨勢圖

圖3 不同治愈參數下各狀態人群所占比例的變化趨勢圖
[1]楊典.特大城市風險治理的國際經驗[J].探索與爭鳴,2015,7(3):33-34.
[2]盧文剛,蔡裕嵐.城市大型群眾性活動應急管理研究 ——以上海外灘“12·31”特大踩踏事件為例[J].城市發展研究,2015,22(5):118-124.
[3]寇麗平.群體性擠踏事件原因分析與預防研究[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1(4):16-22.
[4]張青松,劉金蘭,趙國敏.大型公共場所人群擁擠踩踏事故機理初探[J].自然災害學報,2009,18(6):81-86.
[5]劉澤照,楊帆,黃杰.大型公共活動踩踏事故模糊風險評估應用研究——以上海“12·31”踩踏事件為例[J].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7(2):33-38.
D631.4
A
10.15913/j.cnki.kjycx.2019.18.015
2095-6835(2019)18-0038-03
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臺風災害多主體聯動響應:行為機理、系統仿真與管控機制”(編號:Q19G030026);杭州市哲學社科“基于大數據的城市人群擁擠的風險評估及預警機制研究”(編號:M17JC032);浙江財經大學虛擬仿真實驗教學項目(編號:10122419005)
李秋香(1986—),女,博士,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城市治理與公共政策仿真。
〔編輯: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