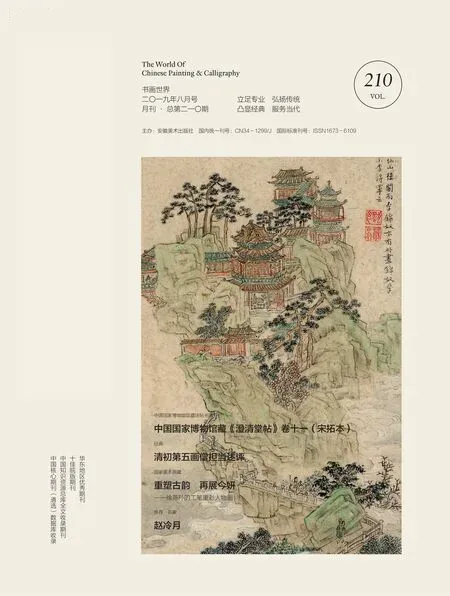自然之變— 李延智訪談錄
劉笑(以下簡稱“劉”):從您第一次獲獎到現在的創作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這十幾年的探索過程已經形成了自我的獨特筆墨語言體系。您能談一談這個探索過程的階段和變化嗎?
李延智(以下簡稱“李”):也就是近十年吧,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開始探索在創作中融入我過去生活中有關藝術的綜合積淀和我對繪畫語境的新認知,并找到了通過中國畫語言進行表達的方式。通過這樣的一個出口,我開始訴說想要說的東西。因為我以前畫過西畫,做過設計、攝影、編輯等工作,和美術都相關,也算是一種多元的積累。我從2004年開始參加省級美展,當時集中創作了一批大畫參賽。那年對我來說挺幸運的,也算是厚積薄發吧,獲得了山東省的一等獎。那時我三十出頭,獲此榮耀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激勵。接著,在下半年我開始準備第十屆全國美展的作品,很榮幸,作品入選了山東省展,對我來說也是一個不小的成績。也就是這幾次獲獎,讓我的創作欲望和信心增強了很多。那幾年,我在創作中追求和探索的方向就是色彩、夢幻、超現實主義、神秘感。2005年,我的作品入選了全國中國畫大展并獲優秀獎,那時候能入選中國美協主辦的展覽對我來說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是一種動力。十年前算是無知者無畏,比較大膽,敢畫,一張兩米見方的畫只要找對了感覺,幾晚就可以畫出來。但是現在來看那些作品,還是有不少欠缺之處的。

1.李延智 太行山寫生45cm×68cm2017

2.李延智 湛山寺晨鐘45cm×68cm2017
劉:那是一種什么樣的啟發轉變成了現在這種繪畫風格?
李:從當時那種風格、筆墨語言以及自己的藝術觀,演變成現在的山水畫風格并不是跳躍式,而是隨著年齡、閱歷、修養的增長,以及對中國畫的理解和認識的加深,逐漸向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演變的過程。一開始的作品雖然看上去很新,但是基礎是不牢的,要不斷地填充、豐富。現在,我對中國畫的理解比過去要深刻得多。2006年的時候,我創作的勁頭還很足,每年中國美協主辦的大展一個不落,那一年我獲得了在深圳舉辦的第一屆城市山水大展的優秀獎,那張獲獎作品也是我的重要代表作品,傾注了很大的心力。“城市山水”是我那年的一個課題,也是在我繪畫風格演變過程中的一個新的嘗試。我當時住的地方在千佛山下的羊頭峪,那幾年房地產開發,山上全蓋了房子,我結合身邊的場景,把西方的一些現代構成方式、抽象派、超現實主義、禪宗的思想融入畫面,整個畫面看上去極富現代氣息,但是筆墨上還是運用南派山水溫潤的筆法。2007、2008這兩年是我的城市山水課題結束以后的一個積淀時期,雖然這兩年沒有獲得什么獎,但是我一直沉下心來研究雪景山水。雪景山水古人畫過很多,現代也有“冰雪畫派”等。但在2009年之前,當時山東那一撥畫家里很少有畫雪景山水的。
也許是一種機緣巧合吧,我當時畫室搬到十六里河,開車往南一會兒就是臥虎山水庫和泰山附脈,和自然山水很親近。一下雪我就沿著南部山區轉,因為我本身也特別喜歡攝影采風,在天氣不太惡劣的情況下,現場也畫過不少寫生,慢慢有了對于雪景的理解和積累。我認為雪后的自然天地,真是簡練到了極致,特別符合中國畫的審美特點,一切繁雜的色彩統統都被融入白色之中,形成了一種統一的黑白關系。這種天公之美令人驚訝,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我把所學集中到雪景山水的創作中,畫了很多大畫、小畫,寫生、創作。但是這種實踐可以算是現實主義的,我以前的想法和經驗可能在雪景山水創作中用得很少了,但是多年積淀下來的筆墨的性格是丟不掉的。到2009年又是五年一屆的全國大展—第十一屆全國美展,當時濟南市美協開動員會,希望我們年輕畫家積極創作,參加美展,在省美協、市美協的座談會上,孔維克主席和韋辛夷主席說:“看你這兩年對雪景山水的探索有一些收獲,雖然還沒有一個完善的體系,但是面貌很新,希望能夠沿著這個題材畫下去。”這讓我備受鼓舞。我把幾年來積累的素材集中起來,先后畫了《雪潤無聲1》《雪潤無聲2》。《雪潤無聲1》入選了第十一屆全國美展,獲得山東省美展的一等獎,《雪潤無聲2》入選了青年畫家都比較看重的金陵百家畫展。經過兩年的沉淀期,2009年雪景山水給我的回報是很豐厚的。獲了這幾個獎后,我的筆墨語言體系慢慢成熟。總而言之,筆墨的演變不是一下子變化的,而是通過不斷的探索,積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找到一個突破點,直到發現一個適合自己去表達的題材,這是一個自覺選擇的過程。
劉:從城市山水到雪景山水,這樣一個逐漸向寫實轉變的過程是基于一種怎樣的思考?
李:中國畫的巔峰期—宋代比較重視純粹繪畫的寫實性,當然這個寫實是相對的,最終體現的還是整體畫面的意境。特別是山水畫,對自然實境的觀照與敬畏都是那個時期的特有審美。我心中的雪景山水,是對這種自然之美、天賜之美的表述,是老天給了人間這么一片美景,如此之美真是舍不得增一筆也舍不得減一筆,如此的美我只是用筆墨或者色彩去呈現,不能說再現,而是呈現,呈現這里面就包括了表現主義、理想主義、完美主義,就是把你看到的自然美景和內心對于美的感受,通過筆墨建立起內心與自然的交流,并產生共鳴,集中展現于畫面中。我的畫里把各種各樣的山水技法簡化,使筆墨語言盡量純粹,符合了中國畫傳統的“尚簡”精神。中國畫的筆墨本身就是一種造型,只是把各種各樣的筆墨符號根據畫面的需要呈現出來。
劉:您的一些速寫的小稿和寫生作品能看到一些水彩畫的感覺和痕跡,還是有很強烈的西方造型的影響。

3.李延智 雁蕩山寫生68cm×45cm2015
李:對于很多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從事中國畫創作的年輕畫家來說,這幾乎都是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實際上,我在山東藝術學院上學的時候,包括我在清華美院進修的時候,西畫對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這是接受學院訓練的畫家難免的,把它拋在一邊不現實,也是浪費。這里面有著我對傳統的理解。國畫、書法的筆墨線條和經典作品是傳統,但是西方的素描、構圖,文藝復興及古典主義的經典也是傳統,這是一個大的傳統的概念。所以,速寫也好,水彩也好,油畫也好,水粉也好,我覺得只要畫面需要,合理地運用中國畫的筆墨語言和色彩,保持中國畫的審美特質,對我們的創作都是有益的。
劉:您剛才談到了根據畫面的需要運用筆墨,能以您的寫生為例,具體地談談嗎?
李:寫實與寫意、具象與抽象都是相對的。比如寫生時看到的建筑,按照西畫的觀察方法是具有透視的直線造型,雖是常態但缺乏繪畫的想象力,而中國畫線性的張力和曲線之美更符合我們筆墨表達以及繪畫的需要。因此,畫面選擇平面結構會顯得更有意味。繪畫是需要意料之外的東西,需要打破常態的。比如我的泰山寫生,畫面需要錯落有致,需要把很多元素融合,房子、路、樹都需要整合進畫面,甚至把它們重新組合,畫家做的余地就大了,這是一種情況。再看我畫的泰山大觀峰,就是用比較寫實的手法,因為大觀峰它本身就是一個很有繪畫意味的山體,組成的石塊已經很豐富了,只要筆墨畫得有意味,本身就很美。如果過于表現的話,反而會失去原貌的自然之美。因此寫生本身就是考驗畫家選景、對景的理解,以及如何將諸多元素以秩序化的方式融合到一個畫面中,并且是快速的、即興的。這需要綜合修養的能力,所以實與虛是相對的,寫生本身也是一種高級的創作過程。

4.李延智 扎尕那畫境90cm×34cm×42018
劉:您剛才提到雪景是一個被簡化了的自然物象,表現在畫面中需要一定的處理手法,比如您說的“純粹的筆墨”“留白”等,您能具體談談自然物象與筆墨語言的對應性問題嗎?
李:這個問題我在創作中深有體會。想象一下,大雪在一夜之間把整個天地都覆蓋了,當你打開窗戶時,呈現在眼前的是非常簡的、亮的景象,你會訝異原來世界還可以是這樣的。中國畫崇尚留白,我有個齋號叫“亦白齋”,我畫雪景以后,對空白在一個畫面里起的作用深有體會。空白是非常高級的元素,它本身是一種空間,也是一種造型。之前有的人畫雪景使用一些材料和方法,用一些洗衣粉或白粉去畫白,但我覺得留白永遠是最高級的。我更喜歡用“布白”這個詞,用心去營造和布置,讓這塊“白”留得合理。畫面細節可能是豐富的,但我覺得那塊“白”該留的時候一點都不敢碰,就好像每個人心中最純潔、最純凈的地方一樣,一定要把它留得合理、漂亮。雪景山水從大的方面來說是一種“簡”,用線把整個畫面撐起來,包括不是雪景的寫生畫,水墨的留白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前畫畫的時候總想著畫滿,實際上如果能用更精煉的、更簡潔的手法就把畫面烘托出來,我覺得是一種更上層的境界。
劉:所以“簡”的畫面對線條的要求更高,是這樣嗎?
李:是,我的畫面比較傾向于一種柔和、溫婉的線,或者說是柔中帶剛的、具有彈性的、蒼澀的線。或濃或淡地畫出縹緲的味道,追求一種靈性、一種動感。這是我對線的追求。作為畫家來講,我有時候并沒有想那么多,只是追求一種繪畫的快感,筆與紙接觸的瞬間—暢快、舒服、行云流水。當然,這些筆觸和線條一定要打動人才行,打動自己才能打動別人。這可能就是所謂的繪畫性,作品一定要有繪畫性。
劉:您所傾向的這樣一種柔和、溫婉的線條,我們可以從傳統山水畫中的荷葉皴、披麻皴中找到依據,您是否也有意識地吸收了這一傳統?
李:傳統繪畫的經典是前人智慧的藝術結晶,是他們根據自己對筆墨的理解總結的一些藝術符號,如果我們在創作中直接照搬古人的東西,肯定不完全符合自己所看到的物象特性,也不符合自己的筆性和心性。但我提倡的是什么呢?傳統在臨摹學習之后,裝在心里、腦子里,在之后的創作中再去印證它、對照它,古人將山石的質感轉換成筆墨并總結為皴法,華山像荷葉皴,太行山像折帶皴,泰山、黃山有一些披麻皴的味道……所以,從自然中我們能夠證實古人的藝術從來都是生動的,不是憑空造出來的。因而我們要用自己的眼睛和雙手去發現、去表達符合自己審美趣味的形式。所謂的寫生,就是真正把生生的、生澀的、有生命的東西轉化到畫面中去,讓它成為一個真正有生命的東西,這樣得來的畫,更鮮活,更能打動人。同時,在創作中,我們也要有膽量去嘗試一些新的畫法。總之,老天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可以拓展的繪畫空間的。
劉:現在您在畫面中加入一些人物和動物,是追求一種動靜的對比嗎?
李:山水畫的范圍是最廣泛的,在山水畫里面可以盡情地體現人物、建筑、走獸,包括抽象的生靈或者充滿神話色彩的故事。我也畫過超現實主義的,把樹變形成人體,帶有鬼神主義色彩,有點“聊齋”或者“阿凡達”的意思,簡言之,山水畫的包容性非常大。我現在在畫面中加入一些動物、神話人物、神獸等,是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是一種調和,讓畫面更豐富,讓山水畫有更多的可能性,也讓我有新的動力和激情畫下去。所以畫畫有時候是給別人看的,也是給自己看的,最終傳達的還是自己的修為。我今年連續畫了很多有馬的山水,馬的這種結構很美,嫁接到山水畫中,非常和諧,非常生動,讓畫面充滿了生機。

5.李延智 溪山新旅220cm×180cm2019
劉:我覺得這些元素也讓畫面增加了古典味道,饒有趣味,不知道這種古意是不是也是您一直尋找的方向?
李:趙孟說畫貴有古意。今天我們畫中國畫,如果畫面有“古意”,是一種高格調的體現。“古意”就是追求一種古雅的格調,這是很難能可貴的。“古意”是整體畫面氣息的營造,帶給人一種很寧靜的心理狀態。我對雪景山水的視覺效果追求的是古意的、寧靜的、古遠的、深邃的氣息。真正的好畫沒有新舊之分,只有好壞之分。所以說,能夠體現出高古的格調本身也是很現代的,因為經典是可以永恒的。
劉:您怎樣評價現在的創作與生活的關系和狀態?
李:近幾年的展覽特別多,這是以前所沒有的,我也深有體會,有點應接不暇的感覺。畫家產量是有限的,這對畫家也是一個考驗。我覺得作為一個有責任的、態度認真的畫家,展覽應有自己的選擇權,盡量參加嚴肅一些、學術性更強一些的展覽。當然,展覽對個人的技藝、畫家之間的交流、市場和藏友之間的溝通都是有幫助的。這對畫家來說也是一種鍛煉,讓畫家更勤奮了,也是好事。

6.李延智 大珠山雪晴34cm×90cm2018

7.李延智 莫奈花園雪后34cm×90cm2018
劉:您對未來的創作有新的方向和想法嗎?
李: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對中國畫的理解和中國傳統文化修養的加強,以及對事物看法的變化,創作會隨著這個過程自然而然地變化。它不是跳躍的,而是漸進的,是一個自我完善的過程。過去講四十不惑,對我來說,我覺得應該到了一個技法、知識、修養都相對完整并形成體系的時候了,是能出作品的年齡了。過去的各種想法、思考也都試驗過了,可以說是“五谷雜糧”已經吃過了。常言道:“人間正道是滄桑。”在經典傳統的基礎上往前發展那么一點點都很難得,所以應該回歸到傳統修養的這條大道上,把這些營養元素和傳統永恒美的元素更好地結合,不光看起來是新的,而且里面也有醇厚的東西,就像是老酒沉淀出的香味。好好地讀書、寫字、畫畫,讓自己的身心真正沉靜下來,去認真研究中國畫的根脈。所以,我下一步的任務更艱巨了,人生如白駒過隙,怎么把自己的時間分配地更合理,用到有用的地方去,是真的需要下大功夫的。當然,這是一段自然而然變化的生命旅程,順其自然,盡心力,不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