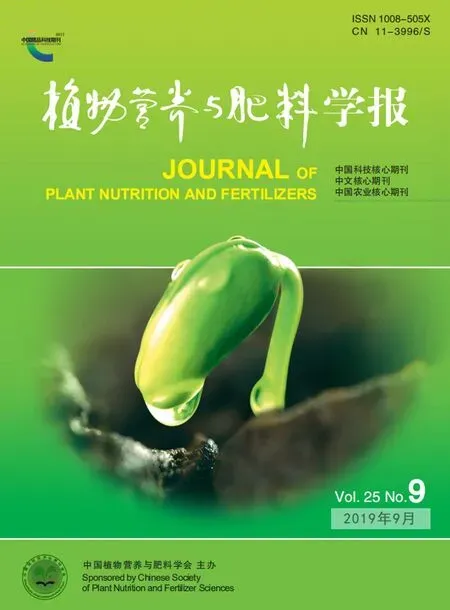氧化/磺化腐殖酸對潮土中Cu、Zn、Fe、Mn有效性的影響
孫靜悅,袁 亮,林治安,張水勤,趙秉強,李燕婷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農業部植物營養與肥料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81)
土壤對植物必需營養元素尤其是微量元素的供給,不僅與土壤中該元素的總量有關,更取決于其生物有效性,而營養元素的生物有效性取決于其在土壤中的化學存在形態,其中,以溶解態和可交換態存在的元素最易被植物吸收利用,是土壤中短期內最具生物有效性的組分[1-3]。我國華北地區的石灰性土壤具有較高的pH值和碳酸鈣含量,導致土壤中微量元素的有效性不高[4-6]。
腐殖酸作為天然有機高分子化合物,含有羧基、羰基、羥基、醌基等多種官能團,具有較高的反應活性,廣泛存在于褐煤、風化煤、泥炭等自然資源中[7-8]。當腐殖酸物質進入土壤后,能夠通過離子交換、吸附、絡合、螯合等反應來影響土壤中微量元素的生物有效性[9-12]。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關于腐殖酸與微量元素有效性方面的研究結論不一,有研究表明,腐殖酸能夠增加土壤中微量元素的有效性,促進植株對微量元素的吸收[13-18],但也有研究表明腐殖酸能夠與微量元素形成沉淀,從而使微量元素的生物有效性降低[9,19-21],有研究者認為研究結論之所以不一致可能與腐殖酸本身的來源或結構不同有關,腐殖酸中參與反應的官能團種類、數量和性質上的差異會導致絡合穩定性不同[22],進而影響微量元素的有效性,將腐殖酸進行人工改性是獲得不同結構腐殖酸的快速手段,氧化和磺化是較為安全環保的腐殖酸改性方式且不引入雜質[23]。然而,改性腐殖酸提高土壤微量元素有效性的效果研究還較少,鑒于此,本研究以風化煤腐殖酸為原材料,通過氧化和磺化技術獲得改性腐殖酸,比較了改性前后的腐殖酸材料對土壤微量元素有效性的影響,結合腐殖酸的結構特征分析產生這些效果差異的原因,以期為開發提高微量元素有效性的腐殖酸功能材料提供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供試材料
1.1.1 土壤 供試土壤采自中國農業科學院德州鹽堿土改良實驗站禹城試驗基地連續三年未施用任何肥料的勻地試驗場,土壤類型為潮土,質地為輕壤。采集0—20 cm耕層土壤,自然風干,過1 mm篩,混勻備用。其基本理化性質如下:pH 7.98、有機質10.06 g/kg、有效銅 1.32 mg/kg、有效鋅1.73 mg/kg、有效鐵5.46 mg/kg、有效錳2.09 mg/kg。
1.1.2 腐殖酸 供試腐殖酸為風化煤腐殖酸(以下簡稱腐殖酸,HA),產地內蒙古。采用4因素3水平正交試驗設計進行腐殖酸的雙氧水氧化改性及亞硫酸鈉磺化改性,分別獲得研究目標產物氧化腐殖酸(YHA)和磺化腐殖酸(SHA)。HA、YHA和SHA的基本性質見表1。
1.2 試驗方法
每個腐殖酸設30、100、300 mg/kg三個添加量,以不施任何腐殖酸為對照,共10個處理。將不同腐殖酸(HA、YHA、SHA)分別按不同用量與500 g干土混勻,裝入培養瓶中,調節含水量至田間持水量的60%,置于25℃人工氣候箱中進行恒溫培養,并保持土壤濕度恒定,每個處理重復3次。
分別在培養后第3、7、15、30、60天采樣,所采土壤樣品自然風干,研磨過1 mm篩。土壤pH(土水比1∶2.5)測定采用電位法;有機質測定采用K2Cr2O7-H2SO4消化法;土壤有效Cu、Zn、Fe用pH 7.30的0.005 mol/L DTPA浸提劑提取,有效Mn用1 mol/L的中性NH4OAC溶液提取[24],各提取液中相應有效元素含量均用電感耦合等離子發射光譜儀(ICP-AES)測定。

表1 腐殖酸基本性質Table1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humic acids
1.3 數據處理
分別采用Origin 9.0、SPSS17.0和Duncan新復極差法對數據進行作圖和統計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氧化和磺化改性對腐殖酸結構的影響
由圖1可知,三種腐殖酸樣品的譜線峰型在波數4000~1250 cm-1段整體相近,在波數1250~500 cm-1段差異較大,都有以下4個主要紅外吸收峰: 1)1580 cm-1波長處,芳烴C=C伸縮振動、羧基對稱伸縮、N-H彎曲變形和C=N伸展;2)1380 cm-1波長處,酚羥基中的O-H和C-O伸縮、烷烴 -CH2和-CH3中C-H變形和COO-的反對稱伸縮;3)1108 cm-1波長處,飽和醚、多糖或多糖類物質的C-O伸縮;4)622 cm-1波長處,炔烴C-H彎曲振動。進一步分析可知,同一官能團在不同樣品中振動強度存在一定的差異。與腐殖酸(HA)相比,氧化腐殖酸(YHA)在1580 cm-1、1380 cm-1波長處振動強度略有增加;而磺化腐殖酸(SHA)在1108 cm-1、622 cm-1波長處吸收峰明顯增強,并在1193 cm-1處產生磺酸基反對稱伸縮振動,在971 cm-1處產生硫氧S-O伸縮。由此可見,氧化和磺化均改變了腐殖酸結構中官能團的數量(羧基,酚羥基),而磺化還增加了官能團的種類(磺酸基),總之,磺化改性對其結構影響較大。

圖1 腐殖酸的傅里葉變換紅外圖譜Fig.1 FTIR spectra of humic acids
由表2可以看出,所有腐殖酸樣品結構中均以芳香碳(110~145 ppm)含量最高,以該種形式存在的碳占全部含碳官能團的59.40%~63.35%,烷基碳(0~63 ppm)以及和糖、多糖相關的氧烷基碳(63~110 ppm)之和占全部含碳官能團的22.52%~31.72%,其次為酚羥基和羧基碳(145~190 ppm),占全部含碳官能團的8.88%~15.0%;酮基/醛基碳(190~220 ppm)占全部含碳官能團的比例最小,在1%左右。同一官能團在不同樣品中的相對含量也存在較大的差異。HA經過氧化改性后芳香碳含量降低4.29%,烷基/氧烷基碳增加2.31%,同時酚羥基碳、羧基碳、酮/醛基碳含量增加;磺化使腐殖酸芳香碳含量降低3.95%,烷基/氧烷基碳增加9.19%,而酚羥基碳、羧基碳、酮/醛基碳含量明顯減少。總體來看,YHA與HA的結構具有較大的相似性,而SHA與HA的結構差別較大。
2.2 不同腐殖酸對潮土pH的影響
由表3可以看出,與對照處理相比,施用HA 30、100、300 mg/kg,在培養前期(3~15 d)土壤pH變化較大,特別是培養3 天時,土壤pH顯著增加,較CK提高了0.19~0.34個單位;施用YHA 30、100、300 mg/kg后,土壤pH在培養期內較CK增加0~0.20個單位;施用SHA 30、100、300 mg/kg,在培養期內較CK增加0.01~0.06個單位。

表3 腐殖酸對土壤pH的影響Table3 Effects of humic acids on soil pH
2.3 不同腐殖酸對潮土銅有效性的影響
根據試驗結果(圖2),各腐殖酸的不同用量在不同培養期內對土壤銅有效性影響不同。一周(7 d)內,除HA 100及300 mg/kg在第7天使有效銅含量降低外,其他處理均增加土壤銅有效性。一周后,與CK相比,施用30~100 mg/kg的HA和YHA土壤有效銅含量分別提高了31.2%、28.5%、13.8%、16.4%,而SHA 30及100 mg/kg土壤有效銅含量與CK無顯著差異;施用300 mg/kg的HA、YHA和SHA均可顯著提升土壤銅的有效性,有效銅含量分別提高了32.0%、12.9%、15.7%。
2.4 不同腐殖酸對潮土鋅有效性的影響
由圖3可以看出,腐殖酸對土壤有效鋅含量的影響呈現階段性變化。7~15天內,施用30~300 mg/kg三種腐殖酸均可增加土壤有效鋅含量,其中以HA效果最佳,第15天土壤有效鋅含量增加了11.8%~20.3%,與CK差異顯著,其次為YHA,土壤有效鋅含量增加了3.8%~9.3%。15~60天,施用三種腐殖酸顯著降低了土壤有效鋅含量,至30天時降低了11.3%~18.6%,以HA對土壤有效鋅含量降低作用最大,但同一用量下不同腐殖酸處理間差異不顯著。
2.5 不同腐殖酸對潮土錳有效性的影響
圖4表明,在培養期間,施用腐殖酸15天可提高土壤錳有效性,30~100 mg/kg用量下,以HA作用最明顯,土壤有效錳含量最多可提高5.6%,與CK差異顯著,300 mg/kg用量時,SHA使土壤有效錳含量較CK提高13.6%,與CK差異顯著。15天后,施用腐殖酸HA、YHA、SHA土壤有效錳含量較CK分別降低8.5%、5.9%、2.4%,其中HA的作用最明顯,30~100 mg/kg用量下,土壤有效錳含量降低了7.7%~10.0%,與CK差異顯著。

圖2 不同腐殖酸及用量對土壤銅有效性的影響Fig.2 Effect of different humic acids and rates on the availability of copper in soil

圖3 不同腐殖酸及用量對土壤鋅有效性的影響Fig.3 Effect of different humic acids and rates on the availability of zinc in soil

圖4 不同腐殖酸及用量對土壤錳有效性的影響Fig.4 Effect of different humic acids and rates on the availability of manganese in soil
2.6 不同腐殖酸對潮土鐵有效性的影響
由圖5可知,施用HA、YHA和SHA三種腐殖酸一周(7 d)均降低了土壤中鐵元素的有效性;而培養15天,土壤鐵有效性增加,與CK相比,施用HA30~300 mg/kg可使土壤有效鐵含量增加4.3%~7.2%,施用SHA30 mg/kg土壤鐵有效性增加4.3%,施用YHA300 mg/kg土壤鐵有效性增加6.8%;之后,各處理土壤有效鐵含量下降,處理間無顯著差異。
3 討論
土壤微量營養元素的移動、積累及其有效性與土壤中有機物有很大關系[25],腐殖酸作為一種外源有機物添加至土壤中,由于其結構的復雜性(分子量、官能團),與土壤中元素反應既能生成可溶性配合物,也能生成不溶性配合物,因此,具有增加或降低其有效性的雙重作用,影響土壤微量營養元素的賦存狀態[26],不同結構腐殖酸官能團種類、數量和性質上的差異會導致其金屬配合物穩定性不同[27]。
當腐殖酸施入土壤后,由于存在離子間的競爭作用,腐殖酸對銅元素有效性的影響大于鋅、鐵和錳[27]。施用腐殖酸能夠增加土壤中銅的有效性(圖2),這與劉平等[28-29]的研究結果一致。試驗中,磺化腐殖酸對土壤中有效態銅含量的提升效果弱于其他兩種腐殖酸,可能是由于磺化腐殖酸中羧基和脂族氮配體等能夠與銅配位[30-32]的位點相對減少,使得其與銅離子形成的配合物不穩定,容易重新被土壤礦物所吸附[33-34]。但也有研究認為腐殖酸中磺酸基基團能夠與銅強配位[35],本試驗中,腐殖酸經過磺化改性后,磺酸基含量明顯增加(圖1)使得配位能力隨之增加,但這種較強配合傾向可能使被配合的銅較難釋放而失去有效性。由于腐殖酸對微量元素的移動和對植物營養的價值取決于配合物的穩定性,較弱或較強的配合作用均不利于土壤中有效銅含量的增加,因此,腐殖酸(HA)和氧化腐殖酸(YHA)較磺化腐殖酸(SHA)更容易活化土壤中的銅,在本試驗中,30~100 mg/kg用量下,腐殖酸(HA)對土壤銅的活化作用明顯優于磺化腐殖酸(SHA)。

圖5 不同腐殖酸及用量對土壤鐵有效性的影響Fig.5 Effect of different humic acids and rates on the availability of iron in soil
在石灰性土壤中,由于高pH值和CaCO3含量,腐殖酸與鋅、錳的配合物具有低穩定性[36],當腐殖酸施入土壤后,腐殖酸中小分子組分的酚羥基和弱酸性的羧基首先與鋅、錳元素以較弱的鍵形成可溶性配合物,減少了鋅、錳元素離子在土壤表面的吸附,提高了其有效性[37-38]。隨著時間的延長,配合物重新被土壤礦物吸附,而且腐殖酸中大分子組分的強酸性羧基能夠以穩定的形式吸附鋅、錳,形成較強的配位鍵[39],從而使土壤中鋅、錳元素有效性降低,這可能是試驗培養期間各腐殖酸處理土壤中鋅、錳有效態含量波動較大且具有階段性(圖3、圖4)的原因之一,具體表現為腐殖酸并非總是活化或者鈍化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在培養15天,腐殖酸對土壤鋅和錳有活化作用,而之后則起到鈍化作用,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17,40-41]類似。腐殖酸(HA)和氧化腐殖酸(YHA)由于具有較多的羧基、酚羥基等含氧官能團(表2),配位能力增強,因此,在培養后期其對鋅、錳元素的鈍化作用要強于磺化腐殖酸(SHA)。腐殖酸對土壤中鋅、錳元素的作用相似,也可能與腐殖酸和鋅、錳的親和力相似[17,42]有關。
試驗中,不同腐殖酸對土壤鐵有效性的影響雖然也呈現出階段性,但規律不明顯,這可能是土壤pH與腐殖酸加入共同作用的結果。石灰性土壤中鐵的有效性受pH值影響較大,每升高1個pH值單位,鐵的溶解度將降低1000倍[43],培養初期(0~7天)各腐殖酸處理土壤有效鐵含量的大量降低可能與土壤pH升高有關。另外,許多研究表明,腐殖酸與鐵的配合作用可能與其分子量大小和羧化程度有關,羧基是鐵的主要結合位點[44-46],具有高羧化度的化合物作為鐵的強配體,而具有較低羧化度的化合物將作為較弱的配體[47-48]。因此,培養0~30天,腐殖酸(HA)和氧化腐殖酸(YHA)由于具有較多的羧基基團,易與鐵形成相對穩定的配合物,而磺化腐殖酸(SHA)由于羧基含量減少(表2)以及分子量降低,易與鐵形成不穩定的配合物,隨時間的延長,在培養后期(30~60天),由于磺化腐殖酸(SHA)與鐵形成的配合物中的鐵可能會重新被土壤礦物吸附[17,49]。因此在不同的培養期,腐殖酸對土壤鐵的有效性不同。由于鐵元素為變價元素,有機鐵配合物穩定性也易受土壤氧化還原作用的影響[50],在本試驗中,不同種類腐殖酸對土壤鐵有效性的影響規律不明顯可能與此有關。
另外,在本試驗條件下,通過磺化改性所得到的磺化腐殖酸(SHA)與腐殖酸(HA)、氧化腐殖酸(YHA)在元素含量上差異較大,特別是碳含量相對降低較多(表1),可能是由于在磺化改性過程中引入了較多的硫和氧元素所致,傅里葉變換紅外光譜分析結果也表明,磺化腐殖酸分別在1193 cm-1、971 cm-1處產生較強的磺酸基反對稱伸縮振動和硫氧(S-O)伸縮振動(圖1)。但限于本試驗研究方法和測試手段,磺化改性后的腐殖酸結構組成尚不能明確,這將在后續研究中進一步探究。
4 結論
在本試驗條件下,腐殖酸(HA)、氧化腐殖酸(YHA)和磺化腐殖酸(SHA)三種不同結構腐殖酸對潮土中同一微量元素有效性的影響不同,總體來說,對銅元素有效性的影響大于鋅、錳和鐵。
三種腐殖酸對潮土鋅、錳有效性的影響類似且呈現階段性變化,可在施用15天之內提高土壤鋅和錳的有效性,其中,HA的效果明顯優于YHA和SHA。
因此,在生產中應用腐殖酸提高潮土微量元素有效性時,需結合腐殖酸特性和養分元素種類選擇其用量與施用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