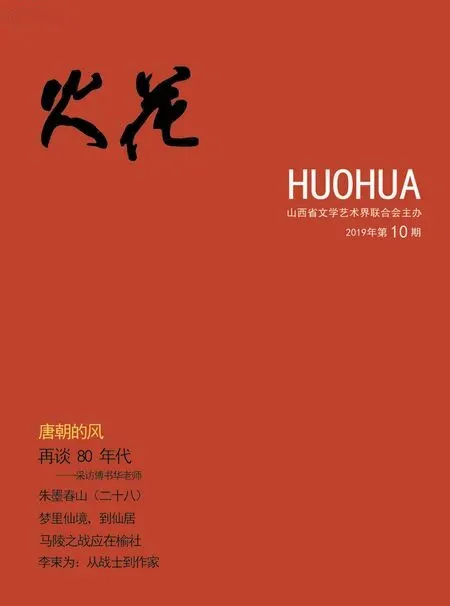唐朝的風
潘玉毅

風可以穿越柵欄,穿越屋檐,穿越墻洞和門縫。只要你所在的地方還沒有密實到讓人窒息,它都有辦法破除障礙,潛入到你的身邊。故而大隱于市也好,小隱于野也好,稍加留心,我們定能察覺到它的存在。
風很多時候就同人一樣,人有喜怒哀樂諸般情緒,風也是如此。有些風性子大條,無論做什么事都漫不經心的,從東吹到西,從西吹到東,沒事人一般;有些風生來敏感,遇到些許碰撞就大喊大叫,仿佛人的嘶吼與咆哮;也有些風生來就是樂天派,走到哪兒,都哼著輕快的曲子,紅了夭桃綠了楊柳,讓大地煥發出蓬勃的生機。
風每個時代都有,但是唐朝的風似乎要多一些神韻,多一些雅量,也較尋常的風來得更令人難忘。之所以這么說,不只是因為唐人的古風寫得極好,還在于當時許多的風雅之事常常都有風的點綴。唐朝的風在都城南莊,在西塞山前,在滕王閣上,在一首首千古傳唱的詩里,在一篇篇驚才絕艷的文章里。
唐朝的風吹過李太白的酒樽,斗酒便得詩百篇;唐朝的風吹過張旭的硯臺,揮毫落紙如云煙;唐朝的風吹過魚玄機的仙居,軒檻暗傳深竹徑,綺羅長擁亂書堆;唐朝的風在張若虛的腦門上輕輕掠過,于是便有了那首“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
《春江花月夜》,“孤篇蓋全唐”。雖然題目中并沒有出現風字,全詩三十六句二百五十二字也無一字談風,然而誰都知道江畔多風,失了它便失了幾多妙趣。鴻雁長飛有風,魚龍潛躍有風,落花搖情亦有風。只不過這些風不在字面上,而在詩的意境里。
或許,有一點,唐朝與現在并無分別,那就是每個季節都有風,且每個季節的風給人的感覺各不相同。唐代的詩人們不負才子之名,將四時之風寫出了各自的味道。
春日的風在白居易的庭院之中。院子里有梅樹三株,春風先到梅樹梢頭,喚醒了將開未開的梅花,告訴它自己來時的見聞。緊跟著,它又來到其它地方喚醒其它的花朵。幾乎在同一時間,櫻花杏花桃花梨花前腳接后腳地露出了芳容。深山冷岙里的薺花和榆莢聞訊后,也紛紛做好了準備,靜候春風的到來。“薺花榆莢深村里,亦道春風為我來。”這十四字,真的太有味道了,讀之可解乏,記之堪回味。
夏日的風受眾很廣,幾乎每一位有名的唐代文人都寫過,這其中最放蕩不羈的還數李白。他的《夏日山中》一詩,直至今日仍被人反復援引:“懶搖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脫巾掛石壁,露頂灑松風。”夏日悶熱,溽暑難消,鵝毛扇的風已經濟不了什么事了,詩人逃到山林里,脫去上衣頭巾,尋一處綠蔭深處,在一塊石頭上睡起覺來。風吹動頭發,竟似吹動松濤一般。這樣的避暑方式真是太有意思了,而這樣的風似乎也來得太合時宜了。
秋日的風吹來時,早已沒有了“荷香滿四鄰”的雅韻,卻添了些許歸意。張說有《蜀道后期》一詩:“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似乎那個時候,只要洛陽與秋風出現在一處,多半是用來表達游子的客思的。張說的本家張籍亦有一首《秋思》,比張說的五絕多出八個字,名頭也響上八分——洛陽城里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秋風起了,該回家了,然則我回不去啊,心中萬語千言,想借書信說與家人知道,遺憾的是,紙短情長,終歸說不了許多,信已寫完封好,捎信的人也準備啟程了,才發現自己竟還有許多話不曾講。這就是唐朝的秋天的風。
相比于前三個季節,冬天的風盡顯肅殺之意。唐朝流行邊塞詩,岑參、高適詩中頗多“北地胡風”意象,就連山水田園詩人韋應物也曾寫作《送孫征赴云中》,氣象極是廣闊:“黃驄少年舞雙戟,目視旁人皆辟易。百戰曾夸隴上兒,一身復作云中客。寒風動地氣蒼茫,橫吹先悲出塞長。敲石軍中傳夜火,斧冰河畔汲朝漿。前鋒直指陰山外,虜騎紛紛翦應碎。匈奴破盡看君歸,金印酬功如斗大。”“寒風動地氣蒼茫,橫吹先悲出塞長”兩句,看似無用之筆,實則有效地渲染了氣氛,將人帶入意境之中,這倒與風本身的作用異曲同工。
四時之風各有特色,交集亦不多,但一名叫李嶠的唐代詩人還是給風的形象作了總結和描繪:“解落三秋葉,能開二月花。過江千尺浪,入竹萬竿斜。”咀嚼之下,竟覺十分有味。
唐朝的風曾經吹入長安城,也曾吹入尋常百姓家,甚至吹到千年以后,它的影響還在。春風化雨,自古已然。就像唐代的詩到宋代變成了詩余,唐朝的風到了宋朝也變成了雨,作家陳富強老師就曾寫過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宋朝的雨》,將坐標定于1090年仲春的蘇堤,主人公是率眾疏浚西湖的蘇軾,文筆優美,十分好讀。
其實,唐朝和宋朝可講的故事有許多,可寫的人亦有許多,一如風雨澤被的蒼生。有人說,唐詩與宋詞是后代人難以逾越的兩座文化高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唐朝的風也是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