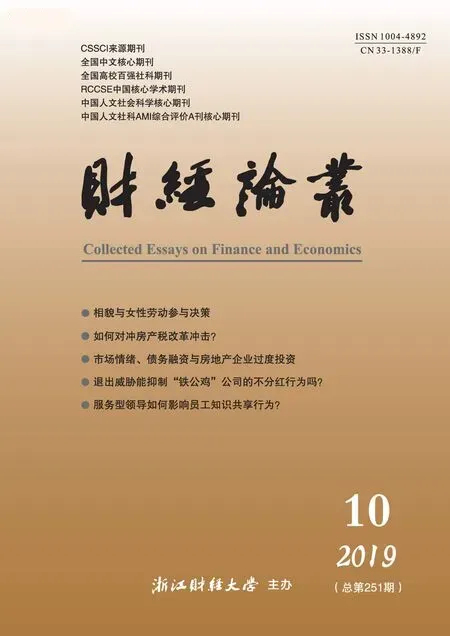退出威脅能抑制“鐵公雞”公司的不分紅行為嗎?
胡建雄,殷錢茜
(1.南京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2.南京大學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
一、引 言
企業最優股利決策的確定是財務學者關注的重點[1]。中國資本市場不健全,上市公司較為忽視投資者的權益,股利支付水平較低[2][3]。因此,不分紅的公司不僅引起眾多投資者不滿,還遭致證監會的嚴厲批評(1)① 2017年12月1日,中國證監會在新聞發布例會上強硬發聲,對于在資本市場只知道抽血而不知回饋的“鐵公雞”上市公司,證監會將采取更嚴格的監管措施,對其違法違紀行為一律嚴肅處理,絕不姑息。。自2001年伊始,證監會循序漸進地頒布了一系列要求提升股利支付水平的“半強制分紅政策”,用來引導和規范上市公司的分紅行為[4],從而對公司的股利決策發揮了重要影響[5]。近年來,在美、日及歐盟等發達經濟體中,股利支付率也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然而政府卻并未進行政策干預,反而依靠上市公司健全的公司治理機制來使股利支付自發回歸到正常水平[6]。雖然中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機制相對不夠完善,但股利支付過度依賴于政策調節的做法也絕非長久之計,否則即便企業暫時達到半強制分紅政策規定的要求,也不利于其長遠發展[3][4]。
與此同時,不同于西方發達經濟體,中國等新興資本市場中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高度集中并呈現“一股獨大”的特征[7]。控股股東通過控制董事會,親自擔任或者委派親信擔任公司的董事長或CEO,牢牢掌控公司的資源支配權。所以在新興資本市場國家,與股東和管理者之間的利益沖突相比,公司代理問題更多地表現為控股股東和其他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8]。在現實中,控股股東可以借助資金占用、過度投資和關聯交易等“掏空”手段,侵占其他股東的利益[7]。其中,上市公司的不分紅決策為控股股東占用公司資金而從事利己的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便利[9]。而除了控股股東之外的其他大股東,較為關注自身的投資收益特別是現金股利的發放,因而控股股東的不分紅行為對其利益造成了一定損害。此時,這些大股東可以采用兩種方式維護自身的權益:第一,積極參與。即通過積極參與股東大會、董事會等方式來約束控股股東的不分紅行為。然而,多數學者認為這種方式在西方較為完善的公司治理環境下備受青睞,而在中國的適用性略有遜色[10][11](2)如前所述,中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高度集中并且“一股獨大”,控股股東始終控制董事會,導致企業決策程序和內部控制機制“失靈”。由于投票權具有“非完備性”的特征,大股東積極參與方式所依賴的股權制衡度不僅難以抑制控股股東謀求私利的行為[10],還加劇了控股股東和其他大股東之間的權力斗爭[11]。。第二,退出威脅。大股東畢竟可以委派董事和高管參與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因而對公司財務和運營狀況掌握一定程度的私有信息。作為知情交易者的大股東,通過發出減持公司股票的威脅,可以向市場傳遞公司價值低的不利信號,對公司股票價格產生負面影響,甚至造成股票崩盤,反過來損害控股股東的控制權利益,從而可能對不分紅的機會主義行為形成一種有效制約,而這方面的研究卻鮮少涉及。
基于此,本文探討了大股東的退出威脅在抑制“鐵公雞”公司的不分紅行為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并結合公司內外治理機制綜合考察該作用所呈現的差別性特征。總的研究貢獻有兩點:一方面,開啟了中國情境下看待股利決策的另一扇理論之“門”,視角由半強制分紅政策轉向公司治理機制,為研究現金分紅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范式。在治理機制的研究中,即便中國上市公司的整體治理環境不如成熟經濟體,導致大股東的積極參與方式難以充分開展,但反而使退出威脅更具有用武之地。因此,本文將大股東的退出威脅視為一種公司治理機制,進一步拓展了大股東治理領域的研究,同時也豐富了股權制衡領域的相關文獻。另一方面,當前有關股利決策的實證研究,揮之不去的一個難題在于內生性的處理。而本文借助雙重差分模型,巧妙利用中國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權結構及發生在2005~2007年間的股權分置改革(3)姜付秀等(2015)[7]認為,股權分置改革使得控股股東及其他大股東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由非流通股轉變為流通股,為大股東的退出提供了可能。該研究還指出,盡管股權分置改革之前,非流通股也可以通過協議進行轉讓,但由于買家難覓、價格難以形成等原因,交易雙方只能在流通股交易價格的基礎上打一個折扣來確定雙方均能接受的非流通股定價,從而阻礙了非流通股股東的退出。事件作為自然場景。對于不同上市公司而言,由股權分置改革導致的股票流通性變動是完全外生的,從而為本文檢驗退出威脅對不分紅行為的具體作用規律提供了難得的“自然實驗”條件。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一)退出威脅和分紅行為
在公司治理的框架內,股東治理具有重要地位。中小股東往往出于收益和成本的考量而“搭便車”,但大股東持股比例相對較高,其持股市值與企業的業績和經營管理狀況密切相關,具有更強烈的動機參與公司治理[12][13]。同時,大股東的監督可以提高企業價值[14],并能從中彌補自身的監督成本。當前有關大股東監督效應的文獻較多集中于探討大股東積極參與公司治理的方式,而對另一種監督類型——發出退出威脅,尤其是其與企業股利決策之間的關聯,卻鮮少涉及。
社會心理學中,威脅是利益主體在決策博弈中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表達訴求的一種方式,通過施加壓力迫使對手做出退讓[15]。而退出威脅是近年來國際財務和會計學領域興起的一種前沿概念,其能緩解公司代理問題的功效已被Hope等(2017)[16]學者證實。即便大股東未介入公司實際的經營管理活動[12],或即使大股東并沒有真正退出,但其發出的退出威脅也足以推動控股股東調整當前有損于大股東利益的財務決策[16]。在企業股利決策的制定時,現金股利的支付能夠有效減少控股股東因從事機會主義行為所需的自由現金流,降低控股股東和其他股東之間的代理成本[9]。所以,出于保障自身利益的需要,較高的股利支付率備受大股東青睞,該結論得到了國內外大多數學者的贊同[3]。但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高度集中,控股股東始終控制董事會,控股股東借助自身的控制權優勢,更傾向于實施利己的不分紅或少分紅的股利決策[7]。當大股東積極參與的方式無法發揮監督效應時,便可能無奈地發出“賣出公司股票而導致公司股價大跌”的退出威脅。此時,資本市場往往將具有信息優勢的大股東這一退出行為解讀為公司價值低的負面信息,非知情投資者會競相采取做空公司股票的策略,蔓延的恐慌情緒造成公司股價大跌,甚至引發股價崩盤。盡管股價下跌難以實現控制權轉移[17],但會影響資本市場中其他投資者和債權人對公司風險的判斷,造成預期資本成本上升,直接威脅企業價值和控股股東的私利[7]。受此威脅,控股股東便有較強的動機支付高額現金股利,減少不分紅行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大股東的退出威脅能抑制不分紅行為。
(二)退出威脅、分紅行為和股權集中度
在分析股利決策時,需要考察公司治理這一關鍵影響因素[1]。公司治理機制存在內外部的區別,其對企業各項財務決策的作用是不同的。就內在治理機制而言,企業股權集中度會對大股東退出威脅的效應產生重要影響。據此,本文分別從控股股東財富的集中度和大股東退出威脅的可信度兩個角度,來分析退出威脅效應的強弱。
1.控股股東財富的集中度。由于控股股東自身的財富與公司股價密切相關,所以當大股東的退出威脅造成公司股價降低時,控股股東的財富也相應縮水[13]。也就是說,控股股東的財富與股價的敏感度越高,那么大股東退出威脅對控股股東財富造成的損失越大。與持股比例較低的股東相比,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越高,財富越集中,有效分散公司特有風險的難度也越大[18]。此時,控股股東財富便幾乎取決于公司股價的高低,使得控股股東尤為高度關注公司股價的任何異動以及大股東可能實施的退出行為[19]。也就是說,控股股東財富與股價的敏感度大大增強。一旦大股東退出,股票價格的下跌將更大程度地損害控股股東的利益,對控股股東財富造成更大的損失,使得控股股東更加收斂不分紅行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越高,退出威脅對不分紅行為的抑制作用越顯著。
2.大股東退出威脅的可信度。除了控股股東財富的集中度外,退出威脅效應的強弱還取決于大股東退出威脅的可信度[12][19][20]。當控股股東持股水平不變時,大股東相對于控股股東的持股比例越低,說明大股東參與公司治理的積極性越弱,對控股股東不分紅行為的約束作用也越小,即股權制衡作用未能充分發揮。但在另一方面,大股東持股比例越低,其出售所持有股票的難度越低,顧慮也更少[7]。否則當大股東持股比例上升,即與控股股東持股比例的差距減小時,越容易“投鼠忌器”,擔心“真正退出”所引致的股價下跌反而更多地損害自身權益。可以看出,即便大股東因持股比例較低而缺乏對公司的控制權,但其仍然能利用自身所具有的私有信息優勢,及時退出而保障自身的收益,這反而對控股股東形成了較強的“震懾”作用[12],最終迫使控股股東的行為方式發生改變,從而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并增強大股東公司治理的效果[19]。所以,較低的持股比例為大股東的退出威脅提供了更多便利,增強了大股東退出的可信度,對控股股東不分紅行為的抑制作用也更明顯。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大股東持股比例相對于控股股東更低時,退出威脅對不分紅行為的抑制作用越顯著。
(三)退出威脅、分紅行為和審計質量
審計被視為一種可以減輕企業內部代理沖突的有效機制,并能降低企業契約各方主體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使得契約得以順利執行[21]。因此,并未侵占其他股東利益的控股股東,更傾向于將聘請高質量的審計服務作為一種信息傳遞機制[22]。較強的外部審計,可以使控股股東侵占其他股東利益的行為更容易被發現及被起訴,從而可以約束控股股東謀取私利的行為[8]。因此,審計質量是外在治理機制的一個重要方面[23]。也就是說,如果在高質量的審計環境下,控股股東謀取私利的空間較為狹窄,通過不分紅行為來侵占其他股東利益的動機也更弱。此時,大股東的退出威脅所能發揮的公司治理作用非常有限,控股股東股利決策的調整對大股東退出威脅的敏感度也會大大降低。Admati和Pfleiderer(2009)[19]認為,當代理人侵占公司利益的可能性越大時,大股東退出威脅的作用越強。據此可以推斷,當外在治理機制較不完善時,即審計質量越低的情況下,公司面臨較低程度的外部審計監督使得控股股東更有可能侵占其他股東利益,此時大股東的退出威脅對控股股東不分紅行為的抑制作用將會更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4:審計質量越低時,退出威脅對不分紅行為的抑制作用越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和樣本選擇
本文初始研究樣本為中國2001~2016年間連續上市的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選取自WIND數據庫和CSMAR數據庫。借鑒魏志華等(2017)[3]的做法,為了減少內生性干擾,本文對各回歸模型的因變量滯后一期處理。所以,需將樣本的時間跨度往前延展一年,最終選取了2000~2016年的數據。為了鞏固控制地位和擴大控制比例,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東通過親緣關聯、產權關聯、任職關聯或簽訂“一致行動人協議”等形式共同持股,以便于在行使表決權時采取相同的意思表示來保障自身的權益[23]。鑒于此,首先本文需要對上市公司的股權狀況進行手工整理,將一致行動人的股東所持有的股票數量合并,作為一個新股東進行分析(4)需要根據年報記載的事項,對上市公司各年份不同持股比例股東的股權狀況進行逐一整理。最終得出的控股股東持股比例其實是一致行動人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而大股東持股比例其實是一致行動人的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根據學術慣例及研究特點,本文按照如下標準篩選樣本:(1)剔除金融和保險類樣本;(2)剔除ST、*ST、PT類樣本;(3)剔除相關數據缺失的樣本;(4)剔除控股股東持股比例低于大股東持股比例的異常樣本;(5)為了消除極端值的干擾,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st和99th分位上進行了Winsorize縮尾處理。最終,本文得到了900家上市公司連續16年共14400個觀測值,整理成平衡面板的數據形式。
(二)大股東的界定
現有研究對大股東的界定存在爭議。Attig等(2009)[24]、姜付秀等(2015)[7]將大股東定義為持股比例超過10%的股東;而Bharath等(2013)[25]則沿用1934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的規定,將持股比例超過5%的股東定義為大股東。這些研究的制度背景和研究目的存在較大差異,而本文認為大股東的退出威脅能產生公司治理效應的基本邏輯在于大股東掌握公司的私有信息,他們的退出會對股票價格產生不利影響,從而抑制控股股東的不分紅行為。從中國實際情況看,根據2004年新修訂的《公司法》中第104條規定,單獨或累計持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東請求時,公司需要在兩個月內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同時,當持股比例超過10%時,股東基本上可以向上市公司派出一名董事或高管參與公司日常經營管理。因此,本文結合中國實際情境,將持股比例超過10%的股東定義為大股東。
(三)實證模型和變量定義
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除了控股股東之外至少存在一位大股東,本文將這種股權結構的公司樣本設為實驗組;另一種為僅存在控股股東而沒有其他大股東的股權結構,本文將其作為對照組。顯然,不能僅憑實驗組公司在其股權分置改革后控股股東的不分紅行為有所收斂,就得出大股東的退出威脅發揮了公司治理作用,而應該將其與對照組公司展開對比論證。具體而言,如果股權分置改革為大股東的退出威脅提供了可能,那么相對于對照組,實驗組公司中控股股東的不分紅行為下降更多,才表明大股東的退出威脅能夠抑制控股股東的不分紅行為。具體實證檢驗的雙重差分模型如下:

Yeart+Industryt+ζt
(1)
如式(1)所示,Dividend代表公司股利決策,包含了是否分紅、分紅多少兩大維度,因此本文再分別定義Dumdiv和Payout兩個變量。具體而言,當該年份公司實施分紅行為時,Dumdiv取值為1,否則為0;而Payout為每股現金股利與每股凈利潤的比值。Treat為公司組別變量,如果為實驗組樣本,Treat取值為1,對照組樣本則為0。以上市公司是否完成股權分置改革衡量大股東的退出威脅,如果該公司完成股權分置改革,則后續年度Exit取值為1,否則為0。可以看出,Treat的系數θ1用于捕捉股權分置改革之前實驗組與對照組公司的分紅行為差異;而Exit的系數θ2捕捉的是對照組公司在股權分置改革前后的分紅行為差異。CONTROL(u)是第u個控制變量,θ0是截距項,ξt是隨機擾動項。本文關注的重點在于交互項Treat×Exit(也稱雙重差分項)的系數θ3,該系數可以表示為:
θ3={E[Dividendi,t+1|Treati,t=1,Exiti,t=1,Zi,t]-E[Dividendi,t+1|Treati,t=0,
Exiti,t=1,Zi,t]}-{E[Dividendi,t+1|Treati,t=1,Exiti,t=0,Zi,t]-
E[Dividendi,t+1|Treati,t=0,Exiti,t=0,Zi,t]}
(2)
如式(2)所示,Z為控制變量集,θ3代表了通過對比實驗組和對照組公司在股權分置改革前后的相對距離來將不可觀測的干擾因素排除后進而分離出股權分置改革外生沖擊的凈效應。假設1的成立意味著θ3>0,說明在股權分置改革后,實驗組公司中分紅公司比重、具體分紅額占凈利潤的比重均有更大提升,即大股東的退出威脅抑制了控股股東不分紅行為。
與此同時,本文在檢驗假設2和假設3時,參考姜付秀等(2015)[7]的研究,構建了控股股東持股比例(Hold)、是否為高控股比例的啞變量(Hhold,高控股比例取值為1,否則為0)、控股股東持股和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差(Difference)以及是否為高持股差的啞變量(Hdifference,高持股差取值為1,否則為0)。在檢驗假設4時,借鑒魏明海等(2013)[23]的成果,以公司是否聘請國際“四大”進行審計來衡量審計質量(Audit,聘請取值為1,否則為0)。此外,本文還參照王國俊等(2017)[1]、魏志華等(2017)[3]的做法,控制了公司規模(Size,總資產的自然對數)、重大投資安排(Invest,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其他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現金、投資支付的現金、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支出四項之和與總資產的比值)、成長性(Growth,企業留存收益與所有者權益的比值)、盈利能力(ROA,凈利潤與總資產的比值)、負債水平(Lev,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值)、現金持有水平(Cash,貨幣資金與總資產的比值)、年度效應(Year)和行業效應(Industry)等變量。
(四)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1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檢驗結果。從連續16年Dumdiv和Payout的取值看,中國上市公司的現金分紅行為并不普遍,且現金分紅水平較低,“鐵公雞”的企業特征較為突出。Treat的平均值為0.4271,即實驗組樣本數目低于對照組,意味著與除了控股股東之外至少存在一位大股東的股權結構相比,中國上市公司中僅存在控股股東而沒有其他大股東的股權結構更為普遍,加上Hhold和Hdifference的統計結果,進一步佐證了中國上市公司具有“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特征。此外,Audit的平均值接近于0,說明聘請國際“四大”進行審計的上市公司比重較低,審計質量有待進一步提升。從整體而言,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均位于合理區間內,與上文的邏輯推演保持了一致性,可以繼續進行下文的實證分析。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對不分紅行為的抑制:退出威脅效應與時間趨勢效應的對比
表2比較了實驗組公司和對照組公司在股權分置改革前后的平均現金分紅水平。結果顯示,在股權分置改革前,實驗組公司的平均現金分紅水平略高于對照組公司,其中Dumdiv的差異在5%的水平上顯著,而Payout的差異并不顯著。但是在股權分置改革后,實驗組公司和對照組公司的平均現金分紅水平相比于改革前都有明顯增強(所有檢驗指標的差異在1%的水平上均高度顯著),同時雙重差分項數值為正還說明實驗組公司在股權分置改革后的平均現金分紅水平的凈增量竟然還高于對照組樣本。可以初步判斷,與對照組公司相比,實施股權分置改革對實驗組公司的現金分紅水平的提升具有更大的促進效應。也就是說,股權分置改革大大減輕了“鐵公雞”上市公司的不分紅傳統,尤其對于除了控股股東外還存在大股東的上市公司而言更是如此。因此,本文假設1得到了初步驗證。

表2 股權分置改革前后的平均現金分紅水平:t-檢驗結果
注:*、** 、*** 分別代表顯著性水平為10%、5%和1%(雙尾)。下同。
表3第(1)~(2)列報告了上文式(1)的回歸結果,由于數據特征的不同分別采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結果顯示,Treat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在股權分置改革前,實驗組公司的平均現金分紅水平均高于對照組公司;Exit的系數都顯著為正,說明就對照組公司而言,股權分置改革后的平均現金分紅水平顯著高于改革前;而交互項Treat×Exit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在股權分置改革完成之后,實驗組公司的實際分紅水平出現上升,且上升幅度顯著大于對照組公司。從整體看,第(1)~(2)列各關鍵變量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高度顯著,模型擬合狀況較好,同時與表2的t-Test檢驗結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然而,如上回歸結果可能是由于存在的一種時間趨勢使然,如大股東治理效應因時間推移變得更加有效,而與退出威脅無關。因此,本文參考梁權熙和曾海艦(2016)[26]的做法,鑒于絕大多數樣本股權分置改革完成的時間均在2005~2007年,所以依次在基準回歸的基礎上引入2005~2007年的虛擬變量Year2005、Year2006、Year2007及其分別和組別變量Treat的交互項Treat×Year2005、Treat×Year2006、Treat×Year2007來控制2005~2007年改革的效應,回歸結果如表3第(3)~(4)列所示。顯然,Treat、Exit和Treat×Exit的系數方向及顯著性水平都未發生明顯改變,而Treat×Year2005、Treat×Year2006和Treat×Year2007的系數均不顯著。這充分說明,與對照組公司相比,實驗組公司在2005~2007年每一年前后的平均現金分紅水平并沒有顯著性上升,而對實驗組公司不分紅行為抑制的凈效應是由于大股東的退出威脅所產生,并非時間趨勢使然。因此,本文假設1得到了最終驗證。

表3 對不分紅行為的抑制:退出威脅效應與時間趨勢效應的對比
注:以Dumdiv為因變量的回歸模型均采用Logit平衡面板數據模型,而以Payout為因變量的回歸模型均采用Tobit平衡面板數據模型。為了保證結論的穩健性,本文對所有回歸模型的標準誤均進行公司層面的聚類調整(clustered by firm)。限于篇幅,未在表中列出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下同。
(二)退出威脅和分紅行為:基于內外治理機制的分組檢驗
如前所述,反映內在治理機制的股權集中度分為控股股東財富的集中度和大股東退出威脅的可信度兩項內容。一方面,為了驗證大股東的退出威脅是否在控股股東財富集中度較高的公司中更有效,本文選取實驗組子樣本進行檢驗。表4第(1)~(2)列報告了控股股東是否為高控股比例啞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關鍵檢驗變量Hhold×Exit的系數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充分說明在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較高時,即在大股東的退出威脅會讓控股股東的財富遭受更大損失時,公司實際現金分紅水平越高。另一方面,為了驗證大股東退出威脅的可信度與退出威脅之間的關聯,本文仍然選取實驗組子樣本進行檢驗。第(3)~(4)列報告了是否為高持股差啞變量來衡量大股東退出威脅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關鍵檢驗變量Hdifference×Exit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充分說明在控股股東持股水平不變時,大股東持股比例相對于控股股東更低時,大股東的退出威脅會更可信,更加抑制控股股東的不分紅行為,從而提高公司的現金分紅水平。因此,本文假設2和假設3得到了驗證。
外在治理機制由外部審計質量進行度量。本文將全部樣本分成低審計質量組(非國際“四大”審計組)和高審計質量組(國際“四大”審計組)兩個子樣本進行分組檢驗,回歸結果分別如第(5)~(8)列所示。結果表明,在低審計質量組,Treat×Exit的系數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大股東的退出威脅顯著提高了實際現金分紅水平;而在高審計質量組,Treat×Exit的系數顯著性有所下滑且均為負,說明了大股東的退出威脅不僅沒能提升現金分紅水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控股股東的不分紅程度。也就是說,大股東的退出威脅對不分紅行為的抑制作用需要在外部審計質量較低的環境里才能有效發揮。因此,本文假設4得到了驗證。

表4 退出威脅和分紅行為:基于內外治理機制的分組檢驗
注:由于內在治理機制主要是由大股東對控股股東發揮的作用而言,而對照組樣本無大股東類型,所以選擇實驗組樣本,得到第(1)~(4)列的結果;而外在治理機制對于不同股權類型的企業均適用,故選擇全樣本進行分組檢驗,得到第(5)~(8)列的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如上結論的穩定性,本文還進行了以下的穩健性檢驗:
1.重新界定大股東。根據《中國上市公司股份減持實施細則》的規定,持股5%以上的股東通過競價交易而減持股份的,應在首次賣出股份的15個交易日內向交易所報告減持計劃,并予以公告。可以看出,持股5%以上股東的退出威脅無疑也會對市場產生巨大沖擊。基于此分析,本文借鑒Bharath等(2013)[25]的研究,重新定義持股比例超過5%的股東為大股東,對公司組別啞變量Treat重新取值,并對研究假設再次進行檢驗,發現主要變量的系數方向和顯著性水平均未發生變化(5)限于篇幅,未匯報穩健性檢驗的回歸結果,留存備索。。
2.更換回歸模型。借鑒魏志華等(2017)[3]的做法,對因變量Payout的方程采用混合OLS模型進行驗證,發現各變量的系數方向和顯著性水平均與主模型高度一致。同時,根據Hausman效應檢驗的結果,采用隨機效應面板數據模型再次進行了檢驗。結論表明,雖然隨機效應模型中多數變量的系數值和顯著性水平都不如主模型,但關鍵交互項Treat×Exit的系數仍然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
3.排除替代性解釋。(1)證監會“強制分紅”的考慮。為排除證監會“強制分紅”考慮的替代性解釋,進行了如下研究設計:選取2008年頒布的《關于修改上市公司現金分紅若干規定的決定》為研究對象(6)之所以選擇該《決定》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其他半強制分紅政策較多涉及各方面的公司法規,而該《決定》只針對上市公司的現金分紅問題而作出專項嚴格的規定[4]。,該文件要求最近三年公司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得少于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30%。我們逐一考察2008~2016年所有年份的樣本公司,剔除最近三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少于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30%的樣本,最終得到4880個觀測值,將其作為子樣本,對本文假設再次進行檢驗。結論表明,各變量系數的方向和顯著性水平均未發生明顯改變,且Treat×Exit的系數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
(2)對照組“一股獨大”股權結構的深層原因。此外,在本文的研究設計中,盡管我們篩選出“僅存在控股股東而沒有其他大股東”的樣本作為對照組。但是,對照組樣本里“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可能具有深層原因:或由公司歷史形成,或是由于以前年度大股東的退出而導致控股股東獨大的現象。如果屬于后者,那么對照組樣本中本身就包含了“大股東退出”的因素,因而上文得到的結論可能有偏。據此,為了排除該替代性解釋,我們在原對照組樣本的基礎上,篩選出在2001~2016年連續16年中始終是控股股東“一股獨大”的子樣本。經過篩選,我們將得到的1200個觀測值作為新的對照組樣本,與原實驗組樣本重新加入到本文模型的回歸中。我們發現,Treat×Exit的系數為正,且各變量的系數基本都在1%的水平上高度顯著,模型擬合優度也大為提升。這充分說明,即便考慮到“一股獨大”股權結構的深層原因,大股東的退出威脅依然會抑制“鐵公雞”公司的不分紅行為,從而充分證實了本文結論的穩健性。
五、研究結論
對不分紅的“鐵公雞”公司如何治理是證監會面臨的重要難題。本文以中國2001~2016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雙重差分估計策略,探討了大股東的退出威脅在抑制“鐵公雞”公司的不分紅行為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并結合公司內外治理機制綜合考察該作用所呈現的差別性特征。以股權分置改革事件作為大股東退出威脅的替代變量,研究發現,大股東的退出威脅能抑制不分紅行為。進一步地,當內在治理機制較不完善時,即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大股東持股比例相對于控股股東更低時,抑制作用更顯著;當外在治理機制較不完善時,即外部審計質量越低時,抑制作用更顯著。該結論經多種穩健性檢驗和替代性解釋排除后仍然成立。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強化對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支付行為的監督,使上市公司充分貫徹證監會關于現金分紅的若干指示精神,嚴懲“鐵公雞”公司故意以不分紅或少分紅的方式而侵害股東利益的行為;(2)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機制,有效保障廣大股東對公司重大決策制定的知情權和決定權,為積極參與方式的有效發揮創造條件;(3)在當前公司治理機制較不完善的背景下,需增強股票的流通性,防止因股票流通性受阻而造成退出威脅效果被大打折扣,從而強化股權分置改革的實施效果,為大股東的退出威脅掃清障礙,充分發揮其對控股股東的威脅效應。總之,在半強制分紅政策實施的同時,本文為治理“鐵公雞”現狀提供了另一種思路,需充分發揮“鐵公雞”公司不分紅行為的自動抑制效應,切實保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