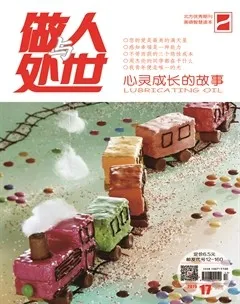陽光與月牙兒
薛文君
窗外下起了雨。我坐在圖書館的角落里,用目光捕捉這細微的陰涼。外面的雨落入我的心底,與我手掌上書中的境況竟然如此吻合。
模糊的視線里,月牙兒從老舍的《月牙兒》里向我走來,近了,越來越近,近得讓我觸到它的寒,時光拉開近千年的寒。我在文字外聽到文字中“我”控訴的悲歌,這悲歌令我淚雨滂沱。我想如果我推開歷史的門,走進那間小屋會怎樣?天空四處彌漫陰云,是不是隨時也將又細又彎的月牙兒吞噬掉呢?
在那樣的壞天氣里,那點微弱的光到底能持續(xù)多久,照亮多遠,隔著陳舊的墨香我嗅到月牙兒像蓮一樣清香,那池塘底的污泥熏染的是她的形,她的靈魂卻一塵不染。
雖然,我不知道月牙兒下的“我”叫什么名字,可我能聽到她的心跳、她的呼吸。我與她貼得那么近,就如她是我的前生,而我是她的后世。同為女人,只是所處的時代不同,我們的命運卻有著天壤之別。雖然都是鮮活的、積極向上的、富有靈性的生物,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的女人大可以隨性地成長,放飛夢想,而那時的女人卻是一株任人踐踏的野草,甚至找不到一條可以回家的路。
那時的“我”只有一個朋友——月牙兒,它在每一個苦難的路口等我。它淡淡的寒卻還有淡淡的光亮,能照見“我”眼底的淚痕,也見證了“我”從清潔到污濁的蛻變。是的,“我”痛苦地蛻變,將微弱的希望與荒謬的幻想挖個坑埋掉。“我”看不見美好,那本能的追求生活的路卻比登天還難。
文字中的“我”第一次看見月牙兒是在父親即將離世時,懷著饑餓、寒冷與它對視,月牙兒在天上是孤獨的,“我”在人間也是孤獨的。那時7歲的“我”立到月牙落到盡頭,月盡了,父親走了,而“我”和媽媽開始在月牙兒下掙扎,為尊嚴,為生計,為兩張嘴。
“我8歲時便學會了當當”,“當鋪不要這面鏡子”時,“我坐在那門墩上,握著最后那根銀簪”,“我看著天,啊,又是月牙兒照著我的眼淚。”“我”所有的苦難只有月牙兒懂得,那微弱的光是媽媽的手還留有的熱度。但這雙手很快被臭“牛皮”磨出了層鱗,已經(jīng)支撐不住兩張大嘴。母親改嫁了,“我”的月牙兒消失了幾年,可是當它再度出現(xiàn)時,母親已成為“我”最恨的人。“我”的內(nèi)心有著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以“我”會對母親不齒。即便母親為了自己最后的生計依然決然地舍棄了“我”,“我”也沒有放棄月牙兒,它依然在我頭上照著我,照著我的眼淚。
“我”天真地以為“我”上過學,練有一手好字,我可以養(yǎng)活自己,甚至還可以養(yǎng)活媽媽。但是“我”錯了,我卑微的生存從換校長后便沒有了著落。“我還不如一條狗,狗有個地方便可以躺下睡,街上不準我躺著。是的,我是人,人可以不如狗。”“我”甚至連媽媽也不如,她還能找到洗臭襪子的活兒,而我連這個活也做不到。“書本里的道理教給我的本事與道德都是笑話,都是吃飽了沒事時的玩意。”此刻我頭頂?shù)脑卵纼阂衙允Я朔较颍俏⑷醯墓獗滑F(xiàn)實的黑暗吞噬了。于是“我”終于明白,媽媽沒有錯!“媽走的路才是唯一的路。”
我的心仿佛是在月光下的蝙蝠,雖然在光的下面,可是自己是黑的。黑的東西,即使會飛,也還是黑的,我沒有希望。“我”只能走向媽媽走過的路,但“恥辱不是我造出來的”,這是多么無奈的抉擇,又是多么憤然的控訴!關(guān)閉歷史的門,打開現(xiàn)實的窗,我慶幸月是圓滿的,澄明的,它可以照亮黑夜的每一處角落,不再有陰影,不再有眼淚。
那時的月牙兒幾乎侵蝕著所有女人的苦。可憐的像磁人似的小媳婦以及那些抱著書本的女同學。可悲的是她們還抱著幻想,而“我”早已把幻想在現(xiàn)實里踐踏了。女人是什么?無非是排著長隊任男人挑選的“物品”,也無非是男人只須花兩元錢的手續(xù)費和找一個妥實的鋪保就可以領(lǐng)走的“物品”。而更痛心的諷刺卻是會洗、做、烹調(diào)、編織的女人找不到生存的出路。這在現(xiàn)代社會令人大跌眼鏡的事實,在那個社會,在那種男尊女卑的制度下,就是不爭的現(xiàn)狀。如此想來那個時代給女人的生存空間能有多大?所幸,歷史的車輪總是向前的,頭頂那彎月牙兒已消失在時代的塵埃里,新的月牙兒破云而生,在澄明的夜空,映著蒼穹下的萬事萬物。
我拭去眼角的淚,看看窗外,雨也停了,陽光穿透玻璃灑落我一身。我從文字里走出來,深深呼吸了一下現(xiàn)實的空氣,我抬頭看了看,沒有月牙兒,天空掛著太陽,它足以溫暖著我的心,使我有勇氣從容、淡然地走出去。
(編輯/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