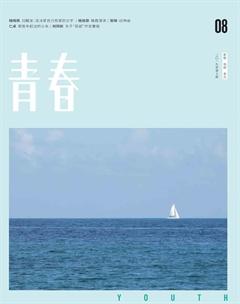關(guān)于“局部”作家曹寇
何同彬
作為“后他們”時(shí)代南京最風(fēng)格化的小說(shuō)家,曹寇具有某種“承上啟下”的功能,而且這種“承上啟下”有著一種潛在的破壞性,也即,曹寇一方面繼承了“他們”對(duì)宏大敘事、烏托邦、希望原則的無(wú)情嘲弄和堅(jiān)決摒棄,另一方面,在“日常主義”“平民化”等維度上,他走得更遠(yuǎn),或者說(shuō)走向了極致。所謂的“無(wú)聊現(xiàn)實(shí)主義”“屌絲文學(xué)”中那些新的“漫無(wú)目的游蕩者”(葛紅兵)、“卑污者”(郜元寶),已經(jīng)消解了“他們”一代糾纏始終的創(chuàng)新、突圍的焦慮,反抗、斷裂的沖動(dòng)。曹寇是一個(gè)懂得自嘲的虛無(wú)主義寫作者,他的寫作沒(méi)有明顯的文學(xué)目的性和流行的“野心勃勃”,也不刻意建構(gòu)“旗幟”“符號(hào)”,他真正實(shí)現(xiàn)了韓東所說(shuō)的“無(wú)中生有又毫無(wú)用處”“降低到一只枯葉的重量”。他在《我看“創(chuàng)作”》中說(shuō):“我已經(jīng)寫了十多年小說(shuō),卻覺(jué)得自己完全不會(huì)寫小說(shuō),眼前一片黑暗。”在近期一篇的“自傳性”小說(shuō)中,他借人物之口再次申明:“時(shí)至今日我仍然認(rèn)為,書法家是個(gè)笑話,就好比小說(shuō)家是個(gè)更大的笑話一樣。我只是無(wú)事可做。” 拉波爾特在談?wù)摬祭市さ臅r(shí)候?qū)懙剑骸巴呃桌铮骸畼?lè)觀主義者寫得很糟糕。但是悲觀主義者不書寫。”(《今日的布朗肖》)曹寇是悲觀主義、虛無(wú)主義者中還在堅(jiān)持寫作的人,這成就了他的鋒利和睿智,也在消解著一些曾經(jīng)生機(jī)勃勃的野蠻力量。某種意義上講,當(dāng)代文學(xué)最具活力和野性的“他們”文脈,被曹寇的冷靜和“虛無(wú)”一手“終結(jié)”,韓東、朱文、顧前、魯羊、吳晨駿、劉立桿、外外,還有曹寇、趙志明、李檣、李黎、朱慶和,以后的南京乃至全國(guó)再也很難有這樣的“一群”作家了,這是一個(gè)令人傷感的現(xiàn)實(shí),正在“生動(dòng)”地實(shí)現(xiàn)——已經(jīng)不可逆轉(zhuǎn)。
曹寇代表著南京乃至當(dāng)代中國(guó)文學(xué),尤其是青年寫作的某種特殊的質(zhì)地和傾向,在他的作品和小說(shuō)觀念的影響下,一個(gè)結(jié)構(gòu)松散但旨趣親近的文學(xué)群落已然形成。曹寇代表著這個(gè)群落的“文學(xué)形象”,由此也戲劇性地印證了韓東對(duì)他的“夸獎(jiǎng)”:“小說(shuō)大師的年輕時(shí)代”。與韓東類似,曹寇不僅僅是一個(gè)小說(shuō)家,而且是一個(gè)突兀的、持續(xù)性地制造著“不適之感”的文學(xué)形象。同時(shí),作為一個(gè)風(fēng)格化極其突出的小說(shuō)家,曹寇引領(lǐng)和召喚出一種風(fēng)靡一時(shí)的寫作傾向,在啟發(fā)了一批青年寫作者的同時(shí),曹“大師”也成了一些年輕人無(wú)法擺脫的與風(fēng)格、表現(xiàn)力和智性有關(guān)的陰影,這一陰影最后也將長(zhǎng)久地“限制”和影響著曹寇自身的創(chuàng)作和“生長(zhǎng)”。
這么多年來(lái),曹寇與這個(gè)時(shí)代的“文學(xué)性”格格不入,盡管他也曾努力化解這種對(duì)立,但秉性中對(duì)于真相的迷戀、對(duì)于直言的渴望(性話語(yǔ)和粗口是必然的美學(xué)伴生物),最終腰斬了這些世故性的努力。與此相應(yīng)的美學(xué)后果卻是可愛(ài)的,無(wú)論是他的小說(shuō)作品,還是隨筆、散文和言談,幾乎看不到虛偽的、大而無(wú)當(dāng)?shù)摹按涝挕保@是一種越來(lái)越罕見(jiàn)的文學(xué)品質(zhì)。當(dāng)然,這是通過(guò)極大降低話語(yǔ)和敘事的戲劇性和豐腴性為代價(jià)的,這一代價(jià)給曹寇的寫作帶來(lái)了某種“局部”性或者所謂的“局限性”。把曹寇稱為“局部”作家源于其最近的一個(gè)短篇小說(shuō)《文藝生活的局部趣味》。曹寇的風(fēng)格是局部的、題材是局部的、經(jīng)驗(yàn)是局部的、優(yōu)點(diǎn)是局部的,當(dāng)然,缺點(diǎn)也是局部的。局部即對(duì)應(yīng)著某些局限性,與那些焦慮于自身局限性的青年作家不同,曹寇并不急于通過(guò)嫁接歷史和知識(shí)的策略,擴(kuò)張自身的經(jīng)驗(yàn)和視域,而是幾乎“故步自封”于自身的“局部趣味”。對(duì)于曹寇的寫作而言,這種“局部”或“局限”就像是建筑的層高,其實(shí)是很難突破和逾越的。比如《市民邱女士》《塘村概略》(如同阿乙的《下面,我該干些什么》)就試圖為日常化敘事植入一些評(píng)論家、闡釋者樂(lè)于“發(fā)現(xiàn)”的那種日常生活、熱點(diǎn)事件的“復(fù)雜性”,此時(shí),曹寇擺好陣勢(shì),想與強(qiáng)大、頑固的世俗人性的愚蠢和偏見(jiàn)短兵相接,并且生發(fā)出與眾不同的“觀點(diǎn)”和“意義”,結(jié)果是“層高”不夠,就像是小孩穿上了大人的衣服,顯得有些笨拙和滑稽。所以,某種意義上講,曹寇必須堅(jiān)守這種“局部”,正如他的辯解:“事實(shí)上,關(guān)于局限性的問(wèn)題本來(lái)就是個(gè)偽問(wèn)題,它所指涉的其實(shí)是成功學(xué),而非文學(xué)。在我看來(lái),無(wú)限放大我們的局限性,才是文學(xué)的價(jià)值所在,也唯有在局限性中,我們才能獲得誠(chéng)實(shí)和切膚。好的作品,無(wú)非是靈與肉無(wú)比合身的結(jié)果。”而問(wèn)題在于,“局限”“局部”該如何面對(duì)重復(fù)和貧乏。
幾年前我有一個(gè)短評(píng),具體談?wù)摬芸軐懽鞯奶攸c(diǎn)。由于曹寇寫作對(duì)“局部性”的固守,因此,其中某些論述仍舊有效,現(xiàn)在擷取片段贅述如下:
閱讀《越來(lái)越》的時(shí)候就準(zhǔn)備為曹寇的小說(shuō)寫一篇觀感,題目草擬為《草寇曹寇的草性、操行和操性》,如今仍然適用于這本新的小說(shuō)集。
《屋頂長(zhǎng)的一棵樹》延續(xù)了曹寇小說(shuō)在故事和人物上的平庸的、日常的、瑣碎的“草性”,那些“野火燒不盡,春風(fēng)吹又生”的雜碎的、卑賤的人物身上的欲望、夢(mèng)想、囈語(yǔ)乃至毀滅,都在曹寇徐緩有致、絮絮叨叨的日常化敘事之下,呈現(xiàn)出瑣屑與宏闊的奇特張力;人性在孩童時(shí)代觀看、賞玩事物的不厭其煩的耐性,被曹寇頑固的青春記憶無(wú)限推延,然后經(jīng)由他粗魯、俏皮、反叛卻又無(wú)比真實(shí)的語(yǔ)言風(fēng)格,結(jié)構(gòu)成一幅幅看似了無(wú)生趣,實(shí)則趣味叢生、機(jī)鋒不斷的生動(dòng)畫面。曹寇寫作的“草性”或者“庸常性”,嚴(yán)格區(qū)別于那些自然主義的“新寫實(shí)”和矯揉造作的“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更不屑于與那些偽造的“民間”“底層”“草根”等名目繁多的階層性書寫為伍,他只是一個(gè)小聲說(shuō)話、絮叨些無(wú)聊的事的人,他的那些偶然性的寫作既不想供人娛樂(lè),也不想啟蒙、教化。那些邊緣的、平凡的、失敗的小人物身上的頑固的、無(wú)聊的庸常性及其苦痛,映射的并不是某一個(gè)階層、某一類人的病癥,而是包括他自己在內(nèi)的每一個(gè)人的、每時(shí)每刻都無(wú)法脫離的困境。由此,曹寇寫作的這種頑強(qiáng)的“草性”也就成就出他在當(dāng)代青年寫作和當(dāng)代小說(shuō)美學(xué)上不可多得的獨(dú)特“操行”。
實(shí)際上,真實(shí)、真誠(chéng)、真相三個(gè)“真”就足以完成曹寇小說(shuō)的“操行評(píng)語(yǔ)”。他以真實(shí)的讓人厭倦和絕望的現(xiàn)實(shí),與真誠(chéng)得荒誕不經(jīng)乃至讓人啼笑皆非的生存態(tài)度,逼迫出日常生活每一個(gè)縫隙中或赤裸裸或妙不可言的真相。這種特征在《屋頂長(zhǎng)的一棵樹》中尤其明顯,證明他已經(jīng)基本上從他的南京前輩的“影響的焦慮”中走出了,那種為了表現(xiàn)反叛姿態(tài)而生的“為真實(shí)而真實(shí)”的日常化、粗鄙化、欲望化敘事,也已逐步被一種從容、蕭散、機(jī)敏的敘事方式取代了。曹寇不為潮流寫作,不為批評(píng)家寫作,甚至也不為讀者寫作,他的這些小說(shuō)“習(xí)作”不過(guò)是一個(gè)平庸、卑微的人的自我慰藉,或者就像葉兆言所說(shuō)的,曹寇不過(guò)是南京那些“玩小說(shuō)”的人之一,只是他玩得很好。這種創(chuàng)作態(tài)度在當(dāng)下的中國(guó)小說(shuō)家中還是比較少見(jiàn)的,如今,文壇上充斥著太多大而無(wú)當(dāng)、虛與委蛇、“假模三道”的小說(shuō)劣作,真實(shí)而有趣的小說(shuō)成了一味“藥”,來(lái)暫時(shí)性地解一解那些虛偽的陳詞濫調(diào)的“毒”。不過(guò),也就僅此而已,曹寇及其小說(shuō)不會(huì)給我們帶來(lái)那么多如今被屢屢標(biāo)榜的“附加值”,庸常就是庸常,不要指望生出高貴的、理想的蛋來(lái);他的身上痛苦地反映出當(dāng)代那些心懷義憤卻又做不到義無(wú)反顧的文藝青年共同的“操性”:真實(shí)又虛弱的反抗。
如今,這仍舊是曹寇的“局部”,或者說(shuō)是“局部”的曹寇。多年之后,當(dāng)我重新引用以上的文字時(shí),時(shí)間和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整體性貧乏已經(jīng)耗盡了當(dāng)年文字中包含的某種“批評(píng)”“批判”的合理性、必要性,此時(shí),我竟然覺(jué)得這種“局部”未必需要更改或者超越。就好比以下的文學(xué)“如果”是毫無(wú)意義的:如果曹寇和顧前少喝幾頓酒、少打幾把摜蛋,那他們就有時(shí)間寫出更多的好作品,或者不至于像現(xiàn)在這樣“故步自封”“后勁不足”。因?yàn)槲覀儫o(wú)法在一個(gè)單純文本的、進(jìn)化論式的觀念系統(tǒng)中評(píng)價(jià)這樣一些作家,他們并非絕對(duì)忠誠(chéng)于所謂“文學(xué)”,或者說(shuō)一般意義上作為一種觀念系統(tǒng)和生活方式的文學(xué)不過(guò)是“他們”人生的“局部”,而且并非是最重要的“局部”。
以下引述的兩段布朗肖的話,曾經(jīng)在一個(gè)評(píng)論中“贈(zèng)予”了黃孝陽(yáng)(他與曹寇是南京小說(shuō)界兩種迥異風(fēng)格的代表,始終處于表面互相恭維、背后互相“鄙視”的極端分裂狀態(tài)中),現(xiàn)在再次贈(zèng)予“局部”作家曹寇:
“文學(xué)的本質(zhì)目的或許是讓人失望。”
“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任務(wù)之一,要讓作家事前就有一種羞恥感,要他良心不安,要他什么都還沒(méi)做就感覺(jué)自己錯(cuò)。一旦他動(dòng)手要寫,就聽(tīng)到一個(gè)聲音在那高興地喊:‘好了,現(xiàn)在,你丟了。——‘那我要停下來(lái)?——‘不,停下來(lái),你就丟了。”
主持人:黃平
編輯:張?jiā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