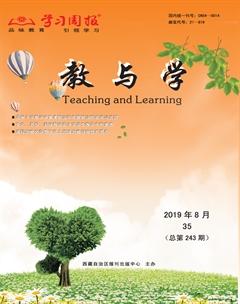簡析沈雁冰革新后的《小說月報》(1921-1922)與中國新文學的嬗變
楊雪鈺
摘 ?要:文學期刊可以作為船舵影響著文學的發展態勢。經沈雁冰“半革新”“全面革新”后的《小說月報》順應了中國古典文學向現代文學轉型的大勢,見證了新文學萌芽發展期的同時,也發揮了期刊作為“指揮者”的作用,為新文學的延續與發展開辟了明亮的前景,對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促進作用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關鍵詞:沈雁冰;《小說月報》;新文學;新舊文學論爭;“為人生”的創作動因
本文從革新后《小說月報》的“文學觀念”“時勢影響”“作家群體”三個方面入手,論證“沈雁冰革新后《小說月報》與中國新文學的嬗變”的觀點,從而加深對“新”《小說月報》與新文學發展關系的認識。
一、沈雁冰革新《小說月報》的背景
在我們對革新的歷史背景作敘述之前,應先了解早期《小說月報》的辦刊定位。在創刊號的“編輯大意”中,印有“本報以迻譯名作,綴述舊聞,灌輸新理,增進常識為宗旨”的說明。“迻譯”及“新理”即把視野投向西方文學;“舊聞”即敘述中國自己的傳統故事。由此看來,《小說月報》在開刊之時就有了中西雜糅、新舊交融的意識。這半新半舊的理念體現在早期《小說月報》運作過程中可概括為:商業性與文化性的統一。兩者雖屬不同領域,卻發生著長足的交鋒與互動:商業性要求雜志以盈利為基本前提,因此報刊必須著眼于當時讀者的需求,保障內容的可讀性、娛樂性,即文化性。《繡像小說》曾是商務印書館創辦刊物之一,其具有“更重視可讀性”“更重視面對市場”的特點。因此從《小說月報》“編輯大意”中:“本館舊有《繡像小說》之刊,歡迎一時,嗣響遽寂,用廣前例,輯成是報”的敘述可以明確《小說月報》向《繡像小說》靠攏,同有抓緊市場、有意流俗的傾向。在1918-1919年王蘊章擔任主編時期,更是將通俗文學“鑲嵌”進了《小說月報》,大量地收錄“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小說,造成了娛樂性通俗作品占“80%以上”的情形。當《小說月報》沉浸在“哀感頑艷”的苦海之時,新文化運動及新文學革命提倡的“白話文學”波涌而來,帶著“激進”的姿態勢必為實現自我發展的合理化、普及化掃清障礙。因此我認為《小說月報》亟待革新的主要原因是處于新舊文學論爭的風口浪尖,而雙方駁論的結果是新文學以其激昂的勢氣旗開得勝。而以商業性為運作根本的《小說月報》自然得向新文學妥協,以保證自身盈利。
二、新文學觀念的倡導:為人生的藝術
對“現實主義”文學觀念的提倡,在《新青年》和五四運動時期就有所體現。例如《新青年》4卷6號推出的“易卜生號”詳細介紹了這位挪威戲劇家及其劇作《玩偶之家》,并由此掀起了“易卜生熱”。值得關注的是易卜生的劇作主題表現為對現實問題的揭示及主人公不拘泥于束縛因而奮起反抗的精神。此外,《新青年》自覺擔任國際政治思潮的“傳聲筒”,發表在刊的相關文章數不勝數:如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東方問題之題要》。由此看出,早在《新青年》時期,就注重以嚴肅的文學觀念為準則選擇并發表與生活實際貼近的文章。但真正大規模實踐了寫實主義,并主張文學作用是指導人生的工具的人是沈雁冰,他有著運用并發展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自覺。在《新舊文學平議之評議》中,他將“新文學”描述為“有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能力”;稱文學作品不再是“消遣品”,而應具有中國時下迫切需要的能反映實際且指導生活的功能。所以他重視現實主義,主張“學習自然派作家”。沈雁冰的這種現實主義自覺還表現在他自己的創作中,在《子夜·后記》中有“我有了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的企圖”的自白,因此我們將沈雁冰稱為中國現實主義第一代言人也不為過。
三、驅時勢:以西為法
《小說月報》之所以長期能夠在與同期雜志的競爭中站穩腳跟,成為“在民國初年和五四運動以后影響很大的文學刊物”,是因為它在創刊之初就將自身運作理念明確為“綴述舊聞”“灌輸新理”“增進常識”。顯然,在開刊之初,商務印書館就沒有忽視灌輸西理的學習意識。而隨著《小說月報》的流俗,我們會忽略對早期其引入西方學理嘗試的事實,而對其娛樂性、休閑性大加鞭笞,這也是我們對早期《小說月報》的誤解。其實在沈雁冰實行革新之前,即王蘊章、惲鐵樵先后擔任主編,被后人評價為《小說月報》最艷俗的時期就存在引入西方文學理論,學習西方文學標準的嘗試。如第一號“譯叢”欄目共刊出四篇,雖然大都以娛樂性為主,但也有《英美報紙之發達》這篇實用文章的發表。還值得注意的是從1卷2號增加的“雜纂”欄,雖其設置的重頭戲仍是娛樂性的那大部分,但占其中小部分的中外知識確是“開明智”而珍貴的,這是后人研究《小說月報》不可忽視,不可不承認的事實。正是因為早期《小說月報》有著以嚴肅的態度和從實用的學理層面引譯、介紹外國文化的“先風”,使得沈雁冰能夠實施“半革新”,創辦“小說新潮欄”變得水到渠成、有跡可循。雖然他在往后的回憶文中聲稱自己與當時的新思想并無過多接觸,但從今天看來,沈雁冰在主動學習西方的認識方面有著極其強烈的先鋒性。與其說他去接受了新思想不如說新思想早已一直內化并存在于他的意識內。
四、《小說月報》與作家群體
一般來說,作家群體一旦產生,就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但值得關注的是,以沈雁冰改革《小說月報》為分界線,前后的作家群體在短時間內發生了質的變化,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新的作家群體不斷壯大。那么沈雁冰在革新雜志的內容之余怎樣吸收、培養、鞏固了新的作家群體,使得《小說月報》產生無數佳作順應甚至引領了新文學的發展,這是我們以下要探討的問題。首先,沈雁冰極其重視作家群體,他認為“文化者現在是站在文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分子”并號召中國的文化者要心懷創造國民文學的責任。因此,沈雁冰非常渴求新文學作家能向雜志社投稿:在12卷1號《小說月報》“改革宣言”的第四條中,有“特辟此欄以俟佳篇”的說明;在《春季創作壇漫評》中有向他人借佳作,流露出期盼的真心;12卷4號起刊登的“本社投稿簡章”,進一步明確了作家投稿的報酬及相應的要求,有力的保障了雜志作家制度的規范化,鞏固了雜志的作家群體。除了沈雁冰本人熱切的期盼及以上提到的相關條例外,《小說月報》在運行實際中,無時無刻不在踐行著推介作家、發表新文學佳作的使命。據我粗略的統計,自沈雁冰擔任主編,施行徹底革新,即1921-1922兩年時間內,共有23期(其中12卷10號為“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12卷12號外“俄國文學研究”已排除)刊登原創作家作品(含小說、劇本、詩歌)共186篇,涉及作家67人。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據,因為每一號的《小說月報》至少設有10個欄目,而“創作”欄只占其中之一。時間證明,沈雁冰終究是盼來了佳作,翻開《小說月報》12、13卷發表的文學作品,確是新文學發展道路上的典型之作,在文學的歷史進程中留下濃重的一筆:冰心女士的《笑》《超人》;王統照的《沉思》《微笑》;葉圣陶的《低能兒》《潘先生在難中》等皆是“問題小說”和人生寫實派小說中的力作,極具典型性。我們知道革新后的《小說月報》是文學研究會的代用刊物,因此這部分作家群體是《小說月報》的主體作家,但僅從1921-1922年發表在刊的作家來看,也有不少非文研會的新文學作家。顯然,沈雁冰在革新之初,就看重培養自家的作家群體,因而采取“博采眾長”的態度吸收、歡迎作家及其佳作的入駐。這無疑為《小說月報》增添鮮活的生命力,也為新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生的力量。
結束語:
關于沈雁冰革新《小說月報》的史實歷來被人們不斷研究、挖掘。如果說1917年的文學革命是一場無硝煙的戰爭,那么新《小說月報》就扮演著戰爭參謀、兵器運輸員的角色,這無疑為新文學的發展加柴積薪,引導著新文學生長的方向,為其得以在中國文壇扎根并壯大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革新后的《小說月報》與新文學之間的影響是雙向的,兩者在歷史進程中不斷互動:新文學的興起為《小說月報》的革新提供一個適宜的環境,而在沈雁冰指導下的《小說月報》更是呼應著這場文學運動,更甚于一個指路人,發揮著對新文學的促進作用。表現為以下三點:首先,沈雁冰號召“為人生”的文學觀,一改往昔致力于流與世俗的娛樂文學,將文學定位為改善人生的工具,同時為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其次,以嚴肅的文學觀念選擇翻譯的方式及內容,其中介紹外國事宜的文章有效地提高了民眾對外國事物的認識,具有一定的科普教育性。再次,以《小說月報》主張的文學觀念為原則,培育了一批新興作家,為新文學的發展注入鮮活有力的力量,成為寶貴的文化資源。因此,革新后的《小說月報》與中國新文化的嬗變相互推動,彼此見證。
參考文獻:
[1]《編輯大意》[J].《小說月報》1卷1號,1910年:1頁.
[2]潘正文.《<小說月報>與中國文學的現代進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11:9頁、20頁、62頁.
[3]茅盾《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J].《小說月報》13卷7號,1922:1頁.
[4]志希(羅家倫).《今日中國之小說界》[J].《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