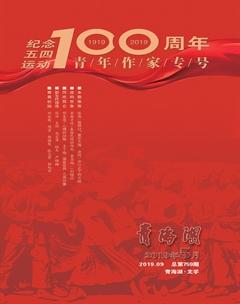在成長中帶著擦傷穿過絕境(評論)
馬鈞
作為新千年我省嶄露頭角的短篇小說作者,張強(筆名央北)一直保持著穩健上升的創作力。如果省心省力地按照職業去劃分,他可以順溜地劃歸到石油作家這個當今文學界視為落伍、僻遠、狹小、邊緣的創作類別里。盡管這種老式的劃分可以輕而易舉地見出他在某些小說題材上的職業表達偏向——表現石油工人的生活,但它也大大局限了我們對這位80后(幾乎臨近90后)小說作者在虛構世界中左沖右突的創作潛力的全面考量,甚至障蔽掉他逐漸拓展著的敘事疆域。
事實上,他一直在磨刀霍霍地營造著自己的虛構天地。在我集中閱讀他初具規模的短篇小說之前,坊間已經出版有他的幾部傳記體文字,比如《那一世,我遇見了你:倉央嘉措的今生今世》《楊絳傳》《當愛已成往事:徐志摩詩傳》。我還在一次他在西寧參加培訓學習期間的短暫聊天中,得知他下一步的一個寫作計劃就是寫作一部《玄奘傳》。僅從他駕馭這些來自不同時代、不同領域、不同文化、不同人物的創作題材時的寫作自由度和隨性調整創作視野的開合度上,我已經嗅出他作為新生代小說作者不同于傳統作家的地方。他們在寫作上特能“東吃西嗅”,越界跨疆。其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已經不完全是一個拘囿于輕車熟路的經驗型書寫者,他們相對瘠薄的社會閱歷和人生經驗,尚不足以去支撐起氣派恢宏的虛構殿堂,他們便采取輕輕雀躍于半空的寫作法術,巧妙利用海量的各種間接經驗和間接知識,與自己一鱗半爪的身經目驗進行榫卯和“混搭”。酷似于江南局促之地的園林營造法式,他們頻頻以“借景”來擴大他們虛構的格局。傳統作家習慣于書寫自己所膩熟的某一特定領域的生活,而央北這一代文學新人,已不那么執著地謹守于窩邊的那一叢青草,他們更樂于去“遠取諸物”,嘗試開辟新的領域,或者說他們更樂于神游于經驗藩籬之外的各種領域,哪怕那是一片他們極不熟悉的世界,他們仍舊會帶著巨大的創作激情去一試身手,哪怕是在異陌之地留下趔趔趄趄的身影。他們的知識結構、想象途徑、創作的興奮點,已然有別于他們的前輩作家。藉由這么一些資稟和異質,他們必將把一些嶄新的元素注入到敘事文本當中。
之前我僅讀到他的短篇小說《黑夜之光》,僅憑這一單篇孤例,我那殘留的“學院派概括癖病毒”小有發作。我曾在一篇關于青海當代文學短篇小說的微型報告里,率意地把我看到的短篇小說類型,分為農村敘事、草原敘事類型,把《黑夜之光》“分揀”到一種跨界的混合類型里,鄙意以為:《黑夜之光》屬于“荒原敘事”類型里蘗生的一個新類型——“荒原敘事”與“工業敘事”的嫁接。小說描寫的是地處荒原的石油小鎮和鉆井工人孤獨、寂寞的精神世界和充滿疼痛感的情欲世界。在這里,“千里荒原被金色的光芒覆蓋,高聳的井塔如一根根銀針扎在這片荒原的血肉里”。作者所賦予小說主人公的那種既孤獨又略含詩意的“空曠感”,在當代小說中已屬于極為罕見的文學書寫,小說中有一段令人過目入心的描述——
我跟季年的通話常常伴隨著風聲,那些風聲嘈雜而兇猛,以致我們任何私密的話都不能說,因為聽不見只能大聲吼,而這座山頭上打電話的男人不止我一個。
以前的時候我喜歡看荒原上的日落,那種不可逆轉的宏偉感才能摧毀這片荒原的寂寥。可后來我給季年打電話的時候常常顧不得看日落了,掛掉電話一抬頭就是滿天星辰。荒原上除了井隊上的那一點光外,再也沒有光亮,星星因此格外閃亮。
就是在這樣的生活舞臺上,這群荒原小鎮上的石油人演繹著他們的激情、他們的向往、他們的苦悶、他們的猜忌、他們內心的堅韌,還有世人難以抵達的那種荒原世界里的尖銳的疼痛感和浩茫的憂郁。在當代小說的形象畫廊中,工人形象的日漸缺失和暗淡已成為當代小說創作里的一種氣候和潛勢力,央北的“荒原敘事”加“工業敘事”,無疑為當代小說雕塑了被遺忘的存在和一群幾乎成為我們認識盲區的存在者。
時間僅僅跨過了短暫的幾年,待央北把他即將付梓的短篇小說集《愿長夜可被慰藉》的電子版發到我的郵箱里,8個短篇組成的敘事版圖已不復是當年《黑夜之光》所能覆蓋的地盤。要想讓鞋子合腳,不能再去采取削足適履的思維自殘,而只能本分地去尋找合腳的鞋子。與傳統作家容易鈣化自己的經驗、鞏固自己的創作根據地相比,央北們更愿意去建立盡可能多的虛擬據點,更愿意去旁逸斜出,超越既有的創作領地。8個短篇中,除了《黑夜之光》,還有延續“荒原敘事”加“工業敘事”的新作,比如《荒原狼》。即便是《荒原狼》,也已經衍化為此種類型的敘事亞種。其更多的篇什已經“移步換景”,別開生面。我仔細尋味了一番之后,覺得可以換用“成長小說”這一更為匹配的批評框架來觀察央北的短篇小說。
依據背景資料,我們知道成長小說起始于18世紀末期的德國。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漫游時代》被認為是這一小說類型的原始模型。成長小說進入當代中國之后,經過意識形態改造,結出本土化的果實。中國的成長小說與西方的成長小說最大的區別就在于:西方的成長小說主要是敘述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發展,敘述他們的各種遭遇和經歷,并通過巨大的精神危機長大成人的故事。而中國式的成長小說,主體積極的完型幾乎未見,而逆反式的與被動式的成長敘事則顯得過剩,尤其是現當代中國成長小說,常常表現為主人公成長的晚熟。及至當前的一些成長小說,擺脫了對巨型歷史時段和事件的依傍,而轉入日常生活的既定秩序對成長的磨蝕與改寫。敘寫“成長中”狀態或“成長的破碎”狀態的作品呈趨熱態勢。央北的小說,作為主體的敘述角色,幾乎都聚焦于二三十歲的青年人身上。他們這些人中較為成熟的一些人,在故事中都扮演著對其他晚熟人物進行生活啟蒙和人生向導的角色。比如《黑夜之光》中工友黑子與陪酒女辛霜之于井下工人張白穆,《荒原狼》中社會上的“混混”灰哥之于工人張鳴一,《和光同塵》的林智夏、顧遠竹之于“傻丫頭”李小冬,《最后的時間》中酗酒后殺了母親的父親顧海之于兒子顧生林,《裝甲車》中的大哥李向陽之于他的三個哥們張遼北、陸宇遠、宋多米,《在山不遠》中李鳴鵲之于陸六,都程度不同地成為后者人生覺醒的啟幕者,或者是后者人生閱歷中突然打開另一面世界的人物。正是這些“啟蒙人物”,或者促成被啟蒙者自天真無知至成熟的歷練過程,或者引領他們進入社會吃虧吃苦,逐漸明白世途的艱難和人心的險惡,或者引領他們經歷某個或某些重大事件而使他們的人生軌跡有所改變。
進一步來探討央北的“成長小說”,我想援引作家阿城的一個說法:“不管你是古人也好,你是現在的人也好,你是未來的人也好,都會有絕境,有過不去的檻。所以我說好的作品常常是穿越這個絕境的。”我以為,這個說法可以給“成長小說”這個已初現骨質疏松端倪的概念,補充到豐肌強骨的“鈣添力”。成長的最大關節點,乃是遇到“過不去的檻”,就是吃塹,就是開眼,就是見世面,就是對人生的諸般禁忌來一次次的脫敏體驗。
央北的短篇小說里,設置了各式各樣的“成長絕境”。
絕境之一:原本屬于“荒原敘事”加“工業敘事”這一混合類型的,基本上都是描寫坐落于荒原上的石油小鎮——“西鎮”人的生活的,他們遇到的巨大絕境就是荒原工廠生活難以消受的寂寞與無聊。因為這個絕境,老一輩石油人采取了一種燃燒式的奉獻與犧牲。而小說里的年輕一代,恰恰被這個絕境導演出“一夜情”、離婚、酗酒、賭博、逃離、情感背叛等一件件事涉命運變化的事情。同時,年輕一代也借著情感背叛、逃離、賭博、酗酒、離婚、“一夜情”等方式,抵抗著他們難以排遣的無聊和寂寞。這個荒原的可怕,正像《黑夜之光》里的一句描述:“我臉貼著車窗,荒漠的黑夜像磚塊一樣,一塊一塊扎實地壘起來,這一下連過去也看不見了。”
絕境之二:年輕一代的選擇自由仍舊被他們的父輩們所操控,繼而埋下兩代人之間難以彌合的矛盾甚至仇隙。比如《黑夜之光》中的張白穆是被父親強硬的態度逼回西鎮的,他的相親和提親也都是老媽一手安排操辦的;《云光》里的白喬婚姻失敗是婆婆阻攔的——“她和他領了結婚證,然而在新婚不到半年的時候,遭到了婆婆的阻攔,阻攔的理由是嫌棄白喬的性格太風風火火不適合過日子。”《荒原狼》中的張鳴一是被父親弄回石油局當采油工的;《在山不遠》中的陸六所有的厄運都來自于父親給他起了一個引人嘲謔的名字;《最后的時間》里主人公“渴望去當一名職業吉他手。這個想法遭到了父親的強烈反對,顧生林真正顧忌的不是父親的反對而是顧生夏是否反對”。
絕境之三:婚外戀。比如《云光》里的白喬與何生之戀,《黑夜之光》里張白穆和辛霜之戀,《在山不遠》里的陸六與李鳴鵲之戀。小說里的婚外戀最后的結果并不是打破他們既有的組合而轉向新的組合,而是愛過、痛過之后走向分離,走向訣別。
絕境之四:重大變故。正如《和光同塵》里作者借林智夏之口所道出的“絕境哲學”或“成長哲學”:“真正讓人成長的不是時間而是事件,比如失戀,比如親人的逝去,再比如事業的挫敗。這是林智夏領悟到的道理。”如此,央北試驗了諸多人生的變故形式。比如《云光》里的何生結婚后,“經濟負擔、女兒的病,讓他沒有時間再拿起吉他了。”“女兒誕生后就是肌無力患者,何生把這個錯歸咎于蘭榮,從而喪失了愛意”,導致其最終的移情別戀;《荒原狼》中的張鳴一因為父親燒傷毀容,逃離單位,逃離讓他痛苦的家庭,在社會上賭牌失蹤,最后又因父親為營救他而償還賭債,而自斷手指;《和光同塵》中,少不更事的李小冬一是經歷了爺爺去世的重大打擊,二是經歷了與顧遠竹由一廂情愿到失戀失蹤再到經歷一場火災;《最后的時間》中顧生林遭遇了骨癌和母親被父親因醉酒而殺害的雙重極端經歷;《裝甲車》中的大哥李向陽經歷了由截肢到自殺的絕境,而他們四人組成的哥們團隊,經歷了經商受到欺騙設局,大哥截肢后大家共同贍養接濟的歷程;《在山不遠》里的李鳴鵲離婚和發生婚外情的禍端是她被醫院查出雙側輸卵管堵塞。
面對這些絕境,央北的小說反復強化著一個潛在的價值指向,那就是選擇面對,緩釋撫慰的溫情,哪怕許多時候好像是在被動地躲避,逃離,出外散心,但隱伏在這些文字背后的一種自我拯救的激情還是涌動在字里行間,一種人性的力量和尊嚴在小說文本的段落和情節中擴大著它們不可輕視的音量。這使他常常在小說的結尾,不憚于被人詬病地“拖出光明的尾巴”——
她開車前往何生家,當時是陰天,大片的烏云籠罩著天空,一縷耀眼的陽光從厚重烏云的罅隙投射下來,那個方向正好是何生家。
——《云光》
那一刻眼前洶涌的火勢,李小冬并不覺得灼熱。她反而覺得這像曾經看見的一片火燒云,而這夜除了這片云之外,再無黑暗。
——《和光同塵》
我個人十分喜歡他的《裝甲車》,篇名與我們的閱讀期待所造成的巨大反差無疑是本篇的一個亮點,但其在反抗絕境后所重鑄的生命尊嚴,更是讓我見識到央北精神世界中可貴的精神鈣質,這一點尤其在他們新生代作者身上顯得彌足珍貴。“他(李向陽)自己在極短的時間里,做了截肢的決定。只是以后得靠人工激素進行維持了。”“即便是腿斷了,他仍舊在維護在我們中的尊嚴,像一個將軍一樣,站在獵獵風中,沖我們揮手,幫助我們實現那些微小的夢想。”“李向陽死得倔強而又殘忍……”“裝甲車上壞掉了輪胎,可是也要一馬平川地向前走啊。”
在《最后的時間》里,兄妹原本懷著復仇之火意欲將來有一天殺掉曾經殺害了母親的父親,故事的結局,卻走向了寬容與原諒:“顧海和顧生夏兩個人各自站在顧生林病床的兩邊,顧生林兩只手拍了拍床,示意他們都坐下來。他伸出兩只手,分別抓住了顧海和顧生夏的手,他用盡全身力氣把兩只手放在自己胸前,顧海的手放在顧生夏手上,顧生林用自己的兩只手緊緊蓋住他們的手,他說了句,好了。這句話并沒有聲音,只是做出了嘴型。”這樣的處理,顯示出作者在人性思考上已具備了可喜的深度和溫度。
央北小說在男女情愛世界的書寫上,確實已經顯露出與傳統作家在情愛觀上不一樣的表達。這種表達,一是時代使然,更是其所描寫的荒原地帶人們情感存在的一種真實樣態,它們作為一種新的生存現實和精神存在,已經很難再被舊有的道德利刃所戧割和評判,而只能以一種人性的觀照所寬宥和通融。就拿《黑夜之光》中的若干片段來管窺——“最近的一場酒宴是因為我們的一個女伴離了婚,她說起這事的時候無驚無喜,就像是揉掉一顆隔夜的眼屎般容易”“婚姻在這里不過就是履行程序般,走一遍就好”“這里的一夜情就是每天食堂里倒掉的剩飯,吃過了就倒掉,不會再端上飯桌”。這種新的現實書寫,昭示了作者直面人生的坦誠、敏銳和勇氣,也隱含著這一代作者們的憂懷,愛的戰栗與遺忘,對愛之崇高價值的崩解的無奈與感傷。
我特別注意到《愿長夜可被慰藉》的電子版的排版設計里,每一篇名的白底白字都被打在漆黑的頁碼上,像是荒原的幽暗與閃光。“黑夜”作為時間的一種形式,被央北布景似的安置在每一篇小說人物命運和生活發生重大轉變的時刻,因而夜晚在他的小說中具有了物理時間和心理情境這兩種敘事功能。這讓我想起以拍攝夜景聞名于世的法國攝影家布拉塞說過的一段話:“夜晚將事物隱約地暗示出來,卻從不清晰地展現它們。夜晚的怪異之處使我們感到驚奇和不安。它將我們體內那些白天被理智所控制的力量釋放出來。”在央北全部的小說里,小說中的人物在夜晚展開他們欲望的另一面,也是“夜生活徹徹底底”讓他筆下的人物“了解到這個活生生的戈壁”,釋放出他們蟄伏的野性欲望。
與夜晚具有異曲同工之效的是,央北在全部的小說里,都會在人物遇到“絕境”、遇到“過不去的檻”、遇到重大人生變故的時候,總要植入各種各樣的“夢境”。這些紛雜凌亂的夢境,要么作為隱喻在暗示著人物的某種糾結、可怕的處境,要么它們就像一段閃回的記憶復制著往昔的瞬間,要么在表達著人物潛在的欲望和向往。這些夢境的穿插,使其小說形成了一定的心理維度。但總體上看,央北的夢境設計有時候顯得草率,還不那么與整部小說的意蘊形成精巧無比的關聯和映照,有些情節就像設置了“快進播放器”,文脈走得過快,失卻了草蛇灰線般的縝密和敘事的內在張力。有些敘事破綻,暴露出央北的敘事底氣尚有待充實。
央北屬蛇,其前輩作家里,至少與他同一屬相的格非,早年間被胡河清視為“蛇精”,富含詭秘、詭譎的寓意。大概是央北生于西北之地,生于荒原戈壁之城,我在其文字里倒沒有嘗出多少詭譎的味道,但能嚼出北人的倔勁和北人式的靈氣。只是這靈氣最害怕滿世界彌散的躁氣。我能體諒如今在繁瑣工作之余烹文煮字的業余作者的艱難與不易;要在身心疲憊之余,在種種娛樂刺激的干擾與強勁誘惑之下,忙中偷出一小片一小片文字的光芒,這種事情,真難!唯其艱難、不易,意欲有成,非得從善始把自己一鏨子一鏨子,又穩又準地敲進善終里。否則前功盡棄。
我們都不具備西西弗斯反復推石上山的耐性和意志,我們只有一次機會去趨近完美地敲打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