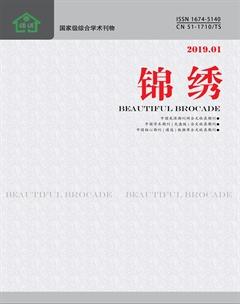喜常傳
羅玉
題記:斯人已逝,然偶入吾夢,故以此文憶之、祭之。
喜常,一個村里大多數人都想不起的名字,當然絕大部分人也想不起在這個寧靜得連公雞都不好意思打嗚的山野小村里曾經會有過這么一位人物,我不知道那個時代的紛紛爭爭,只知道他住在一個因分地主財產而分得的本屬我家祖輩的簡陋的房子里,房子上下兩層直通,是那種出門見天進戶見瓦的結構,進門一間本該是堂屋(城里人叫客廳),卻被用做廚房兼餐廳,但同時也仍做堂屋用,地面是泥巴夯成的,不是很平整,進門左邊緊靠墻壁,墻壁上貼著一張陳年的關公畫像,也是他家里唯一一張墻貼,也許是緣于關公是喜常崇拜的偶像之故,記得他給我講過關公過關斬將的英勇故事,關公畫像往里掛著他最看重也是我最喜歡的家什一桿鳥銃,鳥銃下面吊著兩個火藥袋,鳥銃里是常填充著火藥的,就像《少先隊隊歌》里唱的“時刻準備著”,只要他起身出門就可順手操起鳥銃并在極短時間里扣動扳機開火,我不知道他心里提防著誰或者害怕誰,火統下的墻邊地上亂七八糟的擺了很多鐵錘、鐵棍、鐵釬什么的,我總覺得他不怎么喜歡這些家什,但這些家什卻是他的營生工具,因為他是一個石匠,在我的印象里他很少用這些家當去工作過,除了我父親建新房子時他扎扎實實的用這些又冷又重的家伙干了兩個月的活,我也是在這期間跟著他學會了使用這些工具,有天放學回家我用他的工具在我家門前的一塊大石頭上鑿了一個茶杯大小的洞,這塊巨石后來不見了,他雖然很少干這營生的活,卻能妙手生花,一塊任何形狀的石頭經過他的敲敲打打,總能找最適合這塊石頭的安身之處,任何一塊巨石,他只用幾樣小工具經過錘錘打打就能破開,他很少正經的干活,但每干成一次活,總能令我對他增添一分敬意,這些工具是常年生誘難得見一回陽光的。門對面的墻上掛著一個農民的常備件
蓑衣、斗笠,但基本上只是作為一種身份的像征,一年到頭也難得用一次,旁邊掛著幾件他引以為豪的戰利品
一張狐皮、兩張兔皮和一副什么獸角的,他偶爾會在酒后滿臉神氣地跟我講一些他打獵時的英勇表現,酒后講的故事亦真亦假,但也很令我對他心生敬意。緊鄰這面墻的是一面我也記不起有什么裝飾的黑墻,說它黑是因為倚墻而建的一大一小兩個土灶,長年累月的柴火煙薰,墻不黑也不行,這個土灶上只有一大一小兩口鍋,大鍋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反正在我的記憶里是沒用過的,小鍋是炒菜用的,煮飯用的是一只沙罐,沙罐煮出來的飯特別的香,而且在村里大多數家里吃薯米飯(大米不夠,常以薯米充數)的時候,這只沙罐里煮出的是香噴噴的白米飯,村里我的同齡人中能品味到這只沙罐煮出來的飯的肯怕也只有我了,土灶上頭還有一個神奇的機關,從梁上懸下的一根牛皮繩上吊著一只麻袋,麻袋里是大半袋大米,麻袋末端的一個角上開了一個洞,平時用一根皮筋扎著,每次要做飯時解開皮筋,麻袋里的米就滋溜滋溜正好流落進沙罐里,到他想要的量了就再扎好皮筋,但我特別好奇的是麻袋里好像永遠都有大半袋米,在那個時代里這是一件非常令人羨慕的事。大灶的后面是整齊并列的三只大酒壇,這三只酒壇永遠都最多有一只空壇,壇口用厚厚的棉絮封著,我能察覺到喜常每次走近這些酒壇時心情都是激動的,據說他從未談過戀愛,也許他把對女人的愛全都轉化成了對酒的摯愛,而且這種愛絕對超過了一般男人對婆娘的愛,因為當時在農村里,男人打罵婆娘是正常的,但喜常絕不允許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任何人糟蹋他的哪怕只是一滴酒,酒壇后面有一扇門,通往臥室,臥室陳設非常簡陋,一張也是從我家祖輩那分來的帶著雕花的舊床,床上整齊地鋪著陳舊但也算干凈的一套被褥,床底下有一個寶貝一只不大的酒壇,這壇里裝的是他家最好的酒,這酒一般人喝不到,我倒陪他老人家喝過幾次,外人也不知道他床底下還有這么一個寶貝,我想他每天晚上都是聞著這上等酒香進入夢鄉的,就像其他男人是摟著自己心愛的但又隨時可以打罵的女人進入夢鄉一樣。堂屋里還擺有一張吃喝待客用的桌子,只不過這張桌子比一般人家的要矮小一些,凳子也是通常人家里小孩坐的那種矮小凳,具體備有幾個記不清了,但肯定是兩個以上,因為我清楚的記得我跟他隔桌對飲過。
喜常平日里沒有別的去處,喜歡蹲在我家門前那塊被我鑿了個杯形洞的大石頭上長時間發呆,有時直到我的出現才可能結束他的這種呆狀,當然還有一個地方他特別喜歡去,就是我們村里一個神奇山巖洞,叫鵝泊洞,傳說古時一對天鵝飛經我村時,被一個獵人用鳥銃射殺了一只,另一只因失去了伴侶也不愿離開,就鉆進了這個山洞并化成了一只石鵝,故取名鵝泊洞,這個山洞縱深據說達三千米,常年流水不斷,水里生活著一種對水質要求極高的魚,經年累月的歷史形成了各種形狀的鐘乳石,入口只有一個大拱門的尺寸,但入洞后即有一處可容下十來張八仙桌的寬敞處,寬敞處往里左拐光線變暗,立于道旁的就是那只石鵝,據說村里年輕人談戀愛時都會和戀人一起來這反復撫摸這只石鵝,以期自己的愛情也像這對天鵝一樣忠貞不二,那個時代里離婚的少,也不知是不是這石鵝的靈氣所致,但后來很多來摸過這石鵝的年輕人卻沒被石鵝的靈氣所感染,婚姻維持得長長短短,好多都不得善終。洞內冬暖夏涼,洞頂倒掛無以計數的大型蝙蝠,喜常常帶我進洞捕蝙蝠,我當然只是看客而已,他每次只捕十來只,現場剝了皮帶回家,或煮或炒,加上個小菜,如果沒別人,他就會從臥室的床底下搬出那壇寶貝,舀上兩杯與我對飲,那時的我絕對是個“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余杯”的小酒仙,我的酒量應該就是這樣練成的。這個洞一般人是沒有進到過最深處的,因為很多地方沒有路,只能匍匐著爬行或淌水扶壁而行,即使這樣也不知前面是什么深潭怪險,萬一一腳不慎后果不堪設想,所以一般人都會半途而返,但喜常卻偏好這種險路,而在他的保護下我也不懼前方兇險,有一次我跟在他屁股后或爬或淌經過不知多長時間最終窮盡洞深處,洞窮處真可謂是一線天,深藍藍一大片水,水的盡處是一整面斜削巨石壁,壁面與水面成30度角,將手電筒照向如此陰暗至清的水里,欣喜間還能看到游動著的魚,這完全是顛覆了“水至清則無魚”的哲理,站在這無人踏至的水邊沙灘上,仿佛來到了另一個世界,水和沙灘都純凈得讓人不敢呼吸,我倆一老一少、一高一矮懷著不同的心情靜靜地站在透著涼意的沙灘上足有一刻鐘之久,他似乎在思考著什么,也似于悟到了什么,我總覺得此時的他與平日里的他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個人,窮洞而回不遠處有一岔道,循道而行,有一小洞,需俯身爬行方可入,入此洞后又是一處不足十平米的干爽平坦封閑處,除此小洞可入而無它處可出入,環視四周,確實與別處不同,洞中處處濕濕滑滑,流水聲響,獨此處干爽靜謐,幾米外的濕氣像被什么屏蔽了似的,幾米外嘩嘩的流水聲也似乎停止了傳播,喜常環視四周后在靠后壁中央一稍高處盤腿坐下,口念阿彌陀佛不止,我心中稍驚,但也無他念,這次游歷之后,喜常很少再帶我來此洞深處,只是偶爾來洞口捕捉蝙蝠改善生活。
論輩份,喜常是我爺爺輩,論年齡,喜常也比我爺爺小不太多,所以我常稱呼他喜常公公(公公是我們鄉村對爺爺的稱呼),也許是我有這種忘年交之緣,在我的生活中有那么幾位相交甚深的老年朋友,而喜常肯定是我忘年之交的第一位,而且也是對我有一定影響的忘年交老者,說他是老者因為他與我交往時我還是個孩子,而他已過中年,其實他并不顯老,我曾在他微醉小憩時仔細端詳過他,典型的亞洲黑里透著微紅的甄子丹式的臉龐,在一層米粒長短黑白相間的淺發的襯托下略顯清秀,一雙時常因過量飲酒而充滿血絲的眼睛看了讓人害怕,但于我卻是滿眼的溫柔,我清楚的記得他教我識字淇實他識字也不多)時幸福慈祥并略帶期盼的眼神。他還有一項織草鞋的技能,我小時候穿過不多的幾雙草鞋,大部分是他給我織的,他還手把手教我織過一雙,他自己平時也是穿自己織的草鞋,但他還有一雙橡膠質的草鞋,鞋底刻有一些自刻的特殊花紋,憑這些刻紋不管在哪他都能識別出自己的鞋來,我對這雙鞋也非常的熟悉,尤其是那些他自刻的紋路。
喜常好藏酒,當然也嗜酒如命,每次醉酒總會與人發生爭吵,甚至大打出手,有時還會操起那桿鳥銃嚇唬別人,很多時候只要他操起鳥銃對方就會讓步,爭吵也就停止,我想這桿鳥銃這種作用發揮得最多,但有一次真是個例外,鄰村一個同樣嗜酒的人稱麻子公公(因其先前出痘時在臉上留下滿臉坑坑洼洼的小洞,故被人稱為麻子)的人被邀請到他家喝酒,對酒當歌喝了整整一下午,據說末了因麻子公公不小心灑了幾滴酒激怒了喜常公公,兩個醉鬼從桌邊打出堂屋,并一直糾纏不清地打到了兩里開外,最后以麻子公公被打進水溝而結束,此事被當成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娛樂了鄉親們很久。盡管每次喝酒最后都會以這種不歡而散的形式結束,但他家里總不缺陪他喝酒并最后挨打的角色,也許是那個時代里有頓酒喝本就不易,來者喝酒之前就已做好挨揍的準備的,但人總是不滿足的,本是以挨揍換酒喝,但喝完酒后又不想挨揍,所以只能選擇對打,只是無奈要么打不贏喜常,要么打不贏他的鳥銃,最后不知這些喝了一頓無需花錢的酒但又因挨揍而顏面盡失的人后悔不,但一般隔一段時間,犯酒癮的人總會忘記挨打時的痛苦,并準備用挨打來再換一次酒喝,據說當時我們村一個什么村干部就是經常用這種方式去喜常家討酒喝,不知喜常是明著想用一頓酒去換一個人肉沙包解解單身生活的苦悶,還是壓根兒就沒怎么考慮后果,只是喝著喝著就公式般的進入了這個程序,這個村干部本就沒少去喜常家喝酒,當然也就沒少挨揍,據說喜常人生的最后一次表演是跟這個村干部完成的,兩人在一個知了嗚叫的午后隔著小桌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通,喜常心想你這酒喝不少了,也該受我幾拳幾掌了,但這回這個村干部借他人的酒壯自己的膽,認為自己雖然喝了你幾頓不收錢的酒,卻也是每頓都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眼看這頓酒已喝到點了,卻不愿意再當人肉沙包了,于是借著酒勁開始了反抗,在這次打斗中,喜常沒占到什么便宜,反而受了一肚子的委屈,畢竟對手是個村領導,在氣勢上高人一截,說來也奇了怪,這次喜常競沒讓他的鳥銃發揮威力,不過這次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喜常再沒揭開過酒壇子了,整個人也沉默了許多,像是在思考某種重大問題,有時我走近他也不再日迷起眼睛笑了,只是應付式的交談幾句便將我支開了。
這樣大概過去了三個月左右,我很少去找他,他也沒來找過我,村里人不太適應喜常不喝酒不吵鬧的日子,都開始議論起關于他的事了,是不是開始戒酒了?他為什么戒酒呢?甚至一些婦人們私下議論是不是喜常想找媳婦了?平日里很少受人關注的喜常在那段時間里成了人們私底下熱議的話題,我也有點奇怪,喜常的變化太過突然,瞅了個機會調皮地問了他這些村里人關心的話題,他再次迷起眼睛笑笑,用他那寬厚的手掌撫摸著我的頭說,小孩子懂什么,并告訴我以后要好好讀書,同時他向我要了一本連環畫圖書《周處除三害》,小時候,我有很多的連環畫圖書,每一本他都瞇起眼認真看過,這次向我獨要了這一本,別的我也沒感覺到什么太大的不同,只是他的眼神突然間有點陌生,語調也有些蒼涼。
人們的這種議論也只持續了幾個月,正當大家即將淡忘喜常喝不喝這件事時,入冬后的一個午后,突然間有人說喜常又在請人喝酒了,據說這次請的是他的父親、弟弟和妹妹,這倒令我非常震驚,他居然在我們村里還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而且還相距不遠,至于他的父親我是知道的,我還知道他有一個母親,但他們母子形相陌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這是他繼母。這次與家人喝酒后喜常就從人們的視野里消失了,剛開始人們也沒太在意,但幾個月后還是不見喜常的身影,人們便開始嘀咕了,喜常去哪了?圍繞著這個問題各種流言也開始了,甚至人們開始猜測最后那次家宴上喜常有什么異常的表現,說過什么異常的話語,抑或跟家人說過什么秘密……反正人們腦海里能想到的問題都有不同版本的流言,最終被他宴請的人不得不出來澄清,具體澄清了什么不太記得,但好像澄而不清,流言依舊,喜常在時總會不定期地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淡資,而他離去的方式也留給人們無限遐想,這種遐想所引起的話題雖然持久了些,但畢竟人還是不見了,因而隨著他消失時間的久遠,人們也就真正的淡忘了此事,淡忘了此人,生活中依舊充滿了期待,充滿了與自己無關卻又津津樂道的談資,好像村里從來沒有過這個人。
喜常的離去沒能改變知了年復一年的嗚叫,這叫聲依舊那么單調無聊,也許自從知了學會嗚叫以來就是這么個調吧,但人與知了不同,人類社會是不斷變革前行的,自從安徽鳳陽農民自創式改革被推廣至全國農村,一夜之間農民從之前的饑餓亢奮態進入飽肚無聊態,孩子們放學后在給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農活后也會找一些或有趣或無聊的事情去填補某些時間的空白。有一年暑假,好像是喜常消失后的第三年,三年足以讓一個喜常式的人物從人們的記憶里徹底消失,因為喜常的存在或消失絲毫不影響村里人的生活,人們也絲毫不會因為沒了喜常就缺少茶余飯后的談資,村里人的談資極易從一個不在場的任何人身上找到,中國農村的習俗是發生在別人家身上的任何事都可以成為笑料和談資,而且可以讓本就單純的事件變得血肉模糊般的復雜,所以某一個人的離去改變不了村里這種“哪個人前不說人,誰人背后無人說”的常態,只是人們對于金錢的渴望好像比之前更加強烈了些,但這不是因為喜常的離去,而是因為在改革開放這么多年后,即使邊遠山區農民的思想也開始解凍了,知道社會主義的草終究不能當飯吃,資本主義的寶興許還能派上用途,但大體上農民除了照常日未出而作,日已落而不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句對農民勞作狀態的描述與我所見到的農民勞作狀態是完全不同的)之外,村里有少數年輕人因厭倦了學校也同樣厭倦了農村而逃離學校直奔大城市掏金去了,但不管人們是外出掏金還是滿載而歸故里,也從來不會有人再提及喜常這個人以及與喜常有關的任何事了,但于我似乎是個例外,我偶爾也還會想起他,那個暑假突然想起他之前曾帶我去鵝泊洞玩過而突發奇想,想約幾個玩伴去洞中探險,正好堂姐夫也有獵奇之心,就帶上堂弟,還有一對鄰居兄弟,加上鄰家嬸嬸的外甥一行六人帶著手電備著蠟燭舉著火把風風火火循洞而入,走一路看一路,我就理所當然的擔當著向導講解員的角色,看見可供想像形狀的鐘乳石就會駐足而立,煞有介事的說說像什么是什么,也會杜撰出一些自己所能想到的像那只石鵝似的相關傳說來忽悠大伙,遇上岔道也能道出向左向右分別通往何處,能走多遠,哪處水路可淌水扶壁通行,哪處水路水太深不可涉險,其中有幾處狹窄斜坡處,我就一一囑咐腳踩何處手攀何物,人托人手拉手徐徐而行,在到達某處之前提前告知前方路況及有什么看點抑或更有什么奇特之處,等到了該處果不其然。每處講解我都胸有成竹,每處指點都準確無誤,大家都對我深信不疑,不知當時這么做是為了顯示我之前真的窮及此洞還是顯示我更加大膽,其實這些都是喜常公公曾經告訴我的,只不過此時成了滿足我某種心理的資本而已,我內心非常清楚,之前隨喜常公公游洞時也是非常恐懼的,只是覺得有他在身邊保護也就沒什么可怕了,我們就這樣或走或爬,或淌或滑,偶爾也能見到水中魚兒穿梭的影子,但沒有人能逮到哪怕是一條魚,據說村里有兩個捕魚高手曾在洞里逮到過幾尾魚,但任何人看了都不知道該叫什么魚,只是烹了味道倒是極佳的,當時心想若是喜常公公能逮上幾條我就還真知道這魚的味道了,一路說笑,特別開心,當然誰也不知道我之所以能當向導全是因為之前喜常公公帶我游歷過此洞,我們誰也沒有提及喜常,因為誰也無法把這個帶有美麗傳說的鵝泊洞與一個常與人爭吵甚至大打出手的喜常聯系在一起,更在于在這本就陰森恐怖的深洞中,如有人突然間提及某個已故之人肯定是件極端恐怖的事情,何況喜常的消失在當時村里本就是一個離奇且略帶恐怖的故事,這種情節只能在恐怖電影里出現的。
歷盡千難萬險,在火把即將燃盡之際,我們終于到達了洞的末端,再次見到這汪不知來處卻清澈見底倚壁而蓄的水前,駐足于這潔凈的沙灘上,涼意穿透足底,直逼骨髓,大家嬉著、鬧著、興奮著,因為都知道真的很少有人來到過此處,顯然大家都已盡興,嬉鬧中我突然想起似乎整個行程都是按喜常帶我游玩時的路徑,甚至在某處某點逗留時間的長短都與喜常帶我游玩時的一樣,此時腦海中突然浮現出喜常與我駐足于此的畫面,心中頓生“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之嘆。大家都以為可以打道回俯了,我卻告訴大家還有一個小景點應該去瞧瞧,于是大伙又在我的指點下在返程途中攀巖而至那個神奇的小洞前,由于洞口太小太低,需俯下身才能看到里面的情形,不知是誰第一個俯下身用手電往里照,瞧了一會兒,回頭說里面有個菩薩,大伙都特好奇,一齊俯身用幾個手電筒往里一照,確實有一個端坐于小洞正中、雙手合十、周身長滿白毛的菩薩,有人說是個金菩薩,心中竊喜,正當大家議論誰先爬進去時,我看到了那雙刻有特殊紋路的橡膠草鞋,心中頓悟,隨口而出:“喜常!”瞬間大亂,大伙回頭就跑,全不顧巖濕腳滑,爭先恐后逃命似的,只有我因游洞的整個過程心中都若有若無地念著喜常,似乎此次游洞就是對喜常的一次懷念,因而全無懼意,告訴大家不必害怕,但此時我的指揮已顯然失靈,叫的叫、喊的喊、哭的哭,慌亂之中,即將燃盡的火把掉了,只見幾只手電筒的光束在洞中亂晃,鄰居兄弟中弟弟大喊“哥哥等我!”哥哥回叫“這個時候了,各保各!”先前的興奮與快樂全被這突如其來恐懼所掩蓋,有的鞋子跑掉了,有的衣服刮破了,有的腳扭傷了,有的頭碰破皮了,但這些都已顧不上了,心中唯一的念頭是為保命而須盡快逃離這個恐怖的巖洞,我怕大家慌亂之中出錯,大喊:“不必緊張,有我在后面”,但不管我說什么,大家都聽不見了,這次美好的游歷就這樣在恐怖與慌亂中結束,逃到洞外,吐的吐、暈的暈、慌的慌,一個個臉色煞白,真像是從鬼門關逃回來的,其實當時我還真想多瞧一眼喜常公公。
喜常坐化于鵝泊洞的消息瞬間傳遍全村,那些隨我游洞發現喜常的幾個我的同齡人被嚇得夜里都不敢睡了,全村的小孩也都害怕起來了,有的家長甚至請來道士為小孩驅鬼收魂(據說人受到驚嚇后,魂魄就會逃離肉身,整個人最后因魂魄的遠離而死亡,收魂就是將逃離肉身的魂魄重新附體),特別是那洞中逃跑時受傷的孩子心理陰影持續了老久,聽說鄰家嬸嬸的外甥因受到驚嚇回家后還病得不輕,我也奇怪,村里死人是常有的事,為什么喜常之死會給村里人帶來如此的恐懼。
喜常歸宿的大白天下,讓村民們終于有更多探究喜常在那個入冬不久的午后宴請親人原由的理由了,也讓我終于找到喜常那次與我一起駐足那沙灘時給我那種與往日不同印象原因的方向了,也似乎明白喜常在發現那處小洞天地時盤腿坐于正中口念阿彌陀佛的緣由了,還明白在他沉默的那段時間向我獨要那本《周處除三害》的連環畫圖書的用意了,這本連環畫圖書記載一個出自《晉書》的故事,說有一個叫周處的惡棍,有一次問他的老鄉,咱們家鄉連年豐收為何還愁眉苦臉,老鄉就告訴他,說咱們家鄉有三害:山中老虎,水里蛟龍,人間周處,這三害不除,天下不安寧,周處聽后,非常慚愧自己居然也是鄉親眼中一害,后來周處上山射殺了老虎,入水斬殺了蛟龍,自己也改惡從善成為一個忠勇可嘉的勇士。喜常也深知自己多年來給鄉親們帶來了不少傷害,他是在用他的方式向這個周處學習吧,后來看《水滸》看到花和尚魯智深隨宋江歸化朝廷后在南征前皈依佛門的片段時我就會心中暗問,喜常的結局是不是也是一種人生悟道的結果呢?他生前最后幾個月的沉默應該是在悟什么,也應該是悟到了什么,只不過俗人悟的過程不需要什么儀式而已。
據大家合理推算,喜常是那次宴請之后當晚就入洞而逝了,后來有個高人說喜常是占洞悟道成仙了,于是村里人也找了很多證據來證明了這一說法的合理眭,其中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喜常三年逝而肉身不倒,這種說法也許是村里人對一個逝者的尊重與對其生前所為的包容吧,村里人雖樂于制造和傳播流言,但也是非常質樸善良而寬容的,喜常生前是全村人的話題,死后占有全村人的福地并依舊成為全村人口口相傳的神話,雖說村里人都愿意相信喜常是占洞成仙了,但這帶有美麗傳說并很有開發價值的巖洞卻因此很少有人再次光顧了,現在村里有個養鴨專業戶將鴨子趕進洞里過夜,鵝泊洞成了真正的鴨泊洞,每天早晨成百上千只鴨子從洞口或飛或游或跳著傾瀉而出,這景觀也足以慰籍喜常孤獨而略顯凄涼的身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