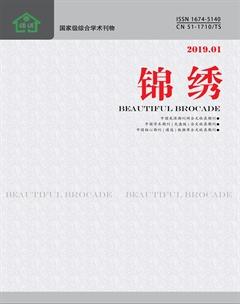《現代性與大屠殺》讀書報告
李天元
1.楔子
或許是巧合,一個鮑曼在所有人都不曾相信現代社會會產生大屠殺的時候,幫助第三帝國實現了這個規劃;而另一個鮑曼(也就是齊格蒙·鮑曼)則在人們漸漸遺忘大屠殺的時候,把它又重新擺到了世人面前。后者重提此事的目的不在于緬懷族人悲痛的過去或警示世人要小心極個別的“惡魔”的再生,而是告訴我們大屠殺究竟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光輝源泉——現代性,是多么的親密無間,如影隨形。
作者在這本書中步步推進,由當前及過去不久社會學家們的研究中對于整個現代性潛在的危機的冷落與忽視;到猶太人當年的經歷之中所體現出來的大屠殺與現代文明某些特性的聯系;再到米格拉姆的實驗是如何證明那些“殘酷、野蠻的行為”仍舊潛藏在現代文明的各個角落,并且它們的陰影在我們經歷過那些“殘酷的事實”之后,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日漸龐大;在本書的最后,審視了道德在社會學理論視野之中的地位并由此提出對當下的社會學理論進行根本性修正的主張。
2.不是瘋狂的宣泄,而是秩序井然的浩大工程
“大屠殺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現象,脫離現代性的文化傾向和技術成就的背景就無法理解。”因而,我們要注意到大屠殺之所以能夠達到如此駭人的規模與令人驚嘆的速度,與科學技術的靈活運用以及理性的思考是密不可分的。盡管,許多人會將“水晶之夜”作為反猶主義的突出體現——被官方慫恿的一群暴徒在一夜之內殺害了一百多個猶太人,然而鮑曼告訴我們,假如每天都是“水晶之夜”,那么要達到最終統計的600萬猶太人遇害的實際結果,至少也要200年。“憤怒與狂暴作為群體滅絕的工具是極其原始和低效的。它們通常在工作完成之前就已經消失。因此無法把宏大的計劃建立于其上。”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將大屠殺最終實現的不是窮兇極惡的暴徒或是充滿反社會思想的心理變態,而是那些具有高度理性思維的,恪盡職守的現代人。經過我們已然在之前論述過的種種之后,擺在這些“現代人”面前的不是一個艱難的道德選擇而是一個技術難題,現代性在教給這些學生現代的科學技術與分工體系的時候,也在冥冥之中用技術責任代替了他們的道德責任。屠殺的行為對于這些人固然可怕,但這與那些人參與這些工作甚至積極的為之添磚加瓦并不矛盾,他們要負責的是他們的工作,而由于他們的工作只是整個“工程”的一環,因而他們的工作并沒有決定計劃的成果,也不會影響計劃的目標,他們的工作只會影響他們手頭的報表,他們看護的閥門,他們指揮的火車……他們的道德是對自己的工作負責,把工作做得迅速而完美就是最為高尚的道德。
可是,這些人之中總會有人看到那些被殺的猶太人,比如那些要清理毒氣室的工作人員或是負責管理焚尸爐的人們,他們又該如何說服自己來接受這一切而不肯站出來對這一切說不,或者至少遠離這些工作呢?這些人在現代性的庇護下比前現代的平民更少見到暴力的實施,但無疑這些人面對了更多的死亡與更加猙獰的面孔,這樣的反差想來應該使這些人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比起過去的人民更容易產生至少些許的憤慨吧?但結果不是如此的,而原因也恰恰在于暴力在日常生活當中的缺席。暴力的缺席不是由于所謂現代性帶來的文明,因為現代性若真與前現代的激情勢不兩立,那么,它只會比前現代的激情帶有更多的折磨與暴力,只不過暴力“不再是激情的工具;它們已經成為政治理f生的工具。”暴力的缺席在于權力的轉移,由于現代明確的分工體制,暴力、政治……不論是何種爭取利益的手段都被集中到了“專業人士”的手里,因為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才能以更加具有效率的方式運轉,我們才能夠“進步的更快”。權力與義務在人們的心中總是相一致的,因而,盡管這些猶太人的死有我的功勞,但我不該為此負責,要負責的是“上面的人”是那些決策者,我只是忠于了我的工作。
3.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假如從一開始德國就宣布要處死所有的猶太人,不僅難以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支持,所有的猶太人也定然會團結一心,奮起反抗。然而正如前面所述,德國人只是想“清理”猶太人,大屠殺,不過是隨著形勢的步步變化,漸漸的演變出來的最有效率并且最為節約成本的“最終解決”的方案。
也正是這種“可能性”讓猶太人前赴后繼地“積極”地參與到這場毀滅自身的計劃當中來,也許是巧合,也許是蓄謀,總之德國人在進行大屠殺的過程之中巧妙地運用了這樣的充滿現代性的“猶太人”——德國人不會一次性的殺掉所有的猶太人,他們會讓猶太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族人,和猶太人首領玩類似于“火車司機的困境”的“是你自己去殺掉一個人還是我來殺掉十個人”的游戲……
鮑曼在此也就向我們展現了現代性在大屠殺當中不僅僅是施害者的發動機,也是受害者的推進器。假如,這些猶太人沒有被現代性教導的如此訓練有素,以至于可以理眭的思考每一種可能性,并精細地計算這些選擇以尋找生存的機會。或許,就不會有如此之多的受害者,或者,至少會讓納粹付出幾倍乃至幾十倍的成本。
猶太人正是在這種由納粹給予的一次又一次“做出理性抉擇”的“機會”里把自己送向了滅亡。
4.反思
大屠殺以及整個二戰之中的那些慘絕人寰的種種行為是人類道德史上的巨大災難,在技術責任被日漸明確的當下,我們還能否在心中劃一道清晰的界線,讓邪惡在通過技術這樣一個光彩奪目的名號突破約束之前戛然而止。
我們不可能指望從互動當中獲得“獨特的道德”的少數人來拯救世界,這樣的想法早就被無數次地證明無效了;也無法希求現代性能夠在短期之內停下他的腳步,因為顯然,我們不可能因噎廢食,況且,我們也難以找到一個可以替代現代性的事物,來賦予我們如此強大的發展動力。但我們依舊可以通過文化的多元性來嘗試抵抗悲劇的再度發生,只要這個世界還沒有統一的規劃,也就不會有“最終方案”。可是,正如鮑曼所擔心的“后現代主義的,以消費者為導向的和以市場為中心的大多數西方社會的環境似乎都建立在經濟特別優先這種脆弱的基礎之上,這種經濟的優越性目前是以對世界資源份額的極大占有為擔保的,但這顯然不會一直持續下去……早已確立并久經考驗的種族主義觀點也許會再一次派上用場。”
或許隨著全球化的進程,這樣的觀點也將不再僅僅針對西方社會。畢竟,每一個受過現代性的完整教育,并且具有高度理性的道德正常的人,都有足夠的能力與心理準備,在某個“特殊的時期”參與到一場類似的社會工程之中,新的計劃將可以在這個科學技術更加發達的當下,被實施得更加徹底與迅速,以至于可能在那之后不會再有下一個鮑曼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