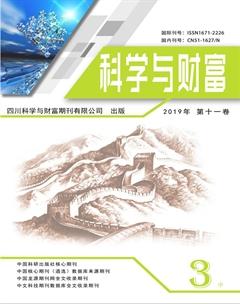淺談《紅樓夢》的影響
王海燕
摘要:百年來中國文學(xué)經(jīng)驗的一大部分——閱讀與潛在的、不能完成的寫作,是與《紅樓夢》有關(guān)。對于我們的生活世界的體會與言說。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中國人所借助的是一部《紅樓夢》。盡管正典化過程中,《紅樓夢》被力圖納入正確的詮釋框架,盡管對它的閱讀被強力引導(dǎo)和訓(xùn)示,但是,《紅樓夢》所展的那個恒常俗世,面對20世紀的強大歷史,它不是話語合法性的,不能被說出,不能被寫出,但它依然在運行,《紅樓夢》作為百年屹立不搖的經(jīng)典,它始終活著,不是因為它按照評家的意圖被批閱,而是因為它始終參與著我們的生活。
關(guān)鍵詞:紅樓夢;歷史;影響
《紅樓夢》是小說,是虛構(gòu),它既不是曹家史,也不是大清的宮廷史和社會史。
此義余國藩先生更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即曾困惑:“這里確有一個奇異的矛盾現(xiàn)象:即《紅樓夢》在普通讀者心目中誠然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小說,然在百余年紅學(xué)研究的主流里卻從來沒有取得小說的地位。”而俞伯平先生在1987年也曾批評索隱派和自傳學(xué)說的學(xué)者將《紅樓夢》視為歷史文獻。
但是沒有用,當(dāng)下,余英時先生說的“普通讀者”的態(tài)度恐怕也已大成問題,近年來因網(wǎng)絡(luò)和《百家講壇》的推動,大批業(yè)余史家鉤沉導(dǎo)隙,于空虛中言之鑿鑿,《紅樓夢》即在“普通讀者”眼里也未必再是“不折不扣”的小說。
情況是:我們有一部偉大的小說,但是我們一定要把它讀成流言蜚語。
當(dāng)然,這樣一種閱讀習(xí)慣和這樣詮釋方式也并非錯到哪里,杜魯門。卡波蒂曾說:小說即飛短流長。在中國傳統(tǒng)中,如果我們同意小說的起源如《漢書。文藝》所說即是“稗官”,那么,稗官的功能就是搜集和上報“小道消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之口說了什么,王又何以得知?大概正是通過稗官,在漢儒的詮釋下,稗官和樂府被理想化為“以觀民風(fēng)”,差不多就是與民同樂了,但揆諸基本的政治野性,則稗官之職恐怕首先在于對事實和虛構(gòu)的收集、審核與控制,即以“稗”字而論,稗是稗草,混同于五谷,似真非真,是無用的和破壞性的。稗官要識別稗草,則他知道何為真,何為事實,這是顯而易見的政治權(quán)力。
小說的起源于事實與虛構(gòu)、真與假的辯證與爭奪,稗官只是這場爭奪的一方,另一方是那些無名的作者和聽眾、讀者。
稗官所搜集者何事?不外乎兩類:一為志怪、志異,一為宮闈流言,所謂野史、秘史。這兩方面的趣味深刻地源于人性,至今在網(wǎng)絡(luò)上也是昭昭在目。
很少有人注意到,野史的敘事的說服力更立在懷疑論和相對主義基礎(chǔ)上:野史地講述者關(guān)切的與其說是確認的事實,不如說是被事實所遮蔽的區(qū)域,他們認為那個區(qū)域肯定是在的,正史告訴我們多少東西,它就同時遺忘和隱藏了更多的東西,正是這個意義上,無可求證的想象,杜撰或虛構(gòu)獲得了一種合法性:當(dāng)我們相信事實中隱藏著假時,我們也就相信虛構(gòu)中隱藏著真。《紅樓夢》最終無法逃脫這個命運:面對這部偉大的虛構(gòu)作品,我們以永遠不厭煩的熱情,組織起一代又一代的偵緝隊,我們必須找出它隱藏的“事”,我們確信存在曹雪芹密碼,他在恢宏的野史中一定說出了什么,他寫這本書的目的盡在于此。
所有的話都說出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這是《紅樓夢》的總綱。我們至今也未必懂了,中國自有小說以來,沒有任何寫作者如曹雪芹這般深曉真與假、有與無之間吊詭繚繞的關(guān)系,他無與倫比的原創(chuàng)性成就首先在此。
即使是熟悉20世紀后現(xiàn)代小說的讀者,也會驚嘆于《紅樓夢》龐大復(fù)雜的后設(shè)性結(jié)構(gòu)——我沮喪地發(fā)現(xiàn)余國藩先生對此已有詳盡的分析和闡述。
但有一個問題依然值得拈出來討論,那就是,這個叫曹雪芹的人對身為一部小說的“作者”的看法。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元明以后,曹雪芹此前這幾部偉大的說部中,我們唯一可以明確辨認的作者只有曹雪芹——當(dāng)然這并非毫無疑問,至少胡適就曾推測曹雪芹并非《紅樓夢》唯一作者,他是依據(jù)某個原始稿本批閱十載,增刪五次。但是我和后世的絕大部分讀者一樣,認為曹雪芹是唯一的作者,理由主要是:那個寫《紅樓夢》的人,他的作者意識是如此之強,以至他不可能聽任自己徹底消隱。
第一回:“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這在中國小說中誠為石破天驚,因為眼目所及,此前似乎沒有作者在書中如此自我暴露,而將明確的作者聲音和作者意識帶進文本內(nèi)部,這遲至于上世紀80年代,才在中國小說中作為一種令人不安的創(chuàng)新出現(xiàn)。
《紅樓夢》之所以不被當(dāng)作“不折不扣”的小說,曹雪芹自己要負很大的責(zé)任,他像一個虛榮的、深通誘惑與營銷之道的當(dāng)代作家,處心積慮地將讀者的注意力引自文本之外的自身,小說的第一段,幾乎是一份閱讀上的“自傳契約”。
這件事此前的中國小說作者從未做過。但曹雪芹的驚人復(fù)雜就在于,他馬上就讓這份契約變得暖昧不清,效力無法估量——我們看到那塊石頭,刻于石上之書,傳抄者空空道人,最后,曹雪芹的名字表現(xiàn)出:他卻是個勤勉的編輯者。
那么,一開始說話的“作者”是誰呢?從邏輯上說,石上之書應(yīng)是石頭自撰,那么,我們可以把“作者”等于石頭嗎?我們就算知道這是曹雪芹的托馬斯。品欽和博爾赫斯式的復(fù)雜詭計,但有鑒于此,我們又該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那份剛剛達成的契約,相信曹雪芹將作品與他其實生活相互印證的愿望?
曹雪芹可能是中國小說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作者,同時也是隱藏得最深的作者,他前所未有地伸張作者的權(quán)利,但卻同時前所未有地揭示了作者虛構(gòu)的權(quán)利。他比任何一個人更直接地現(xiàn)身,但又比任何一個作者更傾向于自我消解。
關(guān)于《紅樓夢》,最怵目驚心的事倒不在于它長期以來未被當(dāng)做“不折不扣的小說”。而在于,自上世紀初新文化運動以后,此書成為中國文學(xué)之正典,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幾乎是讀書之人無人不讀,文人們更是以談?wù)摗都t樓夢》為雅事。但是《紅樓夢》陳述現(xiàn)代以來中國文學(xué)的影響卻驚人地小——幾近于無。
也就是說,我們讀《紅樓夢》,談《紅樓夢》,但是,我們竟沒想來像《紅樓夢》那樣寫小說。現(xiàn)代以來,幾乎沒有什么重要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和作可以明確地見出《紅樓夢》的影響,“家族史”嗎?那可主要不是從《紅樓夢》中來的,我能想起來的依稀還有《三家巷》中對《紅樓》調(diào)子的引用,但其實是不成功的。
唯一例外的是張愛玲。而張愛玲為什么會成了例外,下面就會談到。
這是一個閱讀史和影響史上的奇觀。它告訴我們,最持久的閱讀熱情和最深入的闡釋興趣竟都不足以化為影響。中國的小說家們很少在寫作盛年談?wù)摗都t樓夢》,《紅樓夢》對他們來說無法構(gòu)成影響的焦慮,倒是成了暮年的消遣。
一部《紅樓夢》冤纏孽結(jié),第二十九回,寶玉黛玉慪氣,賈母抱怨道:“不是冤家不聚頭”,這本也是老太太說家常口吻,卻說得寶黛二人心中一動,“好似參禪的一般”。這是冤孽,從情節(jié)上說,卻是當(dāng)日赤瑕宮里神瑛侍者澆灌了降珠仙草,降珠轉(zhuǎn)世,以淚還他。
這是個神話,但是每一個中國讀者卻是默會于心。對于神人仙草,我們是姑妄聽之,但對于其中所含的人生精神,我們是深信不疑的:水與淚的交換關(guān)系中,隱含著際遇與應(yīng)許,那就是一個“情”字。
關(guān)于《紅樓夢》的“情”,論說汗牛充棟,不能再加一言,此處要說的,倒是另一種“情”,秦可卿房中那副對聯(lián):“世事洞明皆學(xué)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兩句話,中國讀者同樣深領(lǐng)會,洞明與練達皆是“格物”,格物之目的,在致知,也在立志、顯名。
《紅樓夢》一書,于此間是巧舌如簧,極具功力。自胭脂齋起,評家讀者對《紅樓夢》中的這份人情都懷有特殊的興趣——時至今日,中國的大眾紅學(xué)中除了探秘索隱,便是老太婆論長短,于每個人,每件事于人情世理上細細考究。《紅樓夢》百余年來一個隱蔽的文化功能就是,它是中國人的人情教科書,舉凡婚姻家庭、私事公務(wù),直至軍國大政,都在《紅樓夢》里對了景兒,借得一招半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