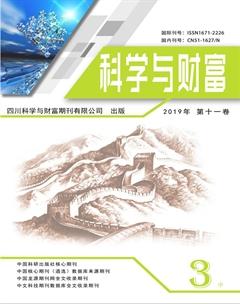明朝中后期中國衰落的制度因素
王鷺
摘要: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在1—15世紀一直領先于世界,然而近代科學革命卻沒有發生在這個文明古國,英國學者李約瑟率先發出了這一千古之問,引得國內外學者廣泛關注,故稱為“李約瑟之謎”。本文以近代科學革命發生時中國所處的明朝中后期為背景,分析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制度,闡明中國明朝中后期衰落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李約瑟之謎,試圖對當今中國科技發展有所啟示。
關鍵詞:李約瑟之謎;科技創新;制度因素
一、引言
世界近代史開端為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但西方世界近代史的開端始于約15世紀。15世紀,又被稱為地球大開發時代,西方大航海時代開始,新航路的發現使得歐洲迅速發展起來并奠定了超過亞洲繁榮的基礎。16世紀,哥白尼提出日心說,出版《天體運行論》,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與《生物進化論》等,初步形成了與中世紀神學與經驗哲學完全不同的新興科學體系,拉開了西方科學革命的序幕,歐洲逐漸領先于世界,而此時的中國處于明朝中后期。也就是說,在明朝中后期,相較于西方世界,中國已經開始衰落。
然而,我們要知道,除了希臘人的偉大思想和制度,從公元1世紀到5世紀,沒有經歷過“黑暗時代”的中國人總體上遙遙領先于歐洲。不僅在技術進程方面,而且在社會的結構與變遷方面,西方都受到了源自中國和中亞的發現和發明的影響。那么為何中國在15世紀以前科技領先于歐洲,而15世紀之后卻落后于歐洲呢?這正是經典的“李約瑟之謎”所提出的問題。盡管“李約瑟之謎”首先是一個技術問題,然而理解這個謎題卻不能就技術而論技術,那樣會犯循環論證的錯誤,對問題的論證不具有說服力。技術落后是表象,其內部必然蘊藏著制度的機理,本文通過分析明朝的一系列制度,試圖從制度因素的角度出發分析明朝中后期衰落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李約瑟之謎”,進而得出對當代中國發展的啟示。
二、何為李約瑟之謎
15世紀以前,中國的科技水平領先于歐洲。除了我國的四大發明傳到歐洲世界外,還有其他上百種發明,比如鑄鐵法、弓形拱橋、運河水閘等 ,都對社會更不安定的歐洲產生了影響,有時甚至是極為重要的影響。然而西方文藝復興晚期發生科學革命,歐洲迅速領先。于是,與古代和中世紀科學相對的現代科學在西方世界發展起來。而中國,遲遲徘徊于科學革命的大門外不肯邁進,不知不覺間落后于世界潮流,逐漸衰落下來。
為何會出現這一局面?國內外無數仁人志士困惑不已,開始探索其中的奧秘,英國學者李約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1976年,李約瑟經過多年的時間與大量的精力進行研究后,在其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這個問題,其主題是:“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之謎。
此外,李約瑟所指出的中國落后于西方的時間正處于中國古代明朝中后期,要想回答這一謎題,必然免不了對同時期的中西方的發展趨向方面做出關聯和比照。本文則集中于分析西方科技革命發生時中國明朝中后期的一系列制度進行論證。
三、明朝中后期衰落的制度因素
科學技術的發展離不開創新,而中華民族并不缺乏創新精神,15世紀以前的中國領先于世界就是最好的例證。之后之所以衰落,是因為一些因素抑制了創新精神的發展。對中國來說,最大的制約因素莫過于漫長的封建社會以及與之相伴的一系列封建制度。歷朝歷代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秩序,頒布并實行一整套政策及制度,這些政策、制度在當時或確實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其創立的目的本不是為了發展科學技術,一旦將其推行發展到極致,必將走向社會進步、文明發展的對立面。
(一)政治制度
明王朝作為中國帝制后期的一個時代,其既帶有自秦漢以來所有朝代都不同程度表現出來的一些共同特征,又有自己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政治特點。其中,君主專制主義強化,內閣的出現和科舉制度的發揚光大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科學技術的發展,成為明朝中后期衰落的原因。
1. 君主專制制度
明朝政治的主要特點莫過于君主專制皇權和中央集權的空前強化,如沿襲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廢除,后來雖形成內閣制度,但六部仍需直接向皇帝負責。除了有開國之君朱元璋個人的印記,其后繼者們也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不斷加以調整,形成了一套高度發展和成熟的君主集權的政治體制。在這種所有權力都集中到中央的權力格局下,政治生活毫無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可言。
然而,科學與民主是相伴相生的,民主會為科學提供適宜的土壤。進行科學研究也著實需要一種寬松、自由的社會環境,縱觀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不難發現,每每在科學技術上取得很大成就的時代,大都是明君主政,政治清明,相對民主的時代。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進步,這一景象的形成就是得益于當時社會沒有文化專制,允許各家學派發出不同的聲音。但明朝中葉以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程度越來越嚴重,民主無法發展,同樣也就沒有科學發展的相對寬松的環境。
2.內閣制度
所謂內閣,只是文淵閣的別稱,那里曾經是閣臣“入直之所”。直到明朝中后期嘉靖年間才加以整修擴建,正式成為“閣臣辦事之所”。但是仍然不是“政事堂”,因為那里禁絕朝臣出入,只是地址設在宮廷之內,也簡稱為內閣。內閣選用閣臣的標準是“有文學修養之士”,所以內閣閣臣幾乎全是翰林文學之士,特別是在明中葉后,“非由翰、詹起家,無由入閣。”
內閣擁有票擬權,即對皇帝需要批閱的奏章給出一個初步的處理意見,皇帝可以選擇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否定或全盤否定。這種獨特的最高權力運行機制,具有明顯的內在缺陷,即內閣閣臣選用文學之士的標準本就降低了國家發展科學技術的可能,加之這些閣臣只有票擬權而沒有任何事權,他們勇于任事,就被認為是擅權,終以賈禍;他們無所作為又會被認為失職,因此許多閣臣進退維谷,能否發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閣臣的個人的素質、才干和對于內閣性質的認識,儒生出身的閣臣很難將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上議事日程。
3.科舉制度
中國古代就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入仕的觀念深入人心,而進入仕途的方式自然是通過科舉考試。科舉制度并非自明朝起,卻在明朝發揚光大。明朝科舉實行四級考試制,即院試、鄉試、會試和殿試,考試內容為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決于八股文的優劣。所以,一般讀書人往往從剛到識字的年齡就接觸的是四書五經這樣的“圣賢書”,往后也多半會把畢生精力用在儒家經典的記憶、朗讀、背誦和掌握文字的表達能力上,他們唯一的事情就是“讀死書,死讀書”,無暇顧及和科舉無關的其他知識。因此,與科舉考試無關的書籍完全不受人重視,也幾乎沒有人翻看。明代宋應星的重要科學技術著作《天工開物》很快就在國內失傳,直到解放后才發現一部明代初刻本。
八股取士的考試方式從內容到形式嚴重束縛應考者,許多知識分子不注重學問,讀書只是出于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的渴望,更無從提及對自然科學研究的任何興趣,讀書人不能成長為真正的人才,而只能成為統治者忠實的奴仆。此外,更為致命的是,科舉制度下的讀書人,循規蹈矩,缺乏創新精神,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桎梏。這種人才選拔的考核方式對自然科學的發展所起的阻礙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二)經濟制度
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互為表里,是一對既相輔相成又相互依賴的關系。明朝科學技術未發展起來,與當時的重農抑商政策的實行和產權保護制度的缺失有很大關系。
1.重農抑商政策
在兩千余年封建歷史中,“重農抑商”政策是古代統治者慣行的基本治國之策,“重農抑商”、“農本商末”政策深深制約和影響中國歷史。明朝總體看,抑商傾向依然是很明顯的。明初,商人從事商業活動,不僅有多重限制,就連對商人的穿著,都有特殊的規定,衣著光鮮便會受到懲罰。明中期以后,商人及其從事的商業活動開始為人們所認識,商人的地位得到一定的改善,商業巨大的贏利吸引了不少權貴經商,但其直接效應是一般的工商業發展艱難,甚至許多商人直接遭到掠奪。
現代科學之所以沒有在中國發生,與中國商人階層難以形成氣候有很大關系。這是因為商人需要精確度量,否則就很難做生意。他們必須關心他們所經手貨物的實際性質,必須知道商品的重量、用途、長度、大小以及需要何種容器來裝。我們知道,在科學工作中,手腦并用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中國古代除了商人階層,好像還沒有人能都做到將動手與動腦完全結合起來,因此,商業的發展與精密科學有一定的關系,明朝中后期中國衰落,也與重農抑商政策脫不了干系。
2.產權保護制度缺失
產權顧名思義是指財產的所有權。15世紀以前,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領先于世界,當時的發明主要源自工匠和農夫的經驗,大多都是自發的、零星的、非營利性的,且這種發明創造作為一種知識產權在推廣的過程中就存在所有權歸屬的問題。但當時對于產權缺乏制度性的保護,有的只是民間一些自發的保護方法,比如我們最為熟悉的:一些手工藝人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不受損,常常將自己的“獨門絕技”、“秘方”對外保密,需要手藝傳承時,也堅持“傳子不傳女”、“傳媳不傳女”,除此之外,并沒有一種制度性的規范來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統治階級對保護屬于私權領域的知識產權權利也毫無興趣,對民間的這種自發的保護方式持默許態度。產權保護制度的缺失,使得商人對其財產安全的預期是不穩定,這種不穩定直接導致普通民眾毅然選擇走上仕途而非進行發明創造,從而使民間缺乏發明創造的動力,再加上社會上普遍的“輕利重義”的風氣和國家家族至上的傳統,即便中國人創造了四大發明,也未借機出現專利制度,去保護發明創造的成果,激勵民眾進行更多的發現,反而將發明創造視為“奇技淫巧”而為士大夫階層所蔑視,可見科學技術發展衰落的原因。
(三)社會文化制度
自古以來,儒家思想因為最符合統治者的需求而成為中國的傳統主流思想,然而儒家文化所蘊含的某些理論觀念不僅對自然科學發展起不到促進作用,反而會阻礙科學革命的發展。主要表現在:
第一,儒家的“圣人”觀念,是科學發展最大的阻礙。在這一觀念中,圣人代表著不可超越、永恒不變的真理,預設了圣人的萬能和常人的無能。這種觀念遠離知識創新,常人都只是在圣人的指導下做事情,沒有人敢超越圣人,久而久之,這種情況就變成了常人遵從圣人的指導是理所應當,沒有人試圖去進行創新、挑戰經典、超越圣人。于是乎,知識進步舉步維艱,即便有,也只是在不違背經典的前提下,進行的小修小補,較大的知識創新是不可能出現的。南朝著名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經過精心的觀測和計算,創制了《大明歷》,首先引進歲差,并改革閏法,而頑固派戴法興竟蠻橫叫嚷“古人制章,萬世不易”、“不可革”,竭力阻撓新歷法的推行,足以見得自然科學發展之艱辛。
此外,與“圣人”至上觀點相對應的,儒家推崇“愚民”。孔夫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強調,人民不可過分聰慧,否則將難以管理。高明的統治者,不是凡事都要讓人民明明白白,而是要想方設法讓人民變得愚蠢起來,如果人民都變成了沒有智慧和欲望的傻子,那天下就穩定了。歷代統治者為維護統治秩序,必實行愚民政策,這種政策基本是反民主、反智主義、反精英主義的,維護統治秩序的同時也阻止民眾獲得真知。
第二,“均”文化注重財富分配而非財富增值。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味地追求平均主義,且這種平均主義不是以物質發展的進步作為前提,忽視了物質的進步性,單純地追求平衡。這種思想否認發展否認進步,必然導致生產技術落后,進而阻礙經濟的發展。
第三,儒家的“天命觀”嚴重阻礙自然科學的研究。人類需要先認識自然,再根據自然規律改造自然,這就需要人類有一個正確的自然觀,明白自然界獨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然而儒家卻拚命宣揚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自然觀,認為天有意志,“天人合一”,天命不可違抗,一切自然現象都不過是上天用來影響人間、賞善罰惡的手段。孔子鼓吹“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要人們“畏天命”,這種思想緊緊束縛著人們,用神學來歪曲科學,把科學引入歧途。
四、總結反思
結合16世紀西方發生科學革命時,中國明朝中后期的情形,我們似乎面對著一種有機的整體,一種連鎖的變化。政治上,君主專制高度集中,中央集權空前強化,缺乏科學發生的民主化的寬松的氛圍;宰相制度廢除,國家大事由內閣票擬,報司禮監批紅,六科簽發,科學技術不在議事日程之內;八股取士,文官治國,缺乏科技人才。經濟上,重農抑商傾向明顯,商人社會地位不高,沒有精神目標和安全感,產權保護制度缺失,科學技術被冠以“奇技淫巧”的稱號。文化上,維護統治秩序的儒家文化占主導地位,遵從“天命觀”,倡導“天人合一”,認為天有意志,教導人們“畏天命”,科學被神學扭曲;“不患寡而患不均”,注重生產分配而非財富增值,缺乏科學革命發生的動力;推崇“圣人”觀念,灌輸以圣人不可超越的思想,扼殺常人創新能力。由此,李約瑟之謎便有了答案。
當然,這里分析的所有制度不是否認他們存在的意義,而是說所有的制度在當時的社會存在下,一定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只是隨著社會的演進,生產方式的變化,他們不再適應社會的需要而成為阻礙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因素。
自1978年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是顯而易見的。經濟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改革開放將我們帶到了一個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機遇面前,然而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如何突破改革瓶頸,進一步深化改革?科技的發展是關鍵。借鑒明朝中后期中國衰落的原因,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契機,制度改革是重點。我們應當深入開展科研體制改革,制定科技發展的長遠目標,完善科技發展模式。把企業作為科學與技術創新的主體,繼續加強科技政策的完善,在制度方面給予保證,在稅收、擔保、貸款等方面對科技研發給予支持,調動企業進行科技創新的積極性,通過技術創新去擴大更廣闊的市場,提升自身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提高國家的國際競爭力;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激發改革的內生動力的同時,也要繼續堅持人民當家做主,營造適宜科技發展的民主和諧的環境;改革教育制度,既要注重基礎教育,又要緊抓高等教育,注重培養創新性人才,在培養本國人才的同時也要引進國外優秀人才,此外還應促進高校、科研機構及社會科研力量產學研相結合,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參考文獻:
[1]黃仁宇.萬歷十五年[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
[2]李約瑟.文明的滴定[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22-27.
[3]王其榘.明代內閣制度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9: 39-350
[4]高顯揚,周尊麗.淺談李約瑟之謎與中國科技創新[J]. 科技楓,2018(02):201-212.
[5]相利盈.政治學視角下李約瑟難題之解析[J].政法建設,2010(05):102-104.
[6]殷繼烈.李約瑟之謎探析——基于諾斯的制度及制度變遷理論的翻譯[D].上海:復旦大學,2009:10-19.
[7]趙新華.近十年來李約瑟之謎研究綜述[J].商,2016(02):100-111.
[8]張顯清,林金樹.明代政治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3: 16-19.
[9]趙軼峰.李約瑟難題與明清社會——讀《文明的滴定》[J].古代文明,2017,10(11):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