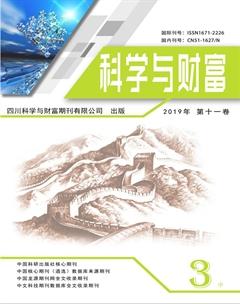“苦難”敘事中作家的自我慰藉情懷
摘要:作為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的文化大革命早已結束,但作為思維方式、政治態度、話語結構、權利傾向的“文化大革命”仍在人們心中延續了多年。“文革慣性”這一強大的支配性力量也在相當一段時間里繼續左右著人們的精神與思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對那段苦不堪言的歷史進行強烈的控訴與揭露,這是因為身處歷史事件中的人們往往用足夠感性的視角對歷史進行追憶與回顧。反思小說在很大程度上繼續發展了傷痕小說的模式,主要集中體現在所謂“反思”的意味真正映射在文本中時所呈現出來的“反”而未“思”。尋根文學所找尋到的“根”的無緒與混亂也表明了人們對“失根”的擔憂與無力,作家們力圖從民族文化之“根”中發出聲音,尋找慰藉,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苦苦探索的“根”本身就是虛妄。大概是文革結束后相當一段時期內,社會并沒有回歸到常態式的環境,歷經苦難的人們沒有過分的喊叫、控訴,反而用一種壓制自己的方式完成一種“憶苦思甜式”的苦難大表演,以此來尋求自我慰藉,填補心中的缺口。
關鍵詞:苦難敘事;自我慰藉;精神意蘊
新時期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上一個極具特色且較為重要的部分,它在相當程度上預示著中國文學向理性、人文等向度的復歸與突破。在此之前的十年文革文學由于某些政治因素導致了文藝近十年的斷層,歷經這一浩劫的作家們不管是在身體上還是心理上都深埋了數道疤痕。這是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劇,也是一代知識分子家庭的災難。歷史的巨輪呼嘯而過,毫不留情地在人們心口上碾出了巨大的缺口,但時間的洪流卻硬拖著人繼續往前走,飽經苦難的一代人還沒來得及舔舐傷口,政治氛圍也沒有給一代苦難者足夠的交代,歷史潮流依舊滾滾向前。這一巨大缺口留下的空白只能由作家們自己找尋慰藉。
文革敘事中相當一部分作品或隱或顯的顯露出了或強或弱的苦難意識,歷經苦難的人們在多年以后回過頭來看,對那段瘋狂歲月仍舊感到難以言說,但更多的卻是發自內心的“自豪”與“欣慰”,甚至有一種為了祖國更好的發展、為了自己修煉的更完善,“我”還要繼續承受更大的苦難的“苦難”精神。我們首先應該明朗,苦難并不絕對意味著財富,艱澀的苦難本身毫無價值可言,或許我們在經歷之后會說一句“多虧了當時受的那些苦”,而這句話本身也是有個大前提的。我們不應該否認,苦難會帶人成長,會幫助你蛻變,但我們更不該一味地把苦難的意義“絕對化”、“神圣化”。倘若在一個永恒的無法消除且歷久彌新的苦難格局中高呼苦難會帶給你精神的富足這顯然是巨大的謊言與欺騙。然而,身處苦難中的人們必須“預支”苦難的意義并且用這種事后的意義不斷鞭策自己,否則任何一個人都無法熬完那杯濃稠的苦。而這一個為自己歷經的苦難找尋慰藉與“名分”的過程,正像是一個人在沙漠中踽踽前行,探索出口。
作為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的文化大革命早已結束,但作為思維方式、政治態度、話語結構、權利傾向的“文化大革命”仍在人們心中延續了多年。“文革慣性”這一強大的支配性力量也在相當一段時間里繼續左右著人們的精神與思想。這進一步導致了歷史給予的平反與自身精神話語的枷鎖形成了巨大的張力與悖論。為了順應政治意識形態的要求,同時也為了疏導歷經苦難的人們內心情感宣泄的欲望,文學率先承負起了這一使命,這同時正從某一側面展示了文學自古以來所特有的承擔“意識形態之重”的責任。但也應該意識到,承擔這一重任的文學者們也是一代歷經苦難的知識分子的一員,甚或是最痛苦的一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一系列關于文革話題的作家作品清一色表現出了在深淵中獨自摸索的狀態。我們當然可以理解作家們在歷經苦難之后對苦難的抱怨、牢騷、不滿與自慰,但同時也該意識到,作為主流話語的政治意識形態在此時相當一段時期內仍左右著作家的價值判斷。這恰好導致了我們在相關作品中所感受到的作家力圖構建個體獨立的精神話語方式卻只做到了淺層次的苦難展示,這一悖論凸顯了作家面對強烈的政治意思形態話語的不自知與無力。
一、一種錯誤的出現并不意味著對這種錯誤的矯正就是絕對合理的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對那段苦不堪言的歷史進行強烈的控訴與揭露,這是因為身處歷史事件中的人們往往用足夠感性的視角對歷史進行追憶與回顧。而當時間不斷向前推移,歷史與人們之間拉開了足夠距離時,人們往往可以用足夠理性的視角去審視那段歷史,從而獲得了更接近歷史本相的相對客觀冷靜的結論。
以盧新華《傷痕》為開端,新時期文學正式開始了對文化大革命或批判或沉思、或揭露或追問的審視與評斷。《傷痕》著重揭示了革命用“命名”的方式進行革命這一瘋狂行徑。“命名”定罪這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一方面,知識分子被迫被政治意識形態話語打上了種種罪惡之名,且意識形態話語之“重”壓得知識分子難以脫身;另一方面,由于知識分子本能的對強大權利話語的崇拜和敬畏,使得知識分子自覺不自覺的會有一種對強大話語的依附感。這兩種思想激烈碰撞,處于絕對權威地位的強大話語本身就將個體碾壓在被“命名”的話語之下,毫無懸念。在這部作品里,我們可以清晰感受到身處歷史洪流中的個人生命的纖微與軟弱,也可以看到為了革命為了自身而放棄親情的人性冷漠。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命名”定罪,就像一系列虛空無義的標簽在找尋各自所謂的對應的商品。在1957年夏季的中國,55萬個“右派”的標簽在尋找55萬個“合適”的“商品”。革命使人瘋狂,讓人喪失理智。將《傷痕》中曉華的革命歷程抽離出來進行縱向比對,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曾有不少為了革命而放棄親情與家庭的例子。如巴金的《家》中,覺慧為了革命為了自由而離開使他感到罪惡的家庭;楊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靜亦是離開封建腐朽的家庭勇敢地奔向革命。但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傷痕》中曉華離開家投身革命與后兩者有著鮮明的不同于后兩者的更為不堪與缺乏正義性的理由,毫不遮掩地說,她是為了在革命中求得自保,即使偶有懷念母親的念頭,她也從未動過質疑這一切的念頭。這正是狂亂的時代所造就的迷狂的精神。類似的情形在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的作品《一九八四》中也有所涉及。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刻畫了一個令人感到壓抑的恐怖的未來社會,一切隱私、自我、感情、追求通通被銷毀,人性被扼殺、自由被壓制、思想被泯滅,象征著“絕對權威”的“老大哥”無時無刻不在監視你,每個人都信仰“絕對正義”,孩子們為了心中的信仰可以毫不留情舉報自己的母親,每個人都陷入了單調可怕的怪圈中卻毫不自知。作者反復強調那個社會信奉的“絕對真理”:“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①奧威爾筆下描述的扭曲世界不正是《傷痕》中所反映出來的嗎?但奧威爾幻想出來的反烏托邦式的小說情境卻在那些年的中國真真切切的存在過。《傷痕》的作者在對剛剛過去的苦難進行鞭撻與痛惜時,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點在于作品結尾處作者借主人公曉華之口所表達出來的對“絕對正確”的意識形態的信仰:“媽媽,親愛的媽媽,你放心吧,女兒永遠也不會忘記,您和我身上的傷痕是誰戳下的。我一定不忘黨的恩情,緊跟毛主席,為黨的事業貢獻自己畢生的力量!”②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一方面受到強烈的情緒力量的驅使,借個人的立場進行時代控訴,揭示文化大革命給人們造成的傷痕,對文革強制性話語顯示了初步的懷疑;但另一方面作者又自覺不自覺的服從于當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要求,在雙重約束下作出找尋突破口的艱難努力。這表明一代傷痕作家仍處在精神蟄伏時期,多少還是依賴于通過尋找強大意識形態支撐來為無法填補的傷口尋找依靠。這種對之前的強大意識形態話語的懷疑與對新的意識形態話語的依賴,不僅在作品中,更在作家心靈上產生了強有力的悖論與反差。這一悖論與反差不僅在傷痕文學期間存在,在文革后相當一段時期內依舊存在,這主要是因為文學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從屬于政治意識形態,文學自身的“精神自立”依舊沒有得以完全樹立,并且對其社會功能的強調還是處于一種絕對權威的位置。一種錯誤的出現并不意味著對這種錯誤的矯正就是絕對合理與正確的,正是作家們對這一點的忽略與不自知,導致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影響了對文化大革命審視的真正合理性。
二、“反思”并非是文學自身出于對生活的真切關照而引發的理性的獨立的思考
歷經傷痕文學時期的不冷靜與不清醒之后,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作家們從社會、政治、人性與啟蒙的角度“重現”文革的荒謬面目,直擊事件本質上的荒唐,較之前的文學更為客觀、深邃。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伴隨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結論的盛行與推崇,社會上普遍出現了一種理智、冷靜的氛圍。且這段時期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工作卓有成效,作家們由此獲得了一種更開闊、更深沉的視野。帶著這種視野再去審視心口上的巨大缺口,作品中展示出了作家們對文革的再思考與再評價,反思文學應運而生。
歷經十余年強勢的政治壓制之后,在七十年代末,作家們在新的社會氛圍、心路歷程中開始尋找另一種新的可能性,突破了最原始的盲目,轉向了對“人”的關注與思考,找到了人道主義這一“茂盛”的田野,終于開始體會到“人性”與“文化”這一系列深層內涵。從前期劉心武的《班主任》到后來王蒙的《活動變人形》,我們可以感受到作家們突破僵化權利話語的努力,但作家們用以將“政治化”的“人”從權力話語中解脫出來的所使用的工具是另一種并不十分成熟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所以傷痕——反思作家所作的努力最終只不過是將人們從一種權利話語轉移到了另一種權利話語中,這也許是一代作家們所始料不及的,但這就是他們自身對文學、政治以及人道主義并不十分通透的認知所直接導致的。
前期劉心武的作品《班主任》,作者用一個全新的視角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的罪惡行徑以及給青少年所造成的心理陰影,以較為堅定的勇氣直面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尤其是在結尾處作者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讓我們想起在五四時期魯迅的《狂人日記》中狂人喊出的那聲“救救孩子”。我們可以感到欣喜,欣喜作者終于有了直面苦難的勇氣,有了批判性地正視苦難給一代青年人造成的無法挽救的不良后果的自覺。但我們不難發現,作者此時發出的感嘆遠沒有達到五四啟蒙者自身那種清醒的自覺與反思的水準。作者在極力挖掘苦難意識并對受難者給予人文關懷的同時,恰恰忽略了“人”的存在,忽視了“人性”的深層底蘊,生硬刻板的指導標準讓難得的溫情也變得冷漠與無力。乍一看,《班主任》中“救救孩子”的呼聲似是啟蒙文學精神在數年蟄伏后在此時期的蘇醒,似是新時期文學與五四文學在人道主義維度上的隔空呼應。作者想從這一層面來挖掘僵硬刻板的意識形態給一代年輕人的心靈所帶來的無法抹去的傷痕。依照文本給定的標準,謝慧敏和宋寶琦與張老師心中的“好學生”的標準相距甚遠,且在謝慧敏身上表現出的對話語的“絕對信仰”似乎更深程度上受到“綱常倫理”的荼毒。盡管作者已經有了質疑的初步自覺,但我們不難看到,班主任的所謂“標準”僅僅是從外部得來的“非此即彼”的表面要求。由此來反觀《狂人日記》中狂人的那聲“救救孩子”,狂人的呼喊是源自于對自身既是“被吃者”同時也可能是“吃人者”的高度警惕與強烈反省,顯示了狂人從內心深處懺悔的自覺以及對時代發出的響徹云霄的詰難。而班主任張老師(實際也就代表了作者)的“拯救意識”僅僅停留在控訴時代對受害者的侵害,缺少了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反問,忽略了自己同時也可能是個施害者的自覺,這就直接導致了這一文本在此層面上的淺薄與空缺。
反思小說在很大程度上繼續發展了傷痕小說的模式,主要集中體現在所謂“反思”的意味真正映射在文本中時所呈現出來的“反”而未“思”。作者在作品中表達的對文化大革命的追憶與思考的確帶有反思意味,但我們也該意識到,這種反思意味并不是出于文學自身那種既熱切關照現實且又努力超越現實的深層次自覺,而是強大的意識形態話語完完整整地橫向嫁接到了作家的思想中,生硬且勉強。這歸根結底還是在于文學對意識形態的深層次依賴。在一系列被號稱為“傷痕”、“反思”名目的小說中,我們從中看到的依然是僵硬的階級對立、非此即彼、好人與壞人的絕對區分、對愛情視若毒瘤的斗爭精神,而這些斗爭意識正是“文革慣性”強有力的表現。所以,但凡文學束縛在這樣強勢的話語的范圍內,就不會有真正突破和超越既定模式所帶來的欣喜,作家們仍然小心翼翼地在“安全”的范圍內寄托意志以此來尋找自我慰藉。像王蒙的小說《活動變人形》中,作者通過對倪吾誠這一病態人物的刻畫表達了對文革、社會、人性等的批判與抨擊,并以生動簡潔的筆墨概括了那個時代的中國的風云變幻與人情冷暖,反“這就是洋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愛情。而中國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勾心斗角,哪里就有人勇于捉奸,為捉奸可以幾夜不睡。”③“全世界還有多少這樣的等待了、渴望了千年萬年億載的凍僵了的、擠扁了的、壓硬了的、失去了語言、情感、溫度和運動的靈魂!”④透過作者這一系列的話語,我們能感受到作者對當時社會生活的揭露,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一代人,靈魂亦無處安放,更何談找尋撫慰傷口的縫隙。從深層次的文化角度去反思病態社會產生的根源,這類小說重新激發了人們對“人”的重新關注與思考,以及對“人”背后的“話語”展開人道主義的追問,這一點是應當值得肯定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類傷痕——反思文本中普遍存在的打著人道主義的旗幟高呼人性的綠洲卻“不約而同”地對“人性”進行淺薄的理解與詮釋這一問題是相當令人詬病的。作家想在人道主義這一田野上找尋苦難的意義,進一步找尋自我慰藉,除了特定的具體的客觀理性因素之外,這一想法是無可厚非且合乎時代的。但問題在于作家們對于具有強大統攝意味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的“自覺”服從也是造成對“人”的真正內蘊理解上存在較大偏差的緣故,同時這也導致了文本自身的內在矛盾及深層內涵的匱乏。
三、尋根文學中“根”本身的虛妄以及作者寄托的幻滅
隨著歷史漸次推進到80年代,距離十年浩劫也已經過去了十余年。十年來人們有過強烈的控訴,也有過冷靜的反思,到80年代普遍開始了對歷史不斷的追問,開始探究那段令人瘋狂的歲月到底是如何發生的。作家們甚或可以說整個文藝界,開始慢慢從既定的意識形態話語框架中走出來,開始突破原始的堅硬的界限。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文壇上興起了一股尋根文學的熱潮,作家們對傳統文化心理、深層文化意蘊開始了挖掘。1985年韓少功先生的《文學的“根”》中,就表明“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則葉難茂。”⑤ ?尋根文學從深究整體的文化淵源著手,以此來挖掘更深層次的精神困境的根源,并試圖尋找到可使精神或靈魂依托的處所。對于尋根文學的出現,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落實,中國的經濟迅猛崛起,經濟基礎的發展亦帶動著上層建筑的活躍;加之西方文化在工業文明的涌動下如猛獸般呼嘯而來,日漸寬松與相對自由的社會氛圍和國際交往,使國內迅速盛行了像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一類的作品,此時國內多數身處中流砥柱地位的作家們還在盡力彌補內心巨大的缺口、找尋苦難的意義。面對這強烈的魔幻現實主義沖擊,相當一部分作家開始了對自身民族更為大膽地挖掘。且自古以來多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所造就的穩定的文化心理意蘊結構和特有的確證民族身份的認同感,使得對民族之“根”的追尋意味著對文革敘事開拓了更為合理的路徑。出現在尋根作家筆下的文革敘事,呈現出某種有意識地躲避或者是淡化大革命背景的精神向度,這顯然與前期傷痕——反思文學直面文革大相徑庭的。但深究底層根源,我們發現這種刻意的淡化并不意味著作家們真正放棄了對文革的追憶與審視,恰恰相反,正是這種“由顯到隱”的置換顯示出作家們退居到了一個更冷靜更寬廣的視角上來審視文革,追憶心中的疑問,這正是一代尋根作家們所找到自我慰藉方式——用敘事上的策略將自己置放在一個制高點。當個人話語與強大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進行正面對話時,個人話語會自覺不自覺的處于弱勢,有意無意間被強大的權利話語吞噬;而當個人話語從本質層面上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實行一種有意識的擱置,人為的將權利話語導置于潛在層面,個人話語就會獲得相對的自由,個體話語由此在這種敘事策略中得以真正凸顯。
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壇,主要有這樣三類作家:一是飽經苦難的“歸來者”作家群,像王蒙等;二是知青作家群,主要代表有王安憶、阿城;三是更為年輕的新一代作家,比如后起之秀余華、馬烽等。我們知道,前兩類作家都是文化大革命的親身體驗者,但有意思的是,這兩類作家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關于文革的敘事與追憶表現出來了巨大的悖逆與差異。例如張賢亮的《綠化樹》等作品中借主人公章永璘所體現的那種“以苦為樂”的價值觀就將一代歸來者作家群內心深處那種不確定、不自信表達的淋漓盡致。歸來者作家們總是在靈魂深處質疑自己,歷經劫難他們更多的是反思自己的缺憾,對“苦難記憶”本身有著放不下的情懷,甚至不斷勸勉自己從苦難中汲取生活的勇氣。而與歸來者這種沉重的苦難意識相反,知青作家群所感受到的苦難更顯縹緲,他們不是像歸來者那樣去質疑為何將自己從所屬團體拋離出來,他們的感觸更多的是出于對政治信仰的絕對信奉以及由此引發的對自我認知的質疑。他們本來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義的,是為了人類社會前進而作出的勇猛的選擇的,而當后來一代“紅衛兵”被冠以“知識青年”的身份下放到邊遠地區時,毫不夸張的說,他們的世界觀幾近崩塌,他們由此嘗到了完全不同于歸來者作家所受到的苦難類型的另一種更大程度上的心靈磨難。知青的苦難是源自于價值理想與冰冷現實強烈對立且毫不相容的精神崩塌,由此他們開始自然而然地寄理想于天地自然、文化歷史。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這兩類作家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苦難意識,但都體現了一種奉獻精神,即就算世界冰冷也要溫暖世界的大無畏精神。這正是從苦難中生發出了對苦難的愛,用痛苦的火焰燃燒他經歷過的時代,這也是一種從苦難中找尋慰藉的方式。尋根家們或者寄托在原始社會形態里(如莫言、張煒),或者在已經逝去的青春記憶里找尋答案(如史鐵生),作家們力圖通過尋找文化之“根”來尋找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深層根源,并借此真正洞察自身體驗過的文化本相。在莫言的小說《紅高粱》中,作者力圖滲透到原始維度中探求人們的精神底蘊,在作品中著力彰顯熱烈、勇敢的原始面貌,在這種敘事方式的關照下,人物大多由內而外地浸潤著原始生命強力。
我們可以理解一代作家們想通過“尋根”這種方式來深入挖掘民族精神向度的這種方式,但細細體味尋根文學中所呈現出來的文化之“根”,我們不難發現作家們提供的“根”只是毫不現實的幻象,或者是一堆毫無生命力的殘羹冷炙,這正從另一側面展示了有著清醒尋根意識的作家們在面對內心深處接近真理的呼喊時的手足無措與精神缺憾。不僅僅是作家們所尋的“根”的“質量”差,還有一方面是每個作家將自身的精神向度投向完全不同的領地,這可能與自身生命歷程有關,但從另一方面分析,“根”的無緒與混亂也表明了人們對“失根”的擔憂與無力,作家們力圖從民族文化之“根”中發出聲音,尋找慰藉,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苦苦探索的“根”本身就是虛妄。
四、一代苦難者寄托在作品中的“憶苦思甜式”表演
社會歷史普遍可劃分為兩種典型的形態。一種是常態式的,身處其中的人們自由呼吸,正如契訶夫在《第六病室》中提到的健康心理狀態:“遇到痛苦,我就喊叫,流眼淚;遇到卑鄙,我就憤慨;看到骯臟,我就憎惡。依我看來,只有這才叫做生活。”⑥常態式的社會生活會給人以足夠的安全感去喊叫、去發泄、去訴說。另一種社會狀態是非常態的、變形的,正如文革十年,人們身處在扭曲的被操控的時代里,被政治意識形態的高壓時刻壓制著,文學也因此變成了政治斗爭的武器。久而久之,人們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政治化”,政治化的話語方式、政治化的風俗習慣甚至是政治化的文學藝術,屈身在堅硬的政治外殼里,人們無法找到恰當的無傷大雅的方式為自己開拓出口。大概是文革結束后相當一段時期內,社會并沒有回歸到常態式的環境,歷經苦難的人們沒有過分的喊叫、控訴,反而用一種壓制自己的方式完成一種“憶苦思甜式”的苦難大表演,以此來尋求自我慰藉,填補心中的缺口。每個人都手捧著大同小異的劇本,心懷著大同小異的感情,懷揣著大同小異的情懷,完成了一場絢爛卻用盡顯空洞的煙花表演。身處歷史舞臺上的每個人,潛意識中都會給自己皺縮的心靈化化妝,在時代的矚目下,這同樣是知識分子不自知的悲劇。
對于那段荒唐的歷史,我們訝異于群眾集體無意識所帶來的巨大殺傷力,也驚詫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內心競有如此強烈的“家國意識”,即無論在黑暗中承受多少苦難,無論苦難給心口劃下的傷痕多深多痛,個人總會無意識地先想到國家的苦難、民族的苦難甚或是任何人的苦難,承擔苦難的自覺促使作家們飛快成長,一代知識分子總是不約而同地用這種方式尋找慰藉,找到出口。
回望歷史,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你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外表可能儒雅大方且舉止得體,內在飽讀詩書且滿腹經綸,但身處在特定的時代特定是群體中,一個個孤立的看起來有涵養的個體卻有可能變成最瘋狂的野蠻人,在歷史洪流的慫恿下,他在群體中表現成一個最原始的動物,身不由己且狂熱兇殘且不自知。置身于群體中不自覺地表現出來的集體無意識并不會使當事人覺察到正發生的一切本質上的殘忍暴力與野蠻荒唐,甚至表現出了對特定群體行為的熱情推動,興致盎然且真誠勇敢。狂亂時代里所造成的巨大的悲劇與這樣一種“群體理論”關系十分密切,身處其中卻未曾清醒。但當我們后來者以一種客觀冷靜的姿態來審視當時那段迷狂的歷史時,我們感受到的是令人震驚的殘酷與兇猛。“受難者”在事后不斷撫慰自己的傷口,以種種不理智卻也不勇敢的方式找尋慰藉,這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局限性充分展示了其特色,大擺的“人道”的盛宴卻獨獨缺席了“人”。
參考文獻:
[1]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黃云霞.苦難敘事的精神系譜--中國當代小說中的文革敘事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3]朱德發.中國現當代500題解[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
注釋:
①奧威爾.一九八四[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馬穎譯,2015.
②盧新華.傷痕[M].上海:文匯報,1978.
③王蒙.活動變人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④王蒙.活動變人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⑤韓少功.文學的‘根[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
⑥契訶夫.第六病室[M].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央金譯,2015.
作者簡介:劉江玲(1997-),女,漢族,山東淄博人,大四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