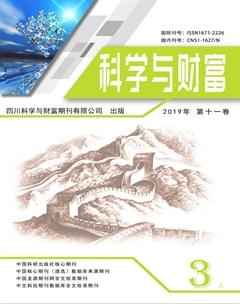當前貧困線研究與及我國貧困現狀分析
李婧
一、引言
貧困問題的研究一直是全世界的學者努力的方向。從整個國際形勢來看,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地區之間貧富差距逐漸增大,非洲等地的極端貧困現象引發了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關注。從國內形勢來看,從1978年改革開放,我國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的政策以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逐漸增大,甚至城鎮與鄉村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也逐漸增大,而這與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最終目標相違背。因此,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許多的國際組織與學者都致力于對減貧問題的研究,以期采取適當的政策,對全世界的減貧事業做出貢獻。
二、我國貧困現狀的分析
陳功,高菲菲(2013)對我國農村殘疾人貧困狀況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殘疾人因勞動能力缺乏、康復治療負擔重,貧困發生率高,是農村貧困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殘疾人相對于城市居民和健全人有雙重脆弱性,并基于經濟缺乏的角度,利用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25美元的固定貧困線,對殘疾人的貧困狀況進行研究,研究發現,農村殘疾人的貧困發生率遠高于農村居民,但兩者的差距在逐漸縮小,從絕對值來看,殘疾人的貧困發生率也在逐年下降,貧困深度指數也呈下降趨勢,并且農村貧困主要是暫時貧困,即一年到兩年貧困者。沈揚揚(2013)在中國農村經濟增長與差別擴大中的收入貧困研究中發現,我國貧困問題日益復雜: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現象并存、貧困人口普遍分布與地域集中分布現象并存、不同類別農戶貧困狀況之間差異化明顯等。在農村絕對貧困逐步得到緩解(但最貧困人口數量似有所上升)的同時,相對貧困狀況日趨惡化;貧困人口持續減少的“表象”,主要源于貧困線絕對值長期保持不變,或其增幅階段性放緩的特征。文章以全新視角審視經典問題,發現相對貧困現象是當今農村貧困領域更為重要的問題。李丹鳳,王亞芬(2017)提到,在消費領域,貧困地區基本的吃穿方面支出在總消費中的占比下降,貧困人口仍具規模,貧困分布呈現出地域性:2016年,我國農村依然有4335萬多貧困人口,而這些貧困人口,有一半以上都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區。陳忠文(2013)從山區與非山區的角度度量貧困人口的分布問題,發現農村貧困人口呈現出山區集聚現象,這中集聚現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表現在農村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分布在山區省份,另一方面表現在山區省份農村貧困人口占比遠遠超過非山區。高帥,畢潔穎(2016)研究認為農村人口從事農業活動的時間越長,持續多維貧困的可能性越高陷入多維貧困的可能性越低。東部、中部、西部發生持續性多維貧困的可能較高,而東部、西部陷入多維貧困的可能性較低。絕對收入、相對收入和社會地位越高,農村人口發生持續性多維貧困的可能性越低。女性、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村人口持續性多維貧困的可能性更高。相對收入較低的農村人口易于陷入多維貧困,然而相對收入對農村人口持續性多維貧困的作用不明顯。社會地位對農村人口持續性多維貧困產生消極作用,卻對陷入多維貧困的影響不顯著。
三、國內外對貧困線的分類
貧困線的設定是貧困問題研究的起點。貧困線是對貧困的度量,從貧困線的定義出發,國內外的學者進行了詳細的界定。首先,學者們把貧困分為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美國人口調查局在工作報告中詳細闡述了各種貧困線的定義與內涵。絕對貧困是從人體維持生存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出發,計算人們求生所需要的最低收入。通常只隨著基本消費品價格的變化而變化。而相對貧困線是從人類的社會性出發,Ravallion(2009)在文中提出,人是一種社會體,在社會關系中生存,因此,人“完全參與社會關系”、“處于社會中”,他們需要適應社會,但對于一些經濟資源顯著少于社會大多數群體經濟資源擁有量的人來說,即使他們不愁吃、不愁穿、足夠生存下來,他們也不能適應社會,因此這些人就屬于貧困人群。除此之外,還有主觀貧困線。主觀貧困線的提出者認為,絕對貧困線和相對貧困線只是針對個人或家庭的客觀物質收入、支出或者個體或者家庭之間的相對收入和支出來判定一個家庭是否貧困,而Van Praag(2005)就指出:“客觀貧困線有一種‘家長式作風的意味。政府或‘專家來決定何種消費水平對應于貧困,這種貧困線是‘客觀的。然而不明朗的是,有些由‘客觀貧困線所確定的貧困家庭不認為自己貧困,而有些被定義為非貧困的家庭卻感覺到貧困。”因此,主觀貧困線為在客觀物質需求的基礎上加上被調查者的主觀意愿,共同考慮這兩個因素計算。除此之外,世界銀行也發布了自己的貧困線,通常被稱為國際貧困線,用于國際間的比較及扶貧項目。國際貧困線的制定主要是根據最不發達國家居民的消費來確定的標準,1990年世界銀行采用了包括肯尼亞、尼泊爾等在內的8個國家來計算極端貧困線。2001年,代表性國家包括了中國、坦贊尼亞、印度等國家在內,收入貧困線劃定為這些國家貧困線的中位數。2008年,代表性國家從74個在1987年到2005年間有貧困線的國家中,選取了15個國家來計算貧困線。據此世界銀行在不同時期提出了不同的貧困標準,如每人每天1.00美元、1.25美元、1.50美元,2015年10月,世界銀行提出了每人每天1.90美元的貧困標準,這是按照2011年購買力平價的調整制定的。也有些學者認為,單獨的主觀貧困線與客觀貧困線都存在不足之處,嚴重影響測算結果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因此在貧困研究中引入了混合貧困線,James(1998)等建立的一種混合貧困線是以社會生活必需品消費支出中位數一定比例的倍數作為混合貧困線,David Madden(2012)以絕對貧困線和相對貧困線的加權幾何平均數作為貧困線。
參考文獻:
[1]陳功,高菲菲.我國農村殘疾人貧困狀況分析[J].殘疾人研究,2013(01):46-52.
[2]沈揚揚. 中國農村經濟增長與差別擴大中的收入貧困研究[D].南開大學,2013.
[3]李丹鳳,王亞芬.我國當前的貧困狀況及精準扶貧政策分析[J].科技促進發展,2017,13(11):940-945.
[4]陳忠文. 山區農村貧困機理及脫貧機制實證研究[D].華中農業大學,2013.
[5]高帥,畢潔穎.農村人口動態多維貧困:狀態持續與轉變[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26(02):76-83.
[6]Ravallion, M., S. Chen, and P. Sangraula. 2009. ―Dollar a Day Revisited.‖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3: 16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