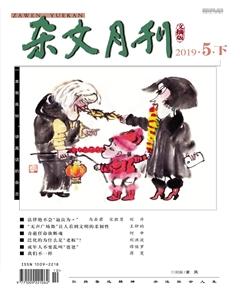沒有誰能夠“遠離自然”
戴榮里
常出去做客,每每宴畢,看到有,人打包就欣慰,看到剩下一桌子酒菜就心疼,這可能與我的童年時光是在農村度過的有關。有一次,與一桌環境保護學者、專家吃飯,遇到剩菜滿桌,當時真想發火,也想打包帶回家去,但最終還是礙于情面,沒好意思說出口。回想起我在廣州工作時,特別佩服那些大老板的“勇氣”,他們每次出去吃飯,都會把殘湯剩羹打包帶回去。從這個細節中可以看出來,這些老板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是因為他們知道-餐一果、一絲一縷來之不易。
生活中,許多人一說起不注重環境保護的那些事情,就侃侃而談、義憤填膺,而常常是事情落到自己身上,就不一定那么注意了。譬如我在某大學講課,看到一位女生用紙巾,一堂課下來,堆滿了整個桌子;在大街上行走,見到行人把喝空了的牛奶盒隨處亂扔;有學生的筆只用了一半就扔掉了,實在可惜。實際上,即便是一支鉛筆,也是許多資源配套制作出來的。這樣隨手一扔,就等于把資源白白浪費了。這些不經意的現象,每日大量發生在城市中,疊加起來,就能間接影響到自然界的平衡。
我向來對用紙巾或者是濕巾過多的人頗有微詞,但想想平時的自己,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譬如用打印紙,大多還不是只用一面?對生活、工作中的其他各類用品的使用,也根本談不上節約和環保,白白浪費了很多資源。一次,我到日本去參觀,當看到每一位公民都那么認真地奉行垃圾分類的做法時,感到非常汗顏。日本的環保是人人參與,而我們的環保則是渴求政府和別人做好,環保好像與個體無關,的確需要從內心深處進行反思。中國是個資源緊缺型國家,每個人點滴的浪費,疊加起來,都是驚人的數字。
在城市里生活的人,貌似遠離自然,其實卻和自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比如一個火車站的設計,往往和一位生活在城市里的設計師關系密切。如果一位設計師不顧及大環保概念,而是單憑自己獨特想象的建筑造型人手,進行高大上的設計,導致占地巨大,鋼結構用量大。這樣的設計不僅對建材直接利用量大,而且會直接占用大量土地資源,也就等于間接地占有其他資源,這些都已被歷史證明是對自然生態的當下平衡和持續性發展極為不利的。設計師看似遠離自然,但他的設計卻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自然的平衡。所以,沒有誰能夠真正地“遠離自然”,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愛護自然。
鄉村看似遠離城市,而城市卻“遙控”著鄉村。鄉村的振興、發展,大多靠城市里的決策者敲定。某市對環保工作一刀切,禁止采集砂石料,但這個城市建設需要大量砂石料,就形成了偷采、亂采之風。上級檢查組做出的這種一刀切停止的決定肯定是不完美的,要有疏堵平衡的思維,才能保證自然生態的平衡。城市里不乏設計者、政策制定者、決策者,這些人從宏觀到微觀,都在影響著自然界的一切。
一個遠離城市的湖泊,可能會因為城市管理者的決策失誤、監督失控而造成污染;一處風景名勝區,可能因為城市管理者的審批而造成別墅合法化。退-步而言,城市公民日常生活的微觀性并不代表與泥土無關、與環保無關,遠離自然的人愛護自然不僅可能,而且能大有作為,當反省、優化而后行!
田曉麗薦自《小康》201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