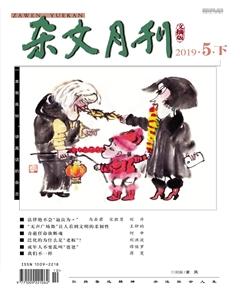文人宜散不宜聚
張宏宇
最近在讀孫犁先生的書,孫犁一生淡泊名利,執著創作,他特立獨行的性格,自我放逐的生存方式,我非常欣賞。他女兒在書中回憶,有一次市長來探望父親,對他噓寒問暖,父親卻站在屋子一角,顯得拘謹無奈。一位親.戚說:“不管什么場合,你爸爸都不愛摻和,更不愛巴結哪個當官的。
孫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我以為文人宜散不宜聚,一集中,一結為團體,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影響寫作。”孫犁晚年深居簡出,放棄、躲避的并不是他對生活的追求,躲避的或許是無謂的應酬和爭奪。
文人宜散不宜聚,“聚”顯然指的是許多人嗡嗡嚶嚶聚在一起,聚訟紛紜、徒耗時間毫無益處的聚會。文人聚在一起,談天說地,切磋文藝,或許不算什么壞事,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很多聚會卻變了質。近年來我也參加過一些大大小小文人的聚會,發現有一些聚會嘈雜不堪,沒有秩序,甚至所談所聊的話題,大多與文字無關。
仔細觀察才知,“聚”成了一種交際的手段,文人忙著簽名,忙著拉關系,忙著公關,這樣聚得多了,就會形成一個小圈子。拉關系是為了便于發表,而見人就推銷自己的書或者稿子,就是為了讓別人關注自己,使自己多一些虛名。有了一些作者的吹捧,有了阿諛奉承,個別編輯發稿更多看重人情,遮蔽了真正的好作品,以致大量人情稿涌入報刊。
如今的寫字更像一個名利場。很多作家總是喜歡打著“聚會”的旗號,時不時搞個筆會,舉辦個采風活動,甚至還打著各種學術交流的幌子,這種聚會更多是一種熱鬧,真正為了創作的能有多.少呢?寫字是需要耐得寂寞.的,各種各樣“聚”的應酬只會影響你的寫作。一旦喜歡上了這“聚”和熱鬧,或許很多人再也寫不出像樣的好作品了。每當文人聚會的時候,有人忙著推銷雜志、為自費出版的作者充當掮客,或者為收費會議拉客戶,我便感.覺,這種所謂的文人圈玷污了文學的神圣色彩。對于文人來說,如果公關大于寫作,關系勝于文字,這樣寫出來的文字還有多少分量可言呢?
在如今的文人圈內,能夠獨立思考、潛心治學、孤獨寫作的文人,似乎越來越少了。能夠待在家里,不受外界環境的誘惑、干擾,一般的社交應酬都不參加,能夠拋掉浮躁的東西的人,越來越少了;喜歡熱鬧,喜歡浮躁,喜歡虛名的,卻越來越多了。創作乃寂寞之道,開筆會交流,搞聚會活動,絕不是真正的作家所樂為、所應為的。
文人宜散不宜聚。散,才可以少一些干擾,少一些干涉。想靜下心來,搞些創作的,還是各自散去吧,不要總是聚在一起,時間長了,就是生事,就會為了一些虛榮而爭執。那些聚在一起的文人,大抵不是為了創作,更多是為了一些自我滿足和利益罷了。文人相聚,多多少少會產生一些是非,人們常說“文人無行”“文人相輕”,文人們聚在一起議論圈子里的恩怨是非,為利而爭,為名而拼,實在是太累了。還是離遠些的好,以免去那些口舌之爭、無謂之辯。
文人宜散不宜聚。真正理解“散”,做到“散”,把寫作當成是寂寞事不是熱鬧事,實屬不易,恪守更不易。文學是一條寂寞之路,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創作出好作品。面對紛繁充滿誘惑力的現實,要善于找到自己的清靜,在屬于自己的時間里,鍥而不舍地追求自已喜好的東西,努力實現自己的理想,并在創作的追求中和實現的過程中得到美的享受。
已故作家路遙曾經對青年作者說過這樣一句話:“不要再做那些無謂的掙扎,安下心來好好寫,發上幾個中篇之后誰也奈何不了你。”試想想,一個整天忙于趕場相聚的文人,一個無時無刻不在挖空心思想著如何進行炒作的作者,一個整天為了一些虛名而費盡心思的人,他能夠寫出有分量的真文字嗎?文人宜散不宜聚,少聚多.思,靜心多寫,淡泊求真,方是為文之道吧。
郭旺啟薦自《桂林日報》2019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