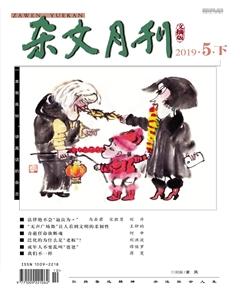讀《齊白石日記》
韓羽
瀏覽《齊白石日記》,如顧愷之吃甘蔗,從梢頭起,吃著吃著-漸入佳境了。
“但見洋,人來去,各持以鞭坐車上。清國人(中國人)車馬及買賣小商讓他車路稍慢,洋人以鞭亂施之。官員車馬見洋人來,早則快讓,庶不受打。大清門側立清國人幾數人,手持馬棒,余問之,雨濤知為保護洋人者,馬棒亦打清國人也。”
在畫家眼里,什么都是“畫面”。這段日記,就是三個畫面。這三個畫面就出現在當年的北京街頭。第一個畫面:洋人持鞭亂打讓路稍慢的清國人。第二個畫面:清國官員機靈麻利躲讓得快,庶不受打。第三個畫面:保護洋人的清國人,手持馬棒亦打清國人也。
不必《清史稿》,只這三個畫面,茍延殘喘的大清帝國是個什么樣兒就一目了然了。
“余嘗謂人日:‘余可識三百字,以二百字作詩,有一百字可識而不可解。”又詩云:“近來惟有詩堪笑,倒繃孩兒作老娘。”
這似是對自己詩作的調侃。《湘綺樓日記》載:“齊璜拜門,以文詩為贄,文尚成章,詩則似薛蟠體。”說這話的是王湘綺,亦即王運,湖南宿儒,大學問家。大學問家說的話能有錯么。又據傳王老先生曾戲撰袁世凱總統府對聯云:“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什么東西。”敢捋虎須,為大清遺老出了一口惡氣。其.實現在細想,也可作另種解讀,比如說,他老先生是否覺察出了袁世凱已厭了總統想當皇帝的花花腸子,給他來個隔靴搔癢?他既能把“總統”將白說黑,難道就不能拿“薛蟠”尋人開心么。
看來白石老人似不全是調侃,倒是卓識。且看他的另-詩:“百家諸子人嘗讀,那見人人有別才,最喜你儂同此趣,能詩不在讀書來。”他的“以二百字作詩”不正是“能詩不在讀書來”么。
“青門經歲不常開,小院無人長綠苔。螻蟻不知欺寂寞,也拖花瓣過墻來。”如無-.雙趣眼,怎得覷見無人小院的綠苔中竟有如此忙碌景象?
“青天任意發春風,吹白人頭頃刻工。瓜土桑陰俱似舊,無人喚我作兒童。”借范成大詩之舊典,化為我用,翻作人生百年一瞬之慨,不亦推陳出新乎?
“小院無塵,人跡靜,一叢花傍碧泉井。雞兒追逐卻因何,只有斜陽蝴蝶影。”個中情趣,尤勝楊萬里“閑看兒童捉柳花”也。
“逢人恥聽說荊關,宗派夸能卻汗顏。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慣桂林山。”心中如無大丘壑,敢出如是盤空硬語乎?
觀詩可知其畫;觀畫可知其詩。
“畫一鳥立于石。上,題云:閑到十分人不識,山中惟有石頭知。”此感慨是出之于鳥,還是發之于人,很明顯,是借鳥嘴說人話。
“借鳥嘴說人話”,雖是大白話,卻質以傳真,比任何一句畫論,都更能表達出齊白石之最。“畫一鳥立于石,上”的畫,已無可稽考。且舉一為人熟知的畫例,白石老人曾畫兩只雞雛,互爭一條蟲子,因利相爭,固然丑惡,然而單只相爭,不足以盡其丑。于是復加一跋語:“他日相呼。”只此四字,立使畫面延伸開來,由目前的“相爭”,延伸到以往的“相親”“相呼”。這不是見利忘義?豈止雞,“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這是畫雞,還是畫人,誰能說得清。是理、是趣,誰能分得清。意中有意,味外有味,將花香鳥語達到如此境界,真可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了。
我們過去有個約定俗成的說法,齊白石的“衰年變法”似乎得力于學習吳昌碩的大寫意筆法。不否認筆墨之于繪畫的重要作用,但這終究是繪畫創作中的“流”,而不是“源”。再好的筆墨也解決不了“借鳥嘴說人話”的根本問題。
“庚申正月十二日,題畫(畫一老翁送孩兒就學):‘處處有孩兒,朝朝正耍時。此翁真不是,獨送汝從師。識字未為非,娘邊去復歸,須防兩行淚,滴破汝紅衣。”我見過這幅畫,可能是自身親歷,舐犢情深,發乎毫端。由于來自生活,平淡中亦能生出趣來。畫中的那個,上學的孩子,一手擦眼抹淚,一手緊抱書本(又是件新玩物),傻小子,知乎知乎,這書本正是你的災星哩。王朝聞先生有句話道得好,他說齊白石“看起來并不新奇的東西,一經他的描寫,就把欣賞者誘人特殊的迷人的境界之中”,恰像白居易的詩,用常得奇。
“余亦以濃墨畫不倒翁,并題記之。記云:‘余喜此翁雖有眼耳鼻身,卻胸內皆空,既無爭奪權利之心,又無意造作技能以愚人世,故清空之氣上養其身,泥渣下重其體。上輕下重,雖搖動,是不可倒也。”
更有為人熟知的題不倒翁詩,如:“秋扇搖搖兩面白,官袍楚楚通身黑。笑君不肯打倒來,自信胸中無點墨。并附跋語:大兒人為巧物,語余:遠游時攜至長安,作模樣,供諸小兒之需。不知此物天下無處不有也。”
又如:“烏紗白扇儼然官,不倒原來泥半團。將汝忽然來打破,通身何處有心肝?
一個泥團不倒翁,忽焉褒之若彼,忽焉貶之若此,“日近長安近”,皆言之成理。看來天下事,橫看一個樣兒,豎看又一個樣兒。對于智者,無往而不通,欲通則變,善變則通,一舉手,一投足,皆可學也。
“題畫菊兼蟲:‘少年樂事怕追尋,一刻秋光值萬金。記得與人同看菊,一雙蟋蟀出花陰。”我為這畫寫過一篇小文。它之所以吸引了我,緣于畫中并排在一起的一雙蟋蟀。這“并排在一起”使人聯想起手牽手的孩子,我也曾猜想,這八成是白石老人的童年回憶,今讀此詩,證之果然。齊老先生是以童眼畫蟋蟀也。
“畫有欲仿者,目之未見之物,不仿前人不得形似;目之見過之物,而欲學前人者,無乃大蠢耳。”無異于棒喝,似這蠢事我們誰沒干過?
“畫蟲并記云:粗大筆墨之畫,難得形似;纖細筆墨之畫,難得神似。”切莫以單純畫技視之。
摘自《燕趙都市報》2019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