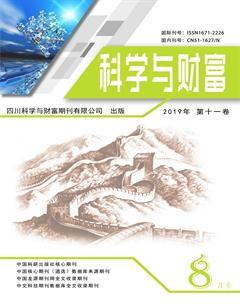淺談拜倫對徐志摩的影響
摘 要:近代中國處于民族危亡的水深火熱之中,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為了喚醒民智,大量翻譯西方優(yōu)秀著作,介紹西方先進(jìn)思想。作為浪漫主義詩歌代表人物之一的拜倫,對近代中國文人影響巨大。
關(guān)鍵詞:拜倫;徐志摩;影響
一、引言
喬治·戈登·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是英國19世紀(jì)“積極浪漫主義”偉大詩人。相較于老一代的以“湖畔三詩人”為代表的“消極浪漫主義”詩人,年輕的浪漫主義詩人形成了其獨(dú)特的風(fēng)格,被稱之為“撒旦派”詩人。他們把老派詩人看成為“為小失大,見利忘義”的“迷途的領(lǐng)導(dǎo)” 。年輕的積極浪漫主義詩人對“湖畔派”詩人到田園鄉(xiāng)村去尋求內(nèi)心的超脫的消極避世行為表達(dá)出強(qiáng)烈的憎恨。他們張揚(yáng)、叛逆,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社會秩序,極具反抗與革命的精神,與老派詩人形成了強(qiáng)烈的對比,他們盡全力將新時代的新精神表達(dá)到了極致。
拜倫出身與一個貧窮沒落的貴族家庭,天生畸形足。其父親浪蕩
荒淫,因避債逃亡到法國并死于異鄉(xiāng)。因此,拜倫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生活十分窘迫。因其個人成長經(jīng)歷,拜倫性格叛逆、行為乖張,內(nèi)心卻過度敏感。大學(xué)畢業(yè)后,拜倫世襲了其曾祖叔父的男爵爵位,進(jìn)入貴族院,但因?yàn)樵馐芾溆觯瑧崙康仉x開了英國,游歷于歐洲各國。拜倫在游歷期間,創(chuàng)作了大量不朽名篇,如《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唐璜》等。其中著名敘事長詩《唐璜》不僅是拜倫的巔峰之作,更是英語詩歌中的璀璨瑰寶。《唐璜》是一首優(yōu)秀諷刺史詩,也許也是英國唯一的偉大長篇史詩。拜倫在創(chuàng)作《唐璜》前曾說要將其寫100章,但因拜倫在援助希臘擺脫土耳其統(tǒng)治戰(zhàn)爭中病逝,《唐璜》在16章戛然而止。整首詩歌拜倫以敏銳的觀察與辛辣的諷刺無畏地揭露了當(dāng)時整個歐洲的墮落、腐敗、道德虛偽和生存的荒誕,提倡為自由解放,為幸福而不息戰(zhàn)斗。
拜倫的身上極具追求超越現(xiàn)實(shí)的自由獨(dú)立的理想,是典型的浪漫主義理想主義者、個人主義者與行動主義者。而這些特性通過他的作品完美地展現(xiàn)了出來,而這些特性被處于民族危亡的中國近代有識知識分子加以巧妙宣揚(yáng),激起了當(dāng)時麻木的中國人民的反抗意識,為當(dāng)時中華民族的求亡圖存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二十世紀(jì)的中國正處于民族危亡的緊要時期。中西方文化開始密切交流與急劇碰撞,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喚醒已然麻木的中國人,開始將目光投向西方的優(yōu)秀思想與文學(xué)著作,渴望從西方智慧中尋求能夠拯救中國的“良藥”。近代知識分子開始大量翻譯西方的優(yōu)秀作品,介紹西方先進(jìn)思想,因此,這個時期也成為了中國介紹外國文學(xué)最為旺盛的時期。其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的文學(xué)作品占主要地位,并且作品主要是以小說為主,但詩歌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部分。在英國文學(xué)中,浪漫主義詩歌處于重要的地位,拜倫作為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之一,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眾多中國知識分子關(guān)注的對象,其鮮明的反叛意識與強(qiáng)烈的斗爭精神受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對探索求亡圖存方法與道路的有志知識分子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徐志摩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二、拜倫對徐志摩的影響
徐志摩(1897-1931),現(xiàn)代詩人、散文家。新月派的代表詩人及新月詩社成員。早年留學(xué)美國與英國,他的詩不僅僅具有唐詩宋詞的意蘊(yùn)深長,又深受浪漫主義的影響,因而讀來音韻和諧流暢,言詞優(yōu)美動人,具有鮮明的藝術(shù)特性,其代表作有《再別康橋》等。
徐志摩受英國浪漫主義影響較深,從華茲華斯那里學(xué)會了人與大自然交融的和諧以及童真是人類理想的人生追求,從雪萊處學(xué)會了對自然的熱愛與自由和對現(xiàn)實(shí)的人格追求的自由。而和他同樣喜歡詩歌,同樣熱愛自然,同樣具有靈性的劍橋大學(xué)校友---拜倫,則被徐志摩看作是“美麗的惡魔”,“光榮的叛兒”,他把拜倫當(dāng)作模范與英雄,把自己看作是中國的哈羅德公子(Childe Harold),憂郁、驕傲。拜倫筆下熱情、高傲、意志堅(jiān)定、英勇不屈,具有叛逆的個人主義特征的人物更是徐志摩所追求的。他心目中的拜倫是一個“絕壁上站著的一個偉丈夫,一個不凡的男子”他在拜倫及其筆下的“拜倫式英雄”身上汲取了奇特的人格力量,不僅在他的詩歌散文(特別是愛情詩)中體現(xiàn)出來,還在生活中將其展現(xiàn)的淋漓盡致——他那理想化的愛情觀,大膽、直率、熱烈。
三、結(jié)論
在翻譯拜倫的作品期間,近代知識分子因個人啟蒙與民族啟蒙雙重人物的壓力,使現(xiàn)代中國的現(xiàn)代性追求有別于西方的特征,并制約了知識分子們對浪漫主義的視野。比方說錯誤理解了拜倫援助希臘擺脫土耳其統(tǒng)治的“英雄行為”,在拜倫的心目中,希臘并不是所謂弱小民族的代表,而是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圣殿,是他心中的精神樂園。
拜倫及其筆下的“拜倫式英雄”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拜倫所追求的自由精神,獨(dú)立的人格和俠義之性受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狂熱推崇。 李澤厚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5中指出,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存亡的外在威脅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儒家傳統(tǒng)根深蒂固的雙重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在追求自由、平等、獨(dú)立的過程中,心靈上總背負(fù)著一種深深的情節(jié)---“中國情節(jié)”。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知識分子在學(xué)習(xí)國外先進(jìn)思想文化時的局限禁錮性,和學(xué)習(xí)西方先進(jìn)思想文化時的矛盾心理并且解釋了翻譯作品不可避免的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救亡圖存的烙印的原因。因此,拜倫詩歌、精神的引入,與其說是一種先進(jìn)思想,不如說是一種工具,一種被有心人用自由解放的精神和個性來沖破傳統(tǒng)觀念和政治制度的工具。知識分子們在外國作品中僅引入自己所需的,不可避免的帶有觀點(diǎn)的片面性與理解的不完善。在介紹拜倫及其詩作時,徐志摩對拜倫及“拜倫式英雄”那種追求自由與獨(dú)立,強(qiáng)調(diào)人格獨(dú)立的個人性,敢于以個體力量來對抗具體權(quán)威和社會準(zhǔn)則與習(xí)俗,以及對命運(yùn)的叛逆精神極其敬仰與贊揚(yáng),試圖通過對這種孤傲、勇敢的叛逆者形象的引入,喚起國人日益禁錮的思想與智慧,喚起國人潛藏的勇于反抗的精神,以及喚起國人對人身自由與思想自由的渴望,從而達(dá)到救亡圖存、民族復(fù)興的大任。
參考文獻(xiàn):
[1]趙紅英主編:《英國文學(xué)簡史學(xué)習(xí)指南》,武昌: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136頁
[2]范伯群、朱棟霖主編:《1898-1949中外文學(xué)比較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十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31頁
[4]李澤厚:《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1979年版
作者簡介:
徐洲(1987 -)女,漢族,四川德陽人,講師,碩士,主要從事英語教學(xu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