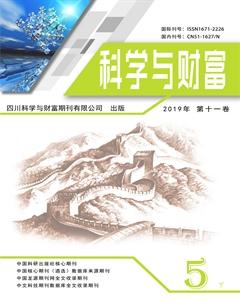從實質刑法觀看刑法解釋
蔡亞鵬
摘 要:現在刑法確定的罪刑法定原則體現了刑法的形式理性,作為形式存在的法律,是從大量法律事實中抽象出來的,在其還原適用于社會現實時,需要對法律作出解釋。本文結合當前學界對實質刑法觀和形式刑法觀的探討,以解釋方法論為工具,堅持對刑法的實質解釋態度。
關鍵詞:實質刑法觀;刑法解釋;罪刑法定原則
古人云:“先王立法置條,皆備犯事之情也。然人之情無窮,而法之意有限,以有限之法御無窮之情,則法之不及人情也。”這段來自《刑統賦解》的摘錄,表述了在古代中國的刑事法規中的“法有限而情無窮”的矛盾所在。對于這一點,古今皆然,均為考量法律價值的命題。不同點在于,古代社會為盡可能多的體現刑律貫輸的人之常情,往往引用類推解釋和比附援引,從而克服成文法的缺陷。現在刑法以罪刑法定主義為基點,劃清了公權力和私權利之間的分水嶺,從而杜絕了類推的存在。雖然對我國刑法于97年變更之時,仍有學者代表少數派的聲音,試圖挽留類推制度于刑法之中的存在,但最終還是順應世界刑法發展潮流,也從側面體現了我國司法經驗的積累和立法技術的提高。97年新刑法頒行已14年有余,期間刑法解釋學處于發展的繁榮時期,刑法學者對此也展開了激烈的論辯,正所謂“學術之盛需要學派之爭”,關于形式犯罪論和實質犯罪論之爭在學界著作中也有所體現,主要表現為形式解釋論和實質解釋論的學說對立。本文擬從實質刑法觀的視角,探討刑法解釋的合理方法論適用問題。
一、從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透視實質刑法觀
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來源于拉丁文"nullum crimen sine lege,nullum poena sine lege"。“即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罪刑法定原則發展初期,設立的宗旨是限制司法權的濫用和保障人權,在司法實踐中使用要求表現為:排斥習慣法、否定不定期刑、禁止事后法以及禁止類推和擴張解釋。進入現代社會以來,隨著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罪刑法定原則的價值觀念也由保障人權向保護社會轉變,而體現其自身的便是從形式的罪刑法定原則到實質的自我嬗變。實質的罪刑法定除了要求形式的罪刑法定所強調的刑法規范和程序的完備外,更要求刑法規范在內容上必須符合公平、正義之理念;必須考慮民主和社會的原則,強調個人利益對社會利益的服從;在傳統形式的人權保障基礎上,更加強調實質的人權保障。在陳興良教授看來,“實際上,在與形式的罪刑法定原則相對應意義上的實質的罪刑法定原則,最初是從意大利的實質的合法性原則中引申出來的。”該合法性原則同樣具備形式和實質的雙重側面,而意大利的通說是以形式的表述意義為“合法性原則”的內核,排斥實質性的側面。意大利刑法學家曼多瓦尼指出實質意義上的罪刑法定原則的傾向性表現為:(1)從法律本質來看,反對“惡法亦法”,該原則中的法只能是體現正義價值指引下的“法”;(2)從犯罪本質來看,強調“無社會危害不為罪”,在認定犯罪時可以行為無社會危害,直接撇開法條的規范予以出罪認定;(3)強調社會本位,把社會生活的維穩和社會利益的需求作為刑法的首要任務。筆者認為,曼多瓦尼的主張從刑法自身的根基上是有違近代的法治國理念,該認識是一種極端的實質刑法觀的體現。陳興良教授認為該學說與我國當前的社會危害性理論如出一撤,“無社會危害不為罪”的對應面便是“有社會危害便為罪”,以此打破形式拘束,透過實質擴大了刑法適用范圍。
筆者認為,“形式”與“實質”之爭暗含的是對刑事法治理念的差異,根本且突出的表現為對待刑法的價值選擇問題上,如果把法律的確定性作為第一要義,以保障人權為刑法的終極目標,法律的公正內涵需借助于外在的表現形式而予以實質應然性表達出來,前者則是當然之選;相反,如果從社會本位作為出發點,堅持對社會利益的保護應為刑法的首要任務,個人的價值存在于社會整體利益的背后,那么后者便為該理論青睞。這種基本價值觀的沖突,尤其凸顯了個人自由和社會維穩的沖突,而這一沖突在處于轉型時期的當代中國更為明顯,并隨著風險社會的到來而愈加激烈。
二、實質刑法觀下的刑法解釋
正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為使精英立法由語言文字應用于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刑法需要解釋。“解釋者運用語言解釋成文法的過程,常常表現為法律的文本意義與解釋者個人經驗及思想的相互征服過程。”現行刑法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之后,我國刑法學界初步產生了形式的解釋論和實質的解釋論之間的學術爭論。前者如阮齊林教授所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還將導致刑法解釋方法論的轉變,即由重視實質的解釋轉向重視形式的解釋”之論斷,后者則是張明楷教授所提出的“只有從實質上解釋犯罪構成,才使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成為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的看法。同樣主張實質解釋論的前田雅英等教授認為“對構成要件的解釋必須以法條的保護法益為指導,然后在刑法用于可能具有的涵義內確定構成要件的具體內容,并且將字面上符合構成要件、實質上不具有可罰性的行為排除于構成要件之外”。對于此種爭議,必須看到解釋學首要是作為刑法研究方法論的工具,盡管張明楷教授提出“解釋學的問題超出了單純的方法論,它是方法和真理的統一,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本體論的問題,是哲學的最根本問題”。但并不能否認自身工具方法價值是解釋學存在的首要意義。因而,我們必須明確解釋的目的是什么,其存在的根基是什么。趙秉志教授指出,“刑法學理解釋為這些問題提供了經驗豐富和認識準確的解答。刑法規范的明確,定罪量刑條件的厘定,符合刑法解釋的對象――刑法條文的司法應用。”而當前司法和執法部門過于強調刑法條文的實踐操作,希望上級部門作出可直接適用的規定,而此種情形恰恰存在于“刑法解釋的邊界”問題之中。“所謂刑法解釋的邊界是指入罪解釋的邊界,這是一個邏輯前提。……我們關注的焦點是:在對法無明文規定,按照實質解釋論的表述,在法律沒有形式規定的情況下,能否通過刑法解釋予以入罪?只有在這一問題上,才存在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之爭。”筆者認為,形式解釋論和實質解釋論并不存在根本意義上的沖突,兩者對于刑法的目的實現和正義理念的追求并不存在偏頗,主要的區分還是在于如何確定罪刑法定原則下的刑法解釋的邊界。當前學界對于兩種解釋論的爭議,在很大情況下忽略了探討這一問題的前提要件。在這一點上,劉艷紅教授認為:“實質的刑法解釋……更注重嚴格控制解釋的尺度而只將那些值得處罰的行為解釋為犯罪,從而實現對國民權利的充分保護,實現刑法保障公民的自由人權的目的。”以此堅持實質刑法解釋論更有利于實現刑法學的目的,即保護法益和保障公民的自由人權。
三、結語
綜上,實質的刑法解釋論就是對作為形式規范而存在的刑法條文背后所蘊含的刑事正義的理念價值追尋,刑法解釋首要作為法律技巧和方法工具存在,更是以科學的價值判斷引領法律實務界對刑法自身進行實證化方法的運用。從這一點來說,實質解釋論的運用不僅是刑法學的理論問題,更是刑法研究方法的適用問題。
參考文獻:
[1]周少華.“類推”與刑法之“禁止類推”原則――個方法論上的闡釋[J].法學研究,2004(5).
[2]劉艷紅.實質刑法觀[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