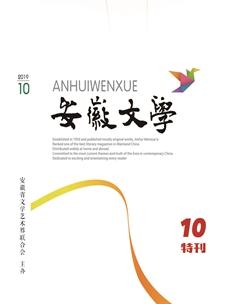葵花子兒、西瓜子兒
賀建軍
我這人有點耿,好認死理,但一直坦坦蕩蕩個性鮮明,缺點明顯優點顯著,單說吃這一塊兒,同樣如此,用好吃而不懶做表述,最為恰當。現如今吃貨滿天飛,都不說自個兒好吃,偏偏美其名曰成了美食家,讓我這好吃的缺點逐年優化成了優點。
生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的我,打小就好吃,尤其少年時期,成長在物質極度匱乏年代,看啥都是美味,吃不到嘴里的更念念不忘。生在合肥市中心,長在市中心的四牌樓,奈何家境窘迫,全家只有父親一人拿工資,我多是看著別人家的小孩吃。餅干、蛋糕、果脯和我基本無緣,哪怕最便宜又甜膩的伊拉克蜜棗,也是要到過年時節才有機會吃到。
到了夏天,像黃瓜、西瓜、西紅柿這樣的“大路貨”便宜得很,早市之后常常是黃瓜、西紅柿估堆賣,西瓜論個賣,自然成為百姓消夏解暑的美味。許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吧,在我還是小屁孩兒的時候,居然就會挑選西瓜。先看西瓜皮上紋理的舒展程度和西瓜屁股上的圈圈是否長得圓,再抱起西瓜貼在耳畔輕拍,能找微微震手、聲音“嘭嘭”的,準熟。還得是鮮秧子瓜哦,不然熟過了買到“倒瓤子”瓜,可是大大不劃算。
西瓜吃完了,洗干凈的西瓜皮可以做成涼拌菜,那是大人的事。我就忙著把淘洗干凈的西瓜子放在竹篩子上,就著熱烈的大太陽曬干,再一點點仔細地收集起來。等攢夠了一平碗,我就打開煤球爐,支上鐵鍋,倒入瓜子,開炒。待炒至大半熟時,撒上一點加了五香粉的鹽水,再翻炒幾下,咸香可口的西瓜子就出鍋啦。
這或許是我好吃不懶做的初級階段吧。
說起這嗑瓜子兒,端的是源遠流長。有資料說嗑瓜子的習俗在明代已經流行,清代民國愈演愈烈,晚清之前,“瓜子”主要是西瓜子,晚清以來南瓜子開始流行,到民國時期,葵花子又異軍突起,最終確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兒時我曾種過幾棵蓖麻,那是老師的科普要求,說是讓我們學習掌握蓖麻油在科技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也種過幾棵向日葵,是自己央著爸媽種下的,我眼巴巴地看著向日葵欣欣然地朝著太陽生長至成熟,一直等到偌大的花盤里結滿了飽滿的果實,才欣然摘下。
原產于南美洲的向日葵種子,便是我們愛吃的葵花子兒。有古詩這般吟詠向日葵:“花開為仁仔,花落為其家。惟愿多結子,名曰向陽花。”司馬光在《客中初夏》一詩中有“更無柳絮因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的美好描繪。
不像如今遠離土地、缺乏陽光雨露的城里人那般癡傻地欣賞美麗的向日葵花,我這“好吃精”關注的是飽滿厚實的葵花子兒。曬干,隨便炒炒,便是美味。出門玩耍時,在小小的褲兜里裝上一小把,遇到小伙伴時不時炫耀地掏出幾粒,好不愜意。
從宿州路九號省文聯大門口到紅星路小學不過幾百米,順著梨花巷走走就到了。那時候年紀小不懂事,除了對能吃的好吃的、能玩的好玩的感興趣,其余的對啥都不求甚解,甚至于我還真干過一次上學不帶書包的事,到了教室才醒悟過來,撒丫子往家跑回去拿書包。就像老師說起遠郊的大蜀山,我們都堂而皇之地稱之為“大頭山”那樣,這文字里透著詩情畫意柔美抒情的梨花巷,同樣被我們這些小屁孩喊作了“泥巴巷”。要是用合肥土話把“泥”音作“謎”音喊出來才好聽,更有韻致。
哪有小屁孩兒們不好吃的,在20世紀七十年代,牛奶冰棒五分錢一支,豆沙的和香蕉的分別是四分錢和三分錢。有小伙伴買了一支香蕉冰棒,邊上要好的幾位小伙伴一準兒理所當然地要求咬上一口,無需多言,咬了再說——上次我買冰棒時你都咬了一大口。
那要是小小的褲兜里只有一分錢咋辦呢?沒問題,照樣會有好吃的等著你。在低矮民房散落其間的“泥巴巷”中段,有個經年累月擺設的小攤子,是位老太太賣著五香葵花子兒,一分錢一小杯。老太太可是大名鼎鼎的“抖手老太”,幾乎全校同學都知道。“抖手老太”擅長用一個小小的透明白酒高腳杯,往葵花子堆里一舀,滿滿當當的瓜子看著喜人,等到往你張開的小手里倒的時候,“抖手老太”的手就開始止不住地抖啊抖啊抖,總算把小杯里的瓜子兒給抖平了,才會瀟灑倒下。或許被我們那眼巴巴且不甘的眼神盯怕了,“抖手老太”會隨手抓起兩粒放在你手心里捧著的那一小捧瓜子上,嘴里嚷著:“伢啦,再饒你幾個。”一派大方慷慨風輕云淡的樣子。
小學畢業上初中,我去了離紅星路小學兩百米之遙的合肥九中。我們四班有六十人,我的入學排名在第四十名,知恥而后勇地奮起直追唄,到了第一學期末,居然躍進到第八名,數學還考了年級并列第一,也許是超常發揮,至少證明我還是能學好數學的。只是,我又當上了語文課代表,由此走上了嚴重偏科之路。
我們四班是重點語文實驗班,省級的,當時全安徽省只有兩家。語文老師韓超倫講課生動風趣,我們都愛聽。我至今還記得韓老師的諄諄教誨,以及“聽、說、讀、寫、練”“看、查、想、議、改”等多種語文學習方法。時任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的丁先生,曾數次親臨我們語文實驗班聽課、調研。
我和團支書張萍合寫的關于我們語文實驗班的通訊,居然在全國著名的《語文報》頭版上有一席之地。那是我得到的第一筆稿費,當時是冬天,我和同學們為抗拒嚴寒,靠用力在走道墻壁“擠油渣渣”抱團取暖呢。三元錢稿費到手,我和張萍各自分了一元以示紀念,還剩下一元錢,全買了多味葵花子,與班里同學們一同分享。1982年的一元錢,真的蠻值錢,那時校門口的肉餡燒餅只要六分錢一個,你便能算出來我買的多味葵花子該有多大一堆。同學們吃得可歡實著呢。
瓜子兒好吃,只是我這一偏科,把我的高中學習生活給偏到了合肥三中。
上高中三年,依舊是語文課代表,還兼了勞動委員、體育課代表啥的。大約是1985年初夏,我的第三筆稿費到手,五元錢。那篇稿子是寫初中語文老師韓老師的,取“韓”字的一半,篇名《韋老頭子》,發在《作文周刊》上。韓老師在課堂上曾有高論,說“老頭子”應該是褒義詞:“老”——德高望重,“頭”——一身之首也,“子”——古之圣賢美稱也。結合韓老師的滿腹經綸兼“奇談怪論”,這篇《韋老頭子》寫出來理應出彩傳神,要不,我這純粹的自然來稿,哪兒會被全國知名的《作文周刊》的編輯老師看中啊。
班里同學鬧著讓我請客,我開心地答應。嘿嘿,有經驗了,買葵花子唄。下午上學路上和同學一起買了三元錢的多味葵花子,帶到學校,上課前,大家伙兒都在熱火朝天地嗑著瓜子兒,順便兒夸著我的能耐。我表面上虛心自謙,內心里還是不免有些沾沾自喜、暗自得意。
下午第一節是政治課,嚴謹的政治老師一上課發現今天有些異乎尋常——課堂上人人目光炯炯,沒人犯困沖瞌睡。政治老師不吱聲,安心講課,背對著我們在黑板上板書的時候,悄悄地豎起了耳朵。果不其然,落入老師耳朵中居然有一兩下微弱的嗑瓜子聲。老師轉過身來,迅疾地把手中的粉筆頭砸向發出聲音的同學。
“怎么回事?”老師大聲地問。
令老師再吃一驚的事發生了,同學們不去看那個嗑瓜子的,竟然全部看向我。慘啊。就這樣,我被罰站了一節課。放學后,又被班主任老師罰我打掃教室衛生。唉,這下,我可是得意不起來咯。
安徽是炒貨大省,本土出產的傻子瓜子、洽洽瓜子、陶永祥瓜子都是我的最愛,捧著小說,嗑著瓜子,滋潤,舒坦。
從我上小學直到高中畢業去當兵,父親賀羨泉一直是《安徽文學》的詩歌編輯。父親下班回來時會帶上新出刊的交換雜志,讓我接觸到了更多的文學期刊,像《清明》《鴨綠江》《上海文學》《朔方》等等。自此我愛上了閱讀,尤其是小說,我細細品讀,沉浸在別人的故事里,感受著人生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交換的雜志看完了,自己就去書店或是郵局買書看,幾十年來還真看了不少小說。
當然,嗑的瓜子兒自然數不勝數。
如今的我,已然過了半百之年,愛看書,愛品茶,愛旅行,愛下廚,還愛嗑瓜子兒。當然,好吃而不懶做也已操練到爐火純青。只是,再無年輕時候看書一夜到天亮,瓜子殼兒堆成一座山的氣勢。
若是瓜子兒嗑得多了,真的會上火呢。
責任編輯 洪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