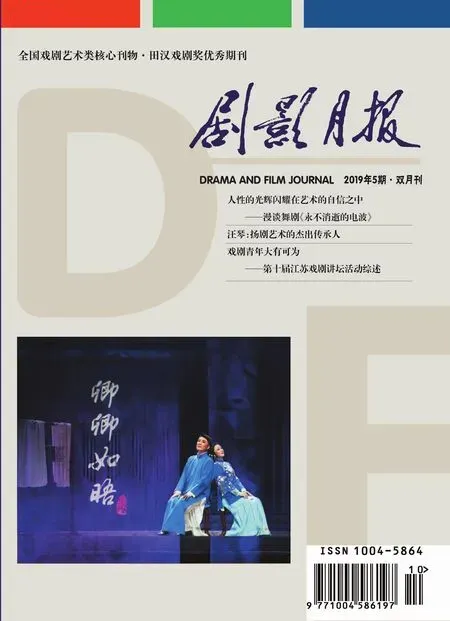戲劇青年大有可為
——第十屆江蘇戲劇講壇活動綜述
曹敬輝
8月19日至23日,火熱的南京,迎來了一群朝氣蓬勃的青年戲劇人,第十屆江蘇戲劇講壇在寧舉行。本屆講壇由江蘇省戲劇文學創作院主辦,邀請了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羅懷臻,著名劇作家、河南省文聯副主席陳涌泉,北京京劇院優秀青年編劇、導演李卓群,上海戲劇學院專職導演、制作人馬俊豐,江蘇省昆劇院優秀青年演員施夏明等戲劇專家、青年戲劇新秀授課。期間,還舉辦了2018年江蘇省戲劇文學劇本評選頒獎儀式,榮譽導師授聘儀式,向學員贈送了江蘇戲劇講壇十周年紀念《劇影月報:十年嘉木蔚成林專輯》等。江蘇省戲劇文學創作院副院長李明華、袁纓、羅周、管若松及來自全省各地的近60名學員參加了活動。
一場關于青年戲劇的美麗約會
本屆講壇以“青年戲劇”為主題,參加本屆講壇的學員80后、90 后占80%以上。授課專家也以80 后為主。這是一場平均年齡38歲以下的戲劇人的聚會。以導師為例,或是青年編導講自己,或是著名編導講自己的戲劇青年。優秀青年編劇、導演李卓群,她生于1985年,目前供職于北京京劇院,她執導和編劇的作品有作品《惜·姣》《碾玉觀音》《春日宴》《好漢武松》《人面桃花》《大宅門》等,其作品極簡卻精致、細膩且豐滿,其藝術風格和體制探索在業內外受到了廣泛贊譽。她講授的題目是《戲曲導演:書案到舞臺的行者》,她認為小劇場戲曲藝術創作的特點在于小、深、精、廣,小即規制、視角小;深即立意、功底深;精即呈現、制作精;廣即觀眾、宣傳廣。她結合自己多年來創作的作品,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她舉例自己編劇和導演的《惜·姣》,從一、二度創作上尊重和秉承較為成熟的傳統戲演劇風格,在新本中將故事和人物予以完整和豐滿,將閻惜姣的命運悲劇通過情節的鋪敘與情感的鋪墊,在二度上以京劇本體的藝術形式呈現于舞臺,做到敘事與抒情、現實主意與浪漫主義的融合。舞美形式沿襲“一桌二椅”、劇情結構遵從“起承轉合”、角色設置歸屬“四樁當行”、音樂意象比興“春夏秋冬”、表演道具涵蓋“蹺絹扇髯”,塵封數十年的“蹺功”重現舞臺。最簡潔,最熾烈;最寫意,最京劇。在劇場中勾勒出了一幅宋時坊間的工筆重彩畫卷。節奏緊湊,扣人心弦,明艷離奇,哀絕驚心。戲曲《破陣曲》再現桂林“抗戰文化城”的光輝歷史和動人故事,采用“群像式”手法,圍繞國歌詞作者田漢、畫家徐悲鴻、戲劇家歐陽予倩、教育家馬君武和音樂家張曙五位文化人士在桂林時的經歷與追求展開劇情,展現了在大后方紛繁復雜的形勢下,他們的家國大義與生死抉擇。該劇將山水、棧橋、漁船、巖洞、石刻等桂林元素融入舞美,投影上殘酷的前方戰場與舞臺上后方文化戰線交疊轉換,從多角度還原了民國文化名城的歷史風貌,也彰顯出桂劇這一經典劇種在新時代的傳承與風采。


李卓群還認為,戲曲中的“骨”、“肉”、“皮”、“毛”的生理結構也很重要,她認為骨即劇本;肉即二度創作;皮即包裝;毛即宣傳。李卓群在傳統戲《烏龍院》基礎上進行大膽改編,借鑒美劇風格,使得情節更緊湊、人物特點更鮮明、結構沖突更有張力,一日之內,花葉輪生,四季輪轉,生死輪回。《春日宴》呈現小劇場戲曲的最佳陣容,用紅生花衫組、花臉花旦組二組演出陣容,首用“平行蒙太奇”手法,跨越古代、現代、文革三重時空。戲淺意濃,情溢盈懷。《好漢武松》反其道而行之,雖然導演在劇本節奏、服裝道具、音樂配器等多處細節求新,但情節上仍保留了傳統京劇劇目中《武松打虎》《挑簾裁衣》《獅子樓》的核心情節;主題上深化原著中的武松精神,建構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隱喻。同時,演員的表演則完全承襲傳統京劇表演程式,突出傳統武生戲的審美特點。
80 后導演馬俊豐,現任上海戲劇學院專職導演、制作人。馬俊豐以《步步驚心——以導演舞臺劇<繁花>為例說開去》為題,結合自己創作《繁花》的前因后果,通過話劇的現代性呈現、小說的舞臺改編等角度談創作實踐的心得體會。話劇《繁花》編劇、導演、演員等主創基本都是80、90后,這個具有時代氣息的原著《繁花》,在一群年輕人的“現代”解讀下,話劇版《繁花》懷著野心,要描繪現代生活中的上海。事實上,他們的確做到了現代性的上海,而不是文人懷舊中、或者是思維定式里那個被無數次等作品消費的舊上海。對《繁花》的現代化,直接表現在演員的年輕化上。年輕化同時也是強烈的美化。六七十年代難以忍受的生活艱難和思想禁錮的難堪,都被青春的荷爾蒙所虛焦為某種集體性的美好記憶。這種虛焦是徹底的,盡管舞臺上時刻降落下電線桿,耳邊響起火車轟鳴。
關于小說的改編,馬俊豐認為,《繁花》的原著選擇了在上海歷史中黯淡無光的某些時間段,它們的存在只在提醒它們可以被遺忘。也因此,這里的上海才根本上是市井的,沒有宏大的殖民時代敘事,沒有西洋萬物的炫彩和糜爛,只有弄堂里的你我,這逼仄、纏聯、被群體所支配的市民普通生活:無論何時,哪怕被置換為現在,上海始終還是那最城市、最瑣碎卻也最繁華的一面。在話劇版里缺失《繁花》的原著文本強烈的群像集體性。單以戲劇性來看,雖然每一場戲都有精妙的氛圍和情緒的構建,演員、制作、導演的巧思無處不在,情節的潛臺詞哪怕不用太多的“不響”都回味悠長。可是這些東西都是專屬于劇場的,甚至可以說,都是碎片化的。話劇版《繁花》將原著里的繽紛人事,最終集中在了六七十年代的滬生與姝華、銀鳳與小毛,以及九十年代的汪小姐與徐總,阿寶與李李四對八人身上。實際上,將原著細密繁雜的文本提煉出直接的戲劇沖突和人物關系,是作為一部商業話劇的必備要務。
生于1981年的羅周,其作品曾多次獲得曹禺戲劇文學獎、田漢戲劇獎,并獲中國戲劇節優秀編劇獎、全國戲劇文化獎編劇金獎等多個國家級獎項。她授課的題目是《命題作品的開掘與寫作》,她與大家分享了找到素材,定好題旨后,如何來最大限度地體現題旨的創作經驗。如何在命題作文中挖掘思路、亮點、題旨。戲劇劇本的結構方式和題旨的探尋。怎么用古典戲曲的形式寫現代題材?怎么處理現代題材的唱念寫作?如何與導演溝通,較好地傳達自已預期中的風格樣式?編劇如何考慮與作曲的關系?多角度地展開論述。她還從作品的構思開始,一步步進行創作演示。她總結自身劇本創作的步驟是:“素材——題旨(最高價值、目的地、巔頂)——結構——劇情——分場——每一場的目的地——載體、結構——文字”。并舉例京劇《梅蘭芳·蓄須記》。素材取自梅蘭芳相關文史材料。題旨為:藝術設有國界,藝術家有他的祖國。該劇戲劇結構是“三訪一亮相”,中島三訪梅蘭芳,梅蘭芳以蓄須一舉在世界面前亮相。基本劇情是太平洋戰爭爆發,梅蘭芳自港返滬,等待他的是日軍的一次次脅迫……全劇分拒票、拒演、寫畫、蓄須四場,寫作時要對每一場要達到的目的了然于心,并考慮每一場的小結構與載體。如《寫畫》以梅蘭芳畫牽牛花為載體,展現他龐大豐富的京劇世界。《蓄須》以讀《豫讓橋》劇本為載體,完成他不躲不避,迎之而前的亮相思考。她還以越劇《烏衣巷》為例。其基本素材是含《世說新語》在內的王徽之、王獻之的文史材料。徽之獻之兄弟,是書圣王羲之之子,家族顯赫,才華橫溢。劇中二人均由南京市越劇團優秀青年演員李曉旭飾演。故而戲劇采用的是雙主角交替登臺的結構。該劇帶領觀眾重回一千年前秦淮河畔烏衣巷里,通過徽之、獻之、郗道茂、新安公主的婚變與糾葛、誤會與了悟,以《選婿》《寫扇》《訪郗(楔子)》《開箱》《叩琴》為分場,充分運用扇子、書法、琴曲等為載體,完成了“情之所鐘,正在我輩”的題旨。
隨后,羅周還和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優秀青年演員施夏明進行了題為《傳承·發展·開拓——以昆曲折子<訪戴>為例》的對話式的授課。他們以《世說新語》系列折子戲中的《訪戴》為例,從文本寫作談到表演藝術之于文本的完成與再創,強調了對前輩的學習傳承與為后世開辟前行之路。
兩代戲劇人對文學性問題的思考
授課專家羅懷臻生于1956年,陳涌泉生于1967年。但是,他們的代表作創作于30 歲左右的青年時期。羅懷臻是當代著名劇作家,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90年代初便創作了奠定其地位的作品淮劇《金龍與蜉蝣》(上海淮劇團1993年首演),獲得文華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曹禺戲劇文學獎。羅懷臻以《紅色題材的藝術表達一一從舞劇<永不消失的電波>創作說起》為題,他指出,《永不消逝的電波》作為一部表現地下黨生活的紅色題材舞劇,沒有依靠宣傳或行政手段做推廣,之所以引發觀看熱潮,一票難求,在于該劇的文學性與深沉的情感表達。他認為,舞劇,是舞蹈,也是戲劇,就有文學性,需要劇情。他說,放眼古今中外的舞劇經典,無不具有一個完整的故事,無不表達一種基本的價值觀,無不追求真善美的人性表達。該劇的劇本不長,就幾頁紙,但舞臺上跳了兩個多小時。劇本里描繪了上海的市井,陰雨霏霏,在迷蒙中有市井,市井中又有壓抑,人們的行走匆匆忙忙,就在這行走中,發生了很多事情。這個人群構成的叢林其實也是城市的陷阱,吞噬著人的生命,危機重重。舞劇編導根據這些描述編排成舞臺上的開場舞:風雨如晦的街道上,黑衣人撐著傘迅速穿梭,故事就發生在這個節奏緊迫、情感壓抑的場景里。
羅懷臻認為該劇的成功在于價值觀的沖突。戲劇性其實是受到蘇聯戲劇觀念的影響。我們對戲劇的關注停留在事件的戲劇性上,戲劇的沖突是事件的沖突,所以要設計情節。后來,我們受到歐美影響,開始講性格的矛盾組成戲劇性矛盾的焦點,也開始認識到價值觀的重要。如今,則越來越體會到,價值觀其實是人與人之間親疏關系的關鍵,價值觀的沖突也是一種沖突,有時甚至是一種本質的沖突。該劇別具匠心地選用“上海特色”作為表達的核心內容,以主要人物以及主要人物周邊的人物、事物構成戲劇沖突。以“環境”影響“人物內心”,進而構造“矛盾沖突”,也是本劇的一個特點。
該劇最令羅懷臻感動的是故事原型李白,他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12年,兩次被捕,經受各種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嚴刑拷打……最后,卻犧牲在上海解放的前夜。人的行為總是有具體目標,李白向往一個新的政權,期望能在其中有所施展,但他卻倒在了目標實現的黎明前。該劇關注的是人生,紅色題材也是一種人生,能讓大家感動,因為每個人都能在其中產生各自生命的聯想,因為你可能遭遇過有些情境和有些感情。舞劇也需要情感。而呈現在該劇里的情感表達在何處?羅懷臻認為:第一,價值觀。該劇的男女主角可以面對無盡的苦難,但是他們的信念不能出現動搖,敵我分明,意志堅定,所有的苦難、痛苦都是在人物自身的堅守中發生的。第二,樣式感。該劇是海派的,是上海的,又是諜戰的,緊張的,劇中人經常緊張到想嘔吐。這種壓抑感、緊張感、隨時不安的感覺不能改變。第三,人物關系。這個舞劇,劇中人物大都具有雙重身份,每個人都帶著一副面具,防不勝防,人物之間的關系很復雜,這對長于抒情、拙于敘事的舞劇來說很難。這三點中最重要的就是價值觀及其中傳達的情感。這不是一種空洞的情感,而是通過表現尋常的情景,讓英雄回到一個普通的家庭,丈夫、妻子、孩子,最后難分難舍,他回到了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人為了一個壯麗的事業,在日常生活中,每天經歷著可怕的壓抑,卻還是在堅守。這就是需要表達的感情。
陳涌泉創作的代表作《阿Q 與孔乙己》《程嬰救孤》《風雨故園》等成名之作時同樣是30 歲左右的年紀。陳涌泉以《改編與原創——以<阿Q 與孔乙己><風雨故園>為例》為題,談了改編的方法和原創的標準。他告訴青年編劇,改編是戲劇創作的傳統,是戲劇發展的主流。改編和原創沒有高下之分,只有成敗之論。善于改編才能更好原創。于戲曲藝術而言,太糾結于原創沒有意義,那樣只會催生出更多的“偽原創”,給觀眾帶來“審美災難”。當然,創新是改編和原創的共同標準。所以,改編要背靠傳統、背靠時代、背靠文學。

羅懷臻說,出身于大學中文系的陳涌泉深受現代文學的影響,很自然地吸收了五四以來現代文學的傳統養分,其創作特別強調戲劇文學作品的現代意識,同時注意將其輸入地方戲曲,因此,他的作品給人的感覺就是富有文學感。這個文學感不是華美深刻的辭藻,不是古典文學的氣韻,而是現代文學的氣質,其表現為對自然人性的自覺關注、對人的生存的促進、悲劇的審美趨向、現實主義追求、戲劇結構的現代化等。這是他在整個河南劇作群家中不可替代的特殊貢獻,也是他創作特別突出的優勢。
在談陳涌泉的作品《阿Q與孔乙己》時,羅懷臻評價,這是世紀末的回眸與檢視,在傳統戲曲與現代理念、文學經典與通俗戲曲之間辟出了一條新路。羅懷臻認為,魯迅先生的小說世界里,著重為我們塑造了兩類人物形象。阿Q和孔乙己這兩個人物性格的截然不同和價值觀念的巨大差異,注定他們潛在互生的、強烈的戲劇性。在他們身上我們還能看到很多相似之處:都孤獨、麻木,都深受封建制度的戕害,在喜劇的面具下,都包藏著一個悲劇的內核,借魯迅先生的話,都是“壓在大石底下的草”。把這兩個人物集中在一起交叉對比,有助于觀眾從他們險惡的生存環境和畸形的精神世界中,感悟、發現更多的東西,從而更澄明地了解歷史,更深刻地認識現實,更細微地體察自我。把兩部作品結合起來改編,其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理論上應高于根據任何單一作品改編的戲劇作品,甚至可以收到“1+1>2”的效果。
陳涌泉認為原創劇本要學會獨立思考、獨家發現、獨特表達、獨一無二。原創具有:開創性、獨特性、唯一性、爭議性。陳涌泉結合自己37 歲時創作的豫劇《風雨故園》,談戲劇的改編說,《風雨故園》通過魯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凄苦心路歷程講述了她和魯迅之間沒有愛情卻有親情的人生故事。讓更多的人知道世上曾經有一個叫做朱安的女子,她嫁給了一個后來名揚天下的人,卻一生沒得到他的心,生前沒有愛,死后又失去了名。讓更多的人知道“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有著自己的傷心和無奈,一個反封建斗士卻無法逃脫封建包辦婚煙的傷害,不得不做長達二十年的妥協:讓更多的人知道原來自己遠未接近事實的真相,從而對傳統文化和中國近現代史產生新的反思。陳涌泉說,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起到一點點這樣的作用。希望通過舞臺實踐,能夠還朱安以尊嚴,還魯迅以公正,還歷史以真實。文學應該關注強大背影里的弱小,傾聽主流話語下的呻吟,敬畏經典,敬畏原著。
陳涌泉說,作為一個中文系出身的人,魯迅先生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從事戲劇創作后我的處女作《阿Q 夢》、成名作《阿Q與孔乙己》均改編自魯迅先生的小說即是證明。我對魯迅先生的深厚情感非一般人可比。正因如此,我愿帶領觀眾走進魯迅的心靈世界,感受他的呼吸,體會他的脈動,認識一個有血有肉、偉大而真實的人間魯迅。因為只有讓魯迅走下神壇、回歸人間,他才能更好地走進二十一世紀,更好地為當代觀眾、特別是青年觀眾所接受。他特別強調,對戲劇傳統的反叛、對中華美學精神顛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統美德價值的否定,不指向原創。真正的原創應當以堅定的文化自信為基礎,以堅守中國戲曲美學精神、堅守中華傳統美德為兩翼,以持中守正、固本求新為原則,以現代人類共同價值為導向,以培育美的人性為目標。
生長中的青年戲劇
這次講壇是60-70年代和80-90年代出生的幾代戲劇青年人的思想碰撞和對話會,一堂青年編劇、導演、演員觀點碰撞的論壇。還舉辦了2018年江蘇省戲劇文學劇本評選頒獎儀式,本次評選共評出特別獎1 名,一等獎2 名,二等獎3 名,三等獎5 名,提名獎4 名。同時,向學員贈送了江蘇戲劇講壇十周年紀念《劇影月報:十年嘉木蔚成林專輯》等。江蘇省戲劇文學創作院負責人、副院長李明華介紹,戲劇講壇從當初向各市通知分攤名額,變成為現在從上年度劇本評選的參評作者中點名參加。十年來,培植了作者、活躍了創作,也使得一年一度的江蘇省戲劇文學劇本評選,由十年前的每年四十來部,上升到目前的八十余部。江蘇戲劇創作人才隊伍青黃不接的局面,得到了改變。為我省演出院團的劇目生產提供了保障,也為各演出單位申報國家藝術基金、省藝術基金的資助項目提供了劇本支持。應邀講課的專家,幾乎涵蓋了國內知名劇作家、導演等戲劇創作信息、拓寬藝術視野的同時,也增進了省外戲劇專家對江蘇戲劇創作者的關注和了解。
十載風雨,春華秋實,江蘇戲劇講壇至今已舉辦十屆,培養了一大批在全國具有影響力的戲劇人。面對江蘇的青年編導取得的豐碩成果,曾多次受邀參加講壇授課的羅懷臻對江蘇青年編劇如數家珍,羅周是全國新生代編劇的代表人物之一,張軍剛剛有作品獲得文華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仲春梅、言禹墨等的作品在他的推薦下,在上海等地由劇團演出……目前,江蘇擁有戲劇編導百余名,很多作者在全國有一定影響力。當前,戲劇講壇學員呈現高學歷、低齡化,學員中獲得江蘇省戲劇文學劇本征選二等獎以上的80后、90后學員已有十余位。
面對如此眾多的優秀青年學員,羅懷臻還以《氣質·氣候·氣象一一劇作家的自我塑造》為題,詮釋了劇作家應該要有的素養。他認為劇作家自我塑造的三個要素:他認為第一是氣質:氣質是先天的,是一種宿命;第二是氣候:氣候是后天的,不能選擇,有一種難言的微妙的變化;第三是氣象:先天的東西經過后天的作用,成型,優與劣,結合在一個人身上。羅懷臻結合自己的年青時候的創作,以自己的創作成長道路為例,他勉勵青年劇作家要學會發現自己、發掘自己、發揮自己,忠誠傳統、忠誠時代、忠誠內心。他指出,青年劇作家要健康的成長,在陽光里成長,不要故意去遭遇所謂的“挫折”。他說,一個種子是不可能改變土壤的,而是要努力去適應這個土壤。每一件作品必須首先感動自己。不然,很難去感動觀眾。關于氣候,他認為,不管時代如何變遷,都不是逃避寫作的借口,不真誠面對寫作的借口。羅懷臻說,他不贊成政治干涉藝術,也不贊成藝術干涉政治。一個人的氣質與所遇的氣候,形成的氣象,高度的吻合。每個人其實都是代言者,成就的大小,看你為誰代言,代言的程度。只有把獨一無二的、不可復制的自己呈現出來,才能攀上一個高峰。
十年來,江蘇戲劇講壇堅持以人為本,旨在培養全省中青年編導的審美情趣和人文素養,提升精神境界,激勵人生追求,樹立作品立命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學員通過學習,學員們在創作觀念、藝術技巧、戲劇藝術創作的動態與趨勢等諸多方面,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和認識。通過集中培訓和學員間的相互交流,也極大調動了青年作者的創作積極性。無錫市文化館戲劇編劇周宇,1989年生于徐州,2013年考進無錫市文化館擔任行政工作。她獲得2018年江蘇省戲劇文學劇本評選一等獎,談到獲獎,她感激地說:“我的昆曲劇本《豫子刺襄》能夠獲獎,離不開在戲劇講壇上,老師講授的戲曲創作理論。特別是張弘老師認為情節和沖突并不是戲曲創作的核心,戲曲寫的是情與趣,人物的情感及其舞臺呈現才是戲曲創作應該關注的重點。戲可以揮毫潑墨,然而情感卻必須細致入微。情感的力度越強,戲就會越動人。這給我全新的視角和啟發。”著名青年編劇,鹽城市劇目工作室主任楊蓉,曾創作過《三三》《青衣》等一系列具有全國影響力的作品。她說,我從1994年大專畢業,進入劇目室是會計崗位。當時市劇目室僅有兩人。局領導要求培養接班人,領導便開始培養我們。十年的戲劇講壇,我聽到了全國不同專家老師的講課,從文學到戲劇到哲學,從編劇到導演到音樂……讓我們在經歷了一年的戲劇創作實踐后,沉淀下來,重回課堂,接受洗禮,重新梳理自己的創作思維與理念,得以開拓,得以整理,得以回顧,得以反思……好苗需要春雨潤,在戲劇講壇的催化下,如我在內的一批中青年編劇得以成長、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