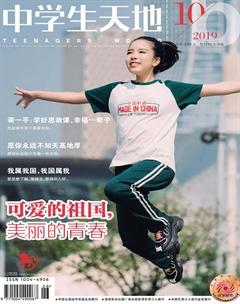慢車去“遠東”
金竹
俄羅斯國境入口,途經一個叫琿春的城市。琿春在滿語里有“邊地角落”的含義,這座小城是名副其實的邊陲之地——中俄朝三國交會處。慢車坐了一夜,我也疲乏了,尋思著下車去洗把臉。琿春火車站簇新而亮堂,站內貼心地標注了朝鮮文、俄文、中文,方便不同國籍的乘客辨識,可逛遍車站,我愣是找不到洗手間在哪里。
詢問站門口的大爺,他解釋說,琿春這幾年才發展起來,車站是新建的,衛生間還沒造好。大爺又指指站外的荒野:“在那兒,有個旱廁。”上一次接觸旱廁,還是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高原上,缺水又極寒,想不到在東北邊境又遇上了。
意料外的野地旱廁竟讓我莫名感到快活,從旱廁出來,站在齊腰高的荒草叢中,我有種想朝著東面的俄羅斯邊境大聲喊“你好”的沖動——或許我們并不像原本以為的那樣嬌貴。身為學生,每一趟精打細算的火車旅行我都不期待能有多“舒適”,條件簡陋一點,反而更有回歸原初的感覺。
事實證明,我的遠東之旅自始至終野氣十足。首先是入關,符拉迪沃斯托克海關被戲稱為“全球最破”,絕非浪得虛名。一個鋼棚,沒有空調和暖氣,兩個工作人員,無暇顧及排隊遞護照的旅客。過了海關并未直達終點,車還要穿越大片荒原,往東走上大半天。我也算見過不少荒原,但中俄邊境的無人區與眾不同,這里的荒草完美詮釋了“野蠻生長”這個詞,大有天高皇帝遠的氣派,鋪天蓋地,隨心所欲。
傍晚的荒原中閃現出一灘灘幽冷湖泊,我知道目的地將近了。聽人說過,俄羅斯屬于冷水海域,與我國境內的暖水海不同,這里的湖泊更為深邃、清冷。窗外的水域逐漸密集,終于變成綿長靜謐的海岸線,前面就是遠東最大的不凍港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我住的小旅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車站附近,是一幢獨門獨戶的紅房子,木質扶梯吱嘎作響,單人間不大但勝在清凈。出門就能看到火車站的“9288紀念碑”,這里是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終點。西起莫斯科,跨越8個時區,總長9288千米,很難想象這條世上最長的鐵路正躺在我窗前,風塵仆仆,面朝大海。
這座小城的塵土感很重,像極了我國東北以及一些內陸城市,天空多有陰霾,漁港清冷靜謐。本地物產匱乏,街上多是日韓的二手車,滿街走著高頭大馬的白人,神色中卻沒有歐洲人特有的泰然自若。好在山海壯美,風光獨特,像野地里的一顆種子,在這大陸盡頭兀自生長。

俄羅斯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其余城市經濟較一般,更何況我所在的是濱海邊疆區。這里的英語普及率極低,我追著好幾個金發大眼的當地青年問路,發現他們并不懂得除俄語外的其他語言,不像我們周圍的同齡人,至少接受過系統的英語訓練。
夜晚降臨時,符拉迪沃斯托克沿街的咖啡館搖身一變,成了燈光迷離的酒吧。人們紛紛匯集到店門外的路燈下,喝酒抽煙,嬉笑打鬧。他們似乎只有眼前的縱情歡樂,有的人已經喝高了,卻還會掙扎著掏出褲袋里最后幾盧布買一瓶伏特加喝。也正是擔憂這些喝醉的伙計擾亂治安,或是不慎凍死在俄羅斯的寒夜里,當地政府嚴禁便利店或超市在晚上十點后銷售酒精飲料。
戰斗民族的豪情不僅體現在喝酒上,年輕人開玩笑的尺度也很大。我常看見路燈下的俄羅斯人你追我打,當街擁吻,或是對鏡頭做鬼臉。港口夜晚的光暈默許他們揮霍多余的活力,僅僅是聚在酒館外推搡笑鬧,就能讓年輕人心滿意足。有一晚我走在市中心,不巧鞋跟斷了,我一個亞洲女孩拖著箱包還跛了腳,總歸感覺不太妙。果不其然,前頭一幫約莫高中生年紀的當地男孩打量我半天,其中一個掏出黑色頭套罩住臉,又從懷里摸出“槍”朝我走來。我遠遠地辨別出那是一把玩具槍,索性站在原地盯住那少年的灰色眼睛。他憋著笑問我要錢,見我無動于衷,便大笑著扯下頭套,用蹩腳的英文宣判“You are free(你自由了)”,說著跑回路燈下去。我望著這群俄羅斯“熊孩子”,又好氣又好笑。這伙“劫匪”戲弄完我,便鉆進一輛二手車,轟鳴著撞入夜色。
俄羅斯人開車都橫沖直撞,崎嶇的山路也能開出賽車場氣勢,但離奇的是,遇到紅綠燈仍能精準急剎車,交通規則是這群不羈青年為數不多的約束了。來到這里,不僅要提防“熊孩子”開的玩笑,要留神高速行駛的汽車,還要謹慎挑選入口的食物。比如當地人就愛生吃凍咸肉卷和咸魚,再比如俄羅斯的餃子,有奶渣餡、土豆餡,還有藍莓、櫻桃等凍水果餡的……我的好奇心很重,站街邊吃俄羅斯餃子,非要把每種口味都嘗一遍。直到賣餃子的老媽媽笑容可掬遞給我一盒酸奶油,鼓勵我用餃子蘸酸奶油吃,我才徹底敗下陣來。不過并非每道俄羅斯菜都不盡如人意,耳熟能詳的紅菜湯、大列巴、烤牛舌,還有奶香馥郁的冰糕、口味新奇的薯片,都豐盛了此行的美食記憶。
當然,千里迢迢跑到俄羅斯遠東重鎮,我的目的不是品嘗美食或街頭閑逛,而是想親身領略一把馬林斯基劇院的風采。總部位于圣彼得堡的馬林斯基劇院,舊稱“國家歌劇和芭蕾舞藝術院”,集中了俄羅斯最頂尖的歌劇演員和芭蕾舞者,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一家規模不小的分院,卻因地處偏遠而鮮有人知曉,只需一千多盧布便可預訂最好的觀劇位置,折合人民幣才百元出頭。
俄羅斯劇院的著裝禮儀比國內嚴謹得多,女性會換上長裙,將金發高高挽成髻,本就傲人的身材更為高挑纖細。三五個俄羅斯式舊美人從大廳走過,你會疑心自己錯入某個復古派對。從東亞到西歐各國,我對劇場氛圍也算略知一二,但俄羅斯的冷峻感是最顯著的。手袋、古董首飾和婦人緊抿的嘴唇,不大的劇院里游蕩著沒落貴族式的疏離與莊重。
我可以在阿姆斯特丹音樂廳端著果汁和老戲迷們侃大山,可以在東京新國立劇院的簽名墻前扮鬼臉自拍,卻在這個偏遠的小劇院里怯了場,覺得自己一身便裝格格不入,去劇場專用的衣帽間寄存外套時,連頭也不敢多抬。
收納衣帽的服務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特地拍了拍我肩膀,從抽屜里掏出一根粉色絲帶,仔細系在我領口。她面龐略顯圓潤,平添了幾分寬厚諒解,在藝術面前,俄羅斯人的冷峻是可融化的。連續一周,我每晚都出現在馬林斯基劇院門口,佩戴服務生贈予我的絲帶。俄羅斯對藝術的專業與熱忱超乎我的想象,而這份嚴肅態度背后的包容與友善,也令我大為嘆服。無論是白發蒼蒼的婦人,還是買不起禮服的窮學生,或是冒失闖入的異鄉人,走進劇場便同為藝術殿堂的一分子。
那一周,我連續聆聽了四五場普契尼的歌劇。其實看戲的外國人不多,但劇場仍提供了俄英雙語字幕,以便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都能理解舞臺上的故事。不太容易被打動的我,好幾次無聲淚流。這樣一批俄羅斯藝術工作者堅守遠東邊疆,極力呈現每一部經典作品,其現場的張力與感染力無須贅述。那段時間,我每日在旅館樓下的格魯吉亞餐廳啃列巴,摸出幾個盧布坐公交跨過海灣,沿著山路走向馬林斯基劇院,看圖蘭朵、托斯卡、蝴蝶夫人、希爾維亞、睡美人一個個拎著裙擺從我眼前晃過,感慨生活尚有許多未曾經歷的美好。
即將離開這座海濱小城時,我跑到當地一座名叫托卡列夫斯基的燈塔邊坐了會,這是俄羅斯最著名的燈塔,小小的塔臺通過一條狹長淺灘與陸地相連。我在塔下回憶這趟旅程,或許是火車出行的緣故,我身處異鄉卻并無遙不可及的隔絕感。又或許,這塊原名海參崴的土地清朝時曾是我國疆域,雖文化已被徹底異化,但故土本身的踏實感是不會改變的。
坐火車回程的路上,冷湖、荒草、鋼棚、旱廁、日落,熟悉的景象再次劃過眼簾,我愛這遠東的山海,我愿最大限度貼近生活,親吻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