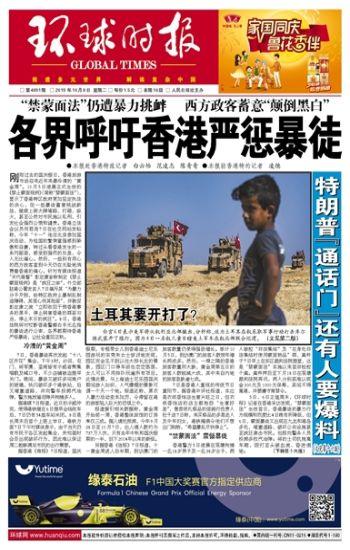如何應對美國將科技優勢“武器化”
封凱棟
從特朗普政府發起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和人才戰,并選擇了部分戰略性高科技領域對華實施技術禁運以來,中美之間是否會“脫鉤”一直是國內熱議的話題。
對于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并不需要刻意強調“脫鉤”對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性。美國在一系列科技領域對中國素有程度不一的限制,根據這些領域過去20年的發展來看,只要中國的戰略路線得當,并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其次,就全球工業技術和科技創新的關系而言,中美之間爆發“結構性”的沖突是大概率的,美國很可能長期地把科技優勢“武器化”,這幾乎不以中國社會渴望合作的誠摯態度為轉移。對此,我的觀點是,我們要做好長期準備,加快中國工業與科技創新知識生產體系的內向整合,中國才能繼續主動利用全球化來推動開放式創新。
美國現在主導的全球經濟體制成形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在軍事和金融上的主導權為其跨國企業的全球資源配置提供了保障。同時,美國也對競爭對手進行戰略性打擊,通過在特定地區、特定產業和特定要素上制造結構性波動來攫取利益,促進其跨國企業優勢的獲得。借助這樣一套體制,美國使得其生產資本和金融資本在全球配置中獲取了巨大利益,并以此部分地轉移了國內的基本矛盾。
當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實現經濟崛起之后,美國日益視中國為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勁對手。雖然中國熱忱地參與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經濟體制,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產業體制和金融體制卻在后冷戰時期表現出全球少有的國家韌性和社會集體意識。這有異于大部分現代國家遭遇二戰后全球化沖擊時所呈現的狀態,即資本與民眾、資本與地區甚至與國家在不同程度下分離的現象。在這些現代國家,資本(和社會精英)往往利用自身的靈活性,脫離自身原本根植于其中的社會基礎,轉向對利益的追逐。一味逐利的金融化資本和各國社會精英的“國際化”異變,既是美國主導的全球體制的產物,也是其主導這套全球體制所需要的條件。
中國的獨特性使得美國不可能利用其主導的全球體制把中國完全消化掉,其金融與軍事主導權也沒能讓中國就范。在這一背景下,保持工業技術和科技創新上的領先,就成為了美國維系其跨國企業主導體系的關鍵武器。
跨國企業主導的全球生產體系,是一套基于技術相對優勢的層級體系。具有技術霸權的系統集成者,通過一套金字塔式的體系在全球配置資源,他們通過資金、技術資本品和管理的投入來獲得對全球范圍內資源、經濟單元和經濟活動的控制權,這種控制權決定了層級體系內具有一種自下而上逐漸增加的回報率分配狀況。
在美國精英看來,中國現在全球技術位置的變化也能挑戰美國整個全球體系的基礎。他們不能接受自身技術主導權逐漸喪失和美國主導的全球體制的動搖。同時,既然技術優勢已經被“武器化”了,那么美國就一定會在這一武器仍然存在而且有效的時候使用,而不會等到武器殺傷力被削弱之后才付諸行動。
面對美國將技術優勢“武器化”,中國工業體系的脆弱性在于,其在產學研三方面的知識生產體系中存在外向依賴。這種外向依賴指的是,被成熟創新經濟體視為核心的“產學研協作體系”在中國的不少產業部門并不存在,中國這些領域的產業和科研部門以國外同行作為主要的技術與知識來源,而沒有以國內產學研的協作來實現知識生產與再生產。
產學研內向整合的缺失,使得中國工業體系缺少了產生基礎性、原創性知識的制度化平臺。這就為美國“武器化”其科技優勢提供了可能性:因為雖然中國已經在工程技術能力和制造能力上實現了巨大的突破,但中國仍然缺乏源源不斷地產生重塑產業技術規范的重要知識的能力。這一問題在半導體、生物制藥、關鍵材料技術等領域都存在。與這一現象緊密關聯的是國內“科技成果轉化難”的痼疾。這一困境是中國后續深化發展的關鍵短板和重大隱憂。面對美國科技戰的威脅,只有建立起內向整合型的工業與科技創新知識生產體系,中國才可能繼續主動利用全球化來推動開放式創新。
這個任務雖然很艱巨,但是時代也賦予了我們機遇。
首先,雖然具有源頭性知識生產機制上的優勢,但美國的制造業基礎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持續衰退,目前已經不再擁有完備的工業體系,在不少領域內甚至已經沒有活躍的制造活動。在缺乏與中國進行產業協作的情況下,這一現狀同樣也會為美國在工業技術和科技創新上的知識生產帶來巨大的困難。當然,美國可以在與中國的對抗中通過重新配置全球的產業活動來部分補齊其知識生產所需的要素,但它也需要付出巨大的轉換成本。
其次,我們現階段正處于信息技術范式的成熟期(即“技術-經濟”長波的第二階段),即關鍵通用技術擴散應用的階段。這一階段側重于技術擴散,尤其是基礎性技術和工程技術創新相比于科學發現和原型技術而言,成本效益更顯著;而基礎科研與產業技術研發結合的重要性相對降低(當然只是現階段相對而言)。這為中國在復雜格局中解決內部結構問題提供了一定的時間。
第三,在相對成熟的技術范式內,競爭的另一焦點在于對未充分開發市場的爭奪,而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未得到充分滿足的單體市場,而且這一市場的潛能已經高度可見。這反過來也會打擊美國跨國企業長期“脫鉤”的意志。同時,即便在那些需要深度開發的新興市場中,即“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中國也已經著手布局。
這些要素都能夠為中國提供足夠的戰略縱深,使得中國有資本邊打邊談,甚至局部打局部談的條件。畢竟相較兩國的發展態勢而言,時間是站在中國這一邊的。當然,即使戰略得當,中國完成工業與科技創新知識生產體系的內向整合,取得科技優勢也將是一條很漫長的道路,我們任重道遠。▲
(作者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