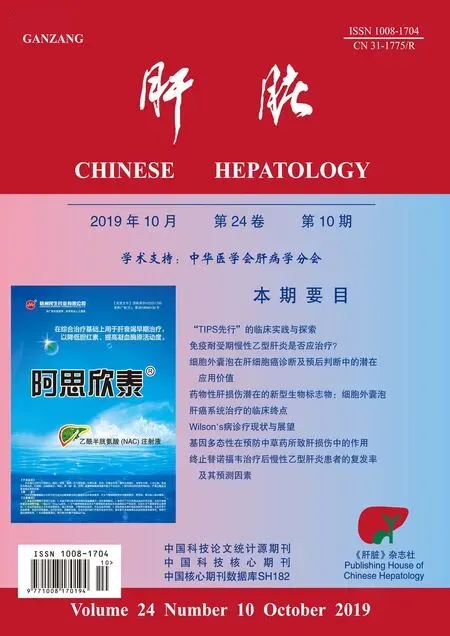Wilson’s病診療現狀與展望
劉晨 楊松
Wilson’s病(WD)是由ATP7B基因缺陷所致銅代謝障礙引起的以肝臟與神經等系統功能障礙為臨床特征的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疾病。1912年,Wilson醫生首先介紹了一組12例以“肝豆狀核變性”為特征的臨床病例;1993年,ATP7B基因缺陷被認定為WD的致病基因。至今臨床醫師對于該病的發病機制與診療已有較為系統的認識,尤其是近年來我國學者在WD領域做了大量工作[1]。
一、WD的發病機制
WD的發病基礎在于ATP7B基因變異。ATP7B是位于細胞高爾基體膜上的銅轉運ATP酶,主要在肝細胞上表達。正常情況下飲食攝入的銅經腸道上皮細胞吸收后通過門靜脈血流轉運到肝細胞的肝竇面,經銅轉運體1(CTR1)轉運入肝細胞。在肝細胞內銅離子與多個分子伴侶結合并轉運到相應蛋白上發揮作用。其中銅離子可經抗氧化蛋白1(Atox1)轉運,將其轉運到位于高爾基體上的ATP7B分子。銅離子經ATP7B轉運入高爾基體后,與銅藍蛋白結合進而分泌到血液中發揮作用。當細胞內的銅增多時,ATP7B可介導銅離子經膽汁排泄。正常人體中約90%銅離子經膽汁排泄。
當ATP7B基因發生變異導致ATP7B功能不同程度受損后,銅藍蛋白結合轉運銅離子的能力不同程度下降或完全缺失。銅離子不能有效地經膽汁排泌,導致其在肝細胞內蓄積,通過氧應激損傷等方式損傷線粒體等細胞器,進而引起肝細胞脂肪變、壞死與凋亡。肝細胞破壞后游離銅釋放入血可引起其他器官損傷。另外,未與銅離子結合的銅藍蛋白在血液中半壽期縮短,導致Wilson’s病患者血銅藍蛋白下降。
現已報道WD相關的ATP7B基因變異已超過500個,不同地域常見的ATP7B致病變異也不相同。歐洲常見的變異為p.H1069Q,印度報道常見變異為p.C271X,而我國報道常見的變異為p.R778L、p.P992L與 p.T935M[2]。需要注意的是,新發現的WD相關ATP7B基因變異需要有相關研究來證實其對于ATP7B結構及功能的影響。
不同變異對于ATP7B基因結構與功能影響程度不同,如截短變異可導致ATP7B基因功能完全喪失,患者可表現為肝功能衰竭;而p.H714Q等變異對ATP7B功能影響較小,導致肝內銅沉積速度較慢,患者多表現為晚發疾病[3]。鑒于WD臨床表現多種多樣,存在肝臟、神經、精神、血液等多系統的表現,有研究試圖確立特定基因變異與臨床表型的相關性。如Usta等[4]報道c.2299insC變異易表現為肝損傷表型,而p.A1003T變異易表現為神經系統病變表型。但總體而言,尚無明確的基因變異類型與患者臨床表型的對應關系。
二、WD的臨床表現
全球范圍內報道的WD發病率約為1/10 000~1/30 000。我國安徽地區的流行病學調查提示WD的發病率約為5.87/100 000[1]。WD臨床表現多種多樣,可累及肝臟、神經、精神、腎臟、血液與骨骼肌肉系統等,其中以前三者受累最為常見。現已報道的WD發病年齡在2~74歲,甚至患者可終生不發病;但大部分患者在5~35歲期間出現相關癥狀。肝臟受累最為常見,患者可表現為單純轉氨酶升高、肝硬化、肝衰竭等表現。神經系統受累常見表現為震顫、強直、肌張力異常等。另外約有10%患者可表現為精神癥狀,包括抑郁、雙向情感障礙等。從性別差異上而言,女性患者發病較男性約晚2年,同時女性患者肝臟受累相對較多,這可能和女性患者雌激素水平等相關[5]。肝豆狀核變性可多系統受累,如可以溶血為首發表現,在臨床上要注意鑒別。
銅藍蛋白是最常用的WD篩查指標。在妊娠、感染等情況下WD患者銅藍蛋白可處于正常范圍。在非WD的肝硬化等患者中也可以出現銅藍蛋白低下。一般血銅藍蛋白< 200 mg/L認為銅藍蛋白低下,對于我國WD患者而言,銅藍蛋白<150 mg/L作為標準診斷WD的靈敏度與特異度分別為 95.6%和95.5%,優于銅藍蛋白< 200 mg/L的標準[6]。就尿銅而言,雖然有研究提示晨尿尿銅也有重要診斷意義,但一般需規范留取24 h尿銅用于診斷與療效評價。總血銅對于患者診斷意義有限,血非銅藍蛋白結合銅對于WD診斷與療效評價具有重要價值,注意在留取血銅時同時抽血檢測銅藍蛋白以計算非銅藍蛋白結合銅。近年來WD診斷的一個重要進展為可交換銅(CuEXC)檢測,CuEXC與血總銅比值> 18.5%診斷WD具有較好的靈敏度與特異度。此外CuEXC還有助于評價WD患者肝外器官受累的情況,CuEXC >2.08 mmol/L診斷角膜及腦受累的靈敏度與特異度分別為86%與94%,而且隨著CuEXC水平的升高,腦受累的概率與嚴重程度也相應升高[7]。
WD患者眼部受累包括常見的K-F環與少見的晶狀體前囊中央“太陽花”樣白內障表現。有相當比率的WD患者可表現為K-F環陰性,所以K-F環陰性不是排除WD的指標。另外K-F環情況還可以用于患者祛銅治療效果評價,隨著長期有效祛銅治療,患者K-F環可減輕乃至消失。隨著肝臟瞬時彈性技術在肝纖維化評價中的應用推廣,不斷有研究探索肝臟彈性技術用于WD患者的肝纖維化評價,如Sini等報道肝臟彈性6.6 KPa可作為臨界值區分輕度與中度纖維化,8.4 KPa可用于區分中度與重度纖維化;Sobesky等[8]報道一組WD肝硬化患者的平均肝臟彈性為(32.3±15.9)KPa。這些結果對于我們評估WD患者病情有一定意義,但考慮到WD患者肝臟病理的多樣性,肝臟彈性檢查用于WD患者肝纖維化評價還需進一步積累證據。頭顱MRI檢查是評價WD患者顱腦受累的重要手段,一般WD患者頭顱MRI表現為在T2與Flair加權相上基底節、中腦與小腦區的對稱性高信號病灶。典型的“熊貓臉征”僅在少數患者中可見,需要注意的是少部分WD患者也可表現為基底節區T2相低信號,可能與WD相關的鐵代謝紊亂等相關。
WD患者肝組織學表現常見脂肪變、慢性炎癥、纖維化等表現,病理表現無特異性。肝組織銅檢測對于WD診斷具有重要價值,這包括肝組織切片的銅染色、肝銅定量等。對于肝切片銅染色而言,臨床上部分確診的WD患者肝組織銅染色可表現為陰性或僅有少量銅沉積,這可能于WD患者本身肝組織銅沉積過少有關,也可能與標本處理和染色方法選擇有關,臨床上不能依據肝組織切片銅染色陰性或較少而排除WD可能性。就肝銅定量而言,歐美指南推薦肝銅定量250 μg/g作為WD診斷的臨界值,但最近Yang等通過大樣本、前瞻性研究提示,采用肝銅定量≥209 μg/g作為臨界值診斷WD的敏感度與特異度分別為99.4%與96.1%[9]。近年來不斷有研究探索肝組織銅等精準定量的方法,如Weiskirchen等報道,采用激光消融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法對于組織銅等微量元素進行精準定量有助于WD患者診斷及療效評價等[10]。
目前WD診斷一般還是依據2001年萊比錫第8屆WD國際會議的診斷標準(表1,通常簡稱Leipzig評分系統)。患者評分≥4分可確診,3分為可以診斷。但如上所述,WD患者癥狀可不典型,血清銅藍蛋白可不降低,可無K-F環,尿銅可不升高,肝組織銅染色也可陰性,臨床患者診斷應綜合患者各項指標進行評價,尤其注意進行ATP7B基因檢測。

表1 WD診斷的Leipzig評分系統
總分≥4分可確診;總分3分為疑似診斷,需進一步檢查;總分≤2分基本不考慮診斷。
注:*如不能進行肝銅定量時采用;ULN:正常值上限。
三、WD的治療
WD患者首先需控制飲食銅的攝入,其次根據患者病情采用祛銅藥物和(或)鋅制劑治療,對于WD相關終末期疾病患者需考慮肝移植。在疾病治療前期需嚴格限制含銅量高的食物的攝入,祛銅劑治療后病情穩定患者對于飲食銅的控制可適當放寬,但盡量避免貝類及動物肝臟等富集銅的食物。
對于確診的WD患者,首選采用祛銅藥物作為一項治療,目前國內外廣泛應用的藥物包括青霉胺與曲恩汀等。青霉胺用于WD治療已有50余年,青霉胺治療前應行青霉素皮試,治療過程中應注意根據銅排泄情況進行劑量調整,初始治療一般患者24 h尿銅排泄>1 000 μg/d,維持治療期間建議維持血非銅藍蛋白結合銅在50~150 μg/L。維持治療期間要避免藥物劑量不足,也應避免過度祛銅引起患者銅缺乏。青霉胺常見的不良反應有過敏(包括遲發性過敏反應)、神經系統癥狀加重、骨髓抑制、腎毒性等。歐美指南推薦曲恩汀等用于WD治療,但國內尚未應用于臨床。鋅制劑作用機制在于腸道內競爭性抑制腸道對于銅的吸收,同時鋅離子可誘導肝細胞金屬硫蛋白表達,增加肝細胞對于銅的存儲能力。鋅制劑可用于無癥狀WD患者或青霉胺不耐受患者的一線治療,或普通患者的維持治療。鋅離子治療有效要求24 h尿銅排泄量<75 μg/d,維持治療同樣要求非銅藍蛋白結合銅在50~150 μg/L。
雙膽堿四硫鉬酸鹽(WTX101)是近年來被認為非常有前景的新一代治療WD的藥物,其作用機制在于結合肝細胞內銅經膽汁的排泄。WTX101在Ⅱ期臨床研究中證實能迅速降低血清非銅藍蛋白結合銅水平,改善患者神經系統癥狀,不良反應輕微,目前正在進行Ⅲ期臨床研究[11]。WD作為一種單基因病變的遺傳代謝性疾病,針對WD的基因治療一直是研究的熱點。ATP7B基因主要在肝臟表達,現有基因治療策略均是靶向導入ATP7B基因在肝臟內特異性表達。按照這個策略分別采用HIV來源的慢病毒載體與腺相關病毒載體轉導ATP7B基因在肝臟表達,在WD的動物實驗均顯示了良好的結果,但目前還處在在動物實驗階段[12]。
WD相關的肝衰竭及終末期肝硬化患者,肝移植是唯一能夠挽救患者生命的治療辦法。WD相關肝移植,一般采用新Wilson指數(NWI)對患者預后進行評價,NWI>11分患者符合肝移植指征。近年來新的預后評分系統如AARC-ACLF 評分系統在WD相關肝衰竭患者預后評價也顯示了良好的預測價值,可在臨床進一步評價后考慮應用于臨床[13]。就WD相關肝移植患者而言,無論兒童與成人,現有研究報道,患者遠期生存與其他病因肝移植患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D患者行肝移植一方面可治愈肝衰竭,另一方面可糾正患者銅代謝紊亂的情況。但由于WD為多系統受累,在WD患者移植前應注意包括腎臟、血液與心血管等多系統情況的評估。對于神經系統病情重、經過祛銅治療后無明顯緩解且肝臟病情尚可的患者,是否可以行肝移植糾正患者神經系統癥狀一直是臨床上有爭議的問題。鑒于早年個案報道提示此類患者肝移植后神經系統癥狀可能無明顯改善甚至惡化,在歐美指南中均未推薦此類患者行肝移植。近年來陸續有報道因神經系統癥狀行肝移植患者在移植后神經系統癥狀改善的情況,有學者提出,對于神經系統癥狀經祛銅治療無改善且患者神經系統無嚴重結構改變的患者可慎重選擇肝臟移植[14]。
對于病情控制良好的育齡期女性,妊娠并非禁忌。Pfeiffenberger等[15]回顧性分析了136例女性282次妊娠的情況,自然流產發生率26%,出生缺陷率3%(7/209)。對于此類患者在妊娠前應充分告知患者有流產與胎兒畸形的風險,并盡可能將病情控制穩定后再備孕。一般建議服用鋅制劑的患者妊娠期間鋅制劑可以不改變劑量;服用青霉胺患者孕晚期應考慮減量以避免過度祛銅導致銅缺乏的情況。服用祛銅藥物的患者應避免母乳喂養。
四、小結
WD臨床表現千差萬別,臨床醫師考慮到WD要盡可能尋找證據,規范診斷。WD可多系統受累,臨床醫師要充分利用多學科診療平臺,除了評價患者肝臟與神經精神系統損害外,還要系統評價患者腎臟、血液等系統損傷,綜合治療。對于WD患者要盡可能做到早診斷并長期規范祛銅治療,盡可能不因WD影響患者壽命;對于疾病終末期患者應綜合評價病情后考慮肝移植及康復等治療,盡可能挽救患者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