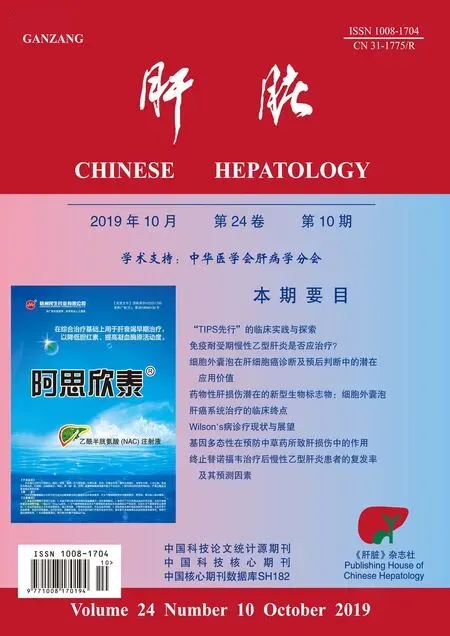肝硬化繼發肺炎克雷伯桿菌肝膿腫1例
王騫 陳維順
患者,男性,68歲,因腹脹伴咳嗽、咳痰、發熱1周余入院。患者于入院1周余前因受涼開始出現腹脹,伴畏寒、發熱,同時有惡心、嘔吐。既往在外院診斷為“肝炎后肝硬化”,并行“脾切除術”。否認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不飲酒,抽煙40余年,1包/d。
入院查體:體溫:39.5℃,脈搏:121次/min,呼吸:21次/ min,血壓:137/77 mmHg。慢性肝病面容,神志清楚,精神欠佳,計算力下降,呼吸肝臭味。左肺可聞及干啰音,左上腹可見一25 cm陳舊手術疤痕,可見腹壁靜脈顯露。全腹無壓痛及反跳痛,無腹肌緊張,未觸及包塊,肝區無叩擊痛,移動性濁音可疑陽性。
實驗室檢查:血常規:HB 122 g/L、WBC 10.78×109/L、N 78.50%;ESR 91 mm/h;CRP 183.60 ng/L;PCT 3.43 ng/mL;肝功能:Y-谷氨酰轉肽酶100.0 IU/L、ALT 53.0 IU/L、AST 77.0 IU/L、白蛋白25.7 g/L;HBV血清標志物:乙肝核心抗體(+)乙肝表面抗體(+),余陰性;腫瘤標志物、自身免疫性肝炎抗體均(-);影像學檢查:肝膽脾胰及腹膜后淋巴結B超:肝實質彌漫性病變。胸片:兩下肺少許感染灶。
診療過程:入院診斷肺部感染、肝炎肝硬化合并肝性腦病(前驅期)。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抗感染、護肝、治療肝性腦病等治療后患者肝性腦病逐漸好轉,肺部啰音減少,但仍反復發熱,最高體溫39.8℃。血培養提示肺炎克雷伯桿菌,血常規白細胞繼續升高(WBC 17.89×109/L),診斷為膿毒血癥。根據藥敏結果改為美羅培南(0.5 g,1/8 h)+甲硝唑+左氧氟沙星抗感染,之后患者熱峰下降。完善腹部CT提示肝右后葉低密度灶:1.考慮感染性病變,肝膿腫可能性大,2.門脈右支內充盈缺損,考慮栓子。復查腹部B超提示肝內低回聲灶:性質待定。大便蟲卵(-)。外科考慮病灶液化不全,不宜穿刺引流。患者反復發熱,肝功能較前惡化(ALT 108 IU/L、AST 122 IU/L),經多科會診后調整用藥為亞胺培南西司他丁(1.0 g,1/8 h)+甲硝唑+左氧氟沙星聯合抗感染,2 d后患者即未再發熱,治療第8天復查:血培養(-);血常規正常;腹部CT提示肝右后葉片狀低密度灶較前縮小,考慮肝膿腫治療后較前改善;將抗生素逐漸降級直至停藥,期間患者無發熱,復查CRP、PCT逐漸恢復至正常,轉氨酶輕度異常,患者出院。

圖1患者首次腹部CT,肝右后葉可見片狀低密度影,邊界欠清,呈蜂窩狀改變

圖2治療后復查腹部CT,可見右后葉低密度影范圍明顯縮小,密度增高,病灶吸收
討論以往研究認為細菌性肝膿腫的病原菌主要是鏈球菌和大腸埃希菌,而1980年于臺灣地區報道了第一例肺炎克雷伯桿菌性肝膿腫后,肺炎克雷伯桿菌逐漸成為東亞地區肝膿腫首位病原菌[1]。肺炎克雷伯桿菌為革蘭陰性桿菌,存在于正常人呼吸道及腸道中。當機體免疫力下降或長期使用抗生素導致菌群失調時可引起機會性感染。莢膜多糖是主要致病因子[2],根據其抗原性不同,可分為82種血清型,其中以K1、K2兩種血清型菌株侵襲性最強,也是中國大陸地區肺炎克雷伯菌肝膿腫的主要致病株[3]。
分析該例肝硬化患者發生肝膿腫的主要原因:(1)肝硬化后肝血流減少,肝內庫普弗細胞保護能力下降,單核-巨噬系統、中性粒細胞及補體系統功能受損,導致局部及全身免疫力下降。同時患者脾切除后免疫屏障功能缺陷;(2)肝硬化后小血管破壞,肝動脈供血不足,同時患者門脈右支栓子形成,影響門脈供血,使病變處血流更少;(3)肺部感染繼發膿毒血癥,成為感染來源;(4)低白蛋白血癥進一步導致了機體抵抗力的下降。
肺炎克雷伯菌肝膿腫主要臨床特征:(1)多有肺部感染等其他感染源存在;(2)患者多為中老年人,男性多見,糖尿病是最為重要的易患因素;(2)臨床表現多不典型,腹部癥狀的發生率較非肺炎克雷伯桿菌肝膿腫要低;(3)對于肝硬化患者,由于大量肝細胞被纖維組織替代,肝血流減少,感染后肝膿腫形成晚,且不易形成液化,容易影響肝膿腫的早期診斷;(4)CT特點為多單發、多房、實性、膿腫壁薄、膿腫周圍無強化、多伴血栓性靜脈炎及遷徙性感染灶[4-5]。
本例診治經驗:對于持續發熱的肝硬化患者,應積極尋找感染源,根據細菌學結果調整抗生素,對于克雷伯桿菌肝膿腫,首選碳青霉烯類;治療效果不佳時應及時更換抗生素,本例亞安培南優于美羅培南的可能原因:(1)兩藥結合靶點不同;(2)亞胺培南殺菌速度更快,起效時間更短。(3)美羅培南使用劑量不足,病灶血藥濃度低,殺菌效果欠佳;對于直徑3 cm以下單發或多發肝膿腫、早期尚未液化完全病灶應用抗生素治療效果尚佳,而直徑3~6 cm者應將B超/CT介導下肝穿刺排膿作為首選治療方案[6]。因此,對于肝膿腫特別是肝硬化合并膿腫患者,治療方案需多學科協作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