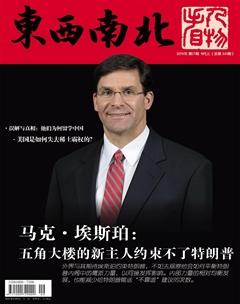誤解與真相:他們為何留學中國
羅幸 陳光

2008 年10 月26 日,北京大學百年講堂廣場,中國學生和外國留學生一起聯歡。
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美國學生馬修自己住在一間如酒店般的宿舍里,享受足夠的個人空間。每天,他在舒適的床上醒來,拉開窗簾,走到獨立衛生間洗漱。站在窗邊時,他能看到對面的宿舍樓。四個和他同樣攻讀碩士學位的中國男生住在一間屋子里。他們住在上鋪,下層是書桌和生活用品。他們每天從床上爬下來,穿過散落著臉盆和水桶的狹窄過道,抓起牙刷和杯子,走出房門,到這一層的公共衛生間去洗漱。
在中國高校,“留學生公寓”存在諸多例外。當中國學生過著4到8人的集體生活時,留學生們卻能享受舒適得多的住宿環境——兩人合住已是居住密度的極限。除此之外,空調、冰箱、微波爐這些中國宿舍里的“稀罕物”,在很多留學生公寓幾乎是必備品。投入再多些的高校,會修建面向留學生的游泳館、健身房、臺球廳、KTV,北京大學中關新園留學生宿舍甚至還有保齡球館。
這些顯而易見的對比,加上“入學條件更寬松”“獎學金唾手可得”等傳言,使得網絡上質疑留學生“超國民待遇”的說法大為流行。再搭配上一些留學生愛逃課、拿著政府獎學金“花天酒地”、只想著戀愛交友等故事,更是增加了中國網友們對留學生的不滿。
矛盾在這個7月爆發。山東大學的“學伴”風波,成為這種不滿情緒的一次集中爆發,各種真假莫辨的消息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為留學生提供“超國民待遇”的高校更是被指責“崇洋媚外”。
情緒裹挾下的網絡討論中,似乎很少見到留學生們的聲音。他們到底為何來中國留學?他們在中國的真實生活到底是怎樣的?面對高校的留學生政策,他們是否也有自己的無可奈何?事實上,在華留學生問題,遠比宿舍條件的對比要更為復雜,它不但牽涉到高校的國際化、全球排名,更與吸引人才、傳遞中國國家形象等問題相關。在留學生問題上,中國做得不是太多,而是還不夠。
不過,這場風波以及伴隨而來的憤怒情緒,至少準確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號:我們對周圍留學生的生活,知之甚少。
“超國民待遇”的另一面
馬修在北大攻讀的是燕京學堂中國學碩士研究生。自2014年5月成立起,圍繞燕京學堂的爭議從未停止過。其中,“超國民待遇”培養幾乎是貼在該項目上最顯眼的標簽之一。
這個一年制項目同時面向國內和國際招生,獎學金豐厚——除了學費、住宿費皆免除外,學生每月還能收到生活補貼。其中,來華留學生及港澳臺學生占到近七成。
燕京學堂教學辦公地點坐落在北大校園的黃金地帶——靜園,屬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燕京學堂研究生不分國籍,統一住在勺園6號樓,分為單人間和雙人間。它的對面是勺園4號樓,用作北大本校研究生的宿舍。
留學生宿舍條件雖好,但常為人忽略的一面是:住宿費很貴。
24歲的鄧世軒很早之前就已經搬離了北大留學生宿舍,和朋友在校外一起租房住。鄧世軒是一名馬來西亞華人留學生,目前在北京大學攻讀國際關系研究生學位。
搬離留學生宿舍前,鄧世軒算過一筆賬,北大的中國學生宿舍價格每年在650元到1000元不等,而兩人間留學生宿舍,每人每月得花2400元,一年就是2.8萬多。單人間價格每個月又要貴上600元。對于沒有獎學金的他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張端鴻在《來華留學生教育為何難以實現管理趨同化》一文中提到,中外學生住宿條件、價格的差異,是由于二者經營性質不同導致。公辦高校的中國學生宿舍屬于普惠性、保障性的廉價住宿服務,就條件而言不夠理想,而留學生公寓屬于準商業性質,價格也就隨著住宿條件走高。
“中國學生覺得我們有特殊待遇,其實,如果給我選擇的話,我可能會考慮跟他們一起住。”鄧世軒說,只是學校沒有給他這個選項。在中國很多高校,中國學生與留學生的生活、日常管理都是分開的。在他看來,這就失去了與中國學生接近并熟悉的機會。針對這個問題,他曾特地咨詢過學校的留學生辦公室,得到的答案是根據“相關法規政策”規定。
住宿的分開管理,只是中國針對留學生“獨立管理模式”的一個側面。由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院長劉寶存主持的研究項目“在華留學生管理現狀及改進對策研究”中解釋道,國際上接受留學生數量較多的歐美院校,一般都會對留學生和本國學生進行無差別管理模式。中國高校一般對外國留學生與中國學生管理實行“兩條腿走路”,對留學生采用“特殊照顧管理模式”。
這一方面是考慮到漢語并非全球通用語言,對留學生來說學習難度大,統一管理門檻較高,加之考慮到留學生的不同生活習慣和宗教問題,所以采用留學生獨立管理模式。但這種模式不利于來華留學生融入中國大學生活和學習。

另一篇論文《來華留學生趨同化管理研究與分析》則指出,國內高校一般由國際教育學院獨立負責留學生招生、教務、管理和后勤等工作,但其他管理機構,包括教務處、后勤處等部門在留學生管理上權責關系不明確,留學生事實上無法在校內資源、職能部門的管理等方面與中國學生享受同等待遇。
“大部分留學生的狀態,偏向放養。”曾在廣東省某高校擔任過輔導員的林藝說。
在北大燕京學堂讀書的馬修情況要好一些,留學北大前,他曾在中國生活過兩年,燕京學堂中外學生上課、住宿都又在一起,融入感相對要好很多。
即便如此,他仍然會遇到很多現實問題。第一學期選課時,他操作失誤,多選了一門課。那時,他中文還不太好,但北大選課系統上只有中文。由于不知道自己選了那門課,在接下來的一個學期里,他從未上過課,直到期末才發現成績單上有一個“不合格”。
娜娜也比較幸運,到復旦第二天就認識了一個本科生朋友,后者熱心地給了她一張校園地圖,并陪同她穿梭在不同教學樓之間。“要是沒有她的話,我真的完蛋了。”回想起那時不知該向誰求助的迷茫,娜娜說,“我不知道其他留學生,尤其是不會中文的留學生,能怎么處理這個問題?”
事實上,學伴制度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而設立的。“我們設了學伴制度,就是為留學生融入中國提供了一個橋梁。”林藝說,這是一項好的制度,不止山東大學,國內很多高校都有這種設計,一般會給參加的學生一些補助或者算學分。
為何要留學中國?
作為“第三代”馬來西亞華人,鄧世軒留學中國前,已經有一定的漢語基礎。在馬來西亞公立學校,漢語本是教育體系的一環,一些華人還會選擇去民辦華文中學就讀。
在華文中學時,鄧世軒接觸到中國歷史并產生濃厚興趣,決定本科要來中國攻讀歷史學。恰巧一位在北大學習國際關系的學長回高中做分享會,介紹在北大學到的知識,還談到很多學者都會去北大講座,這些都對他產生巨大的吸引力。
對于一些留學生來說,“排名”并不是選擇學校的第一要素,相比之下,自己的興趣、項目內容更加重要。越悅在外交學院一個負責接待留學生的學生會組織工作時,遇到一位來自克羅地亞的男生,“明明是申請哈佛、耶魯的水平,偏偏來了外交學院,還是自費”。越悅說,這是該學生瀏覽各個學校項目后做出的選擇。這個男孩隨后憑借自己出色的成績拿到北京市政府獎學金。


當然,這些只是個案。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除港、澳、臺學生,2018年共有49.2萬名留學生來華讀書,這些學生來自196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為何要到中國來讀書,原因很難一概而論。
高等教育研究領域的主要國際期刊《高等教育》上曾刊登了一篇由Jiani撰寫的論文:《國際學生為何及如何選擇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論文中,Jiani的研究樣本來自28個國家的23個女生和19個男生,在問及他們來華留學的原因時,有人像鄧世軒一樣,出于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也有人是海外華人子女——Jiani發現,越來越多海外華人希望子女回歸中國接受高等教育,尋找文化認同。也有學生是考慮到中國留學的性價比。
娜娜選擇來中國,也是出于對中國文化的喜歡。但曾在英國讀本科的她也承認,“英國學校肯定要比中國學校貴多了”。據她介紹,自己在復旦讀書,每年學費2萬元,住宿費1萬,但如果在英國,住宿費可能是七千多英鎊(約合人民幣6萬元)。
除了個人原因,也有共性。接受Jiani訪問的大部分留學生都提到了中國的快速發展,他們認為來華留學可以為其帶來更好的工作前景,尤其是能夠學習漢語,成為其來華的一個重要原因。Jiani發現即便來自發達國家的留學生,也非常看重中國提供的獎學金。
留學生基金委官網顯示,中國政府獎學金覆蓋面包括學費、住宿費、生活費和醫療保險,本、碩、博三個學歷層次的資助金額各分為三類。其中,本科生的年資助總額最低為59200,最高66200元,研究生在7-8萬之間,博士和高級進修生能拿到每年87800-99800元的資助。
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的49.2萬名來華留學生中,12.81%的人獲中國政府獎學金,87.19%為自費生。雖然后者還有機會獲得其他類別的獎學金,如省、市政府獎學金,孔子學院獎學金等。
獎學金制度是高校吸引留學生的國際通行規則。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一份排名,美國前20名的綜合性大學就讀的國際學生中,有41.5%的人獲得獎學金,而在排名前20的文理學院中學習的國際學生,有73.3%的人獲得了獎學金。當然,因為教育體制不同,美國高校獎學金多為學校發放,中國高校對留學生發放的獎學金則來自各級財政。
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院長劉寶存主持的“在華留學生管理現狀及改進對策研究”課題中認為,雖然中國政府每年都在增加獎學金名額,但所占比例較低,并且整體呈下降趨勢。“我國政府獎學金的制定是根據與有關國家之間的教育協議和交流計劃,因此更多強調的是其政治功能,基本上是向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提供獎學金。”該項目組認為,此外,留學生獎學金制度還存在資助力度低、來源渠道單一等問題,長期來看,這不利于吸引海外優秀學生。
五十萬留學生之現狀
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田方萌此前在北大和北師大教授留學生公共政策分析課六年,學生大部分來自非洲。他的課堂較為西化,以討論為主,用的語言為英語。
相比之下,歐美學生對中國擁有較強的好奇心,對中國的了解程度總體深一些。另一方面,盡管英語在許多非洲國家是官方語言,但非洲留學生的數學、英文寫作等能力都要比歐美學生落后一些。
剛開始,田方萌并不了解班上留學生的水平,沒有設置期末考試,以書評和論文的方式考核,結果發現有些學生交上來的文章抄襲嚴重,從網上東抄西抄。改成考試后,他發現“開卷考試有的學生都答不對”,效果和自己想象差別比較大。經過幾輪調整,他才慢慢摸到出題難度的邊界,最后采用考試和論文相結合的考核方法。
田方萌承認,非洲學生里也有優秀的個體,“三分之一我覺得功課是比較好的,上課也很認真,還有三分之一馬馬虎虎”,剩下三分之一相對較差,寫出來的文章邏輯層次不清、語病較多,有的老師“都恨不得替那個學生寫出來”。
劉寶存主持的“在華留學生管理現狀及改進對策研究”課題中也注意到,在建設一流大學和高校教育國際化的背景下,中國一些高校一味追求規模擴張,政府公布歷年來在華留學生統計數據時,也總是把留學生規模較大的單位排在前面;教育官員講話時,傾向于把接受留學生數量多的高校作為范例來進行介紹。教育部也曾提出把接受留學生數量作為考核重點大學的基本指標之一。然而,“量”的提升對“質”的監控也提出了挑戰。
2010年,教育部出臺《中國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其中提到,到2020年,中國要“建成一批國際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學校,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
影響高校國際排名的要素之一,便是國際學生比例——國際權威排名里,來自英國的QS和美國的US News都把這一點納入排名算法中,兩者各占5%。由《泰晤士高等教育》制作的排名則給予國際學生比例2.5%的權重。
決策機構對國際化的重視體現在教育部在2010年發布的《留學中國計劃》里,其中提到,2020年時來華留學人員應提升至50萬人——從2018年的數據來看,這個目標已基本實現。
田方萌認為,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過分重視留學生數量而忽視其質量。“中國目前階段吸收不了一些國家的一流學生,歐美有些大學是可以做到的。這個情況下你就只能錄取二三流的學生。但問題是,二三流的這些學生不僅不如美國或者英國的留學生,而且也不如中國自己的學生。
北京市一所雙一流大學的教授接受采訪時說,校內一些中亞學生不僅能力差,還愛逃課,而有關部門的精神又是“照顧這些學生”,導致這些學生被寵壞了,有時讓自己不堪其擾。
在林藝看來,盡管住著條件相對較好的宿舍,獎學金門檻相對更低,學校也經常組織一些面向留學生的旅行活動,但教學方案設計和學業管理上的缺失,使得這些留學生很可能難以如期完成學業。
? ? “媽媽看,外國人”
在中國期間,來自亞洲之外國家的留學生總是能感受到來自身旁的注視。在超市,有小孩會指著娜娜說,“媽媽看,外國人!”天性開朗的她會哈哈大笑,“那些小孩真的好可愛”。馬修一度對這種關注有點困擾。等地鐵的時候,他能聽到身旁的女孩兒用中文討論自己的身高、國籍,娜塔莉的體驗要更糟一些。她發現,走在路上的時候,常有人偷拍她。

2012 年12 月8 日,杭州,兩個留學生在浙大校外一家咖啡館復習漢語課程,這是留學生常去的一家咖啡館,墻上用各國語言寫滿了留言。
雖然1949年新政權成立后,中國很快就開始接受外國留學生,也陸續派留學生出國深造,但中國社會與外國人的接觸程度,整體仍然偏低,同樣,外國人對中國的認知程度,也并不是很高。
在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看來,擴大吸引留學生來中國讀書,是增強彼此了解的一個重要方式。“相對來說,培養人才確實是很長遠的。”周永生認為,隨著中國的發展,與國際的聯系越來越密切,而想要擴大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讓國際上更了解中國,培養留學生是“成本更低,影響更深遠”的一種方式。
雖然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三、亞洲第一大留學生接收國,但與排在前面的美國、英國相比,仍然有不小差距。據2015-2016的統計數據,美國東北大學國際生比例達到58.69%,哥倫比亞大學國際生比例是48.84%,而清華大學截至2017年12月31日,國際生比例僅為6%。
所以,問題不是來華留學生太多了,而是交流程度和管理水平還不夠。
中國教育部門也意識到了學生管理上的一些問題。7月20日,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負責人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教育部將進一步推動來華留學生與中國學生的管理和服務趨同化,加大力度敦促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將政策落到實處。
(肖春萌薦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