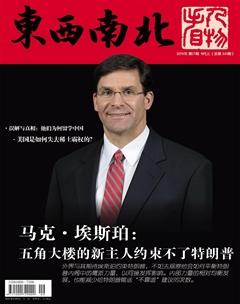洋化樓盤,資本為什么要做一件“蠢事”?
陳光

近日,浙江溫州的“曼哈頓小區”改名為“曼哈屯”,“歐洲城小區”改為“矮凳橋小區”,洋氣的樓盤名瞬間畫風突變,引發網友熱議。
為落實民政部等六部委去年底發布的《關于進一步清理整治不規范地名的通知》,海南、浙江、陜西、河北、廣東等地近期紛紛開展針對不規范地名的清理整治工作,在各種存在“大、洋、怪、重”的不規范地名中,房地產樓盤名的“洋化”問題突出。
地名亂象已是屢治不改的老問題。其中,房地產樓盤的命名更是集資本邏輯、消費心理與地方政府行政水平為一體的典型代表。改與不改,這些名字都已成為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真實寫照。
刻意營造出的美好幻象
為了買房,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潘祥輝教授逛過不下百家樓盤。在各種房地產廣告的“圍攻”下,他發現房地產商在營銷中,埋伏著眾多“語言陷阱”。
除了在各地常見的“威尼斯水城”“巴洛克花園”等小區名,南京還有不少像羅托魯拉小鎮(源自新西蘭旅游勝地)、阿爾卡迪亞(源自希臘神話里的世界中心)等拗口的洋名樓盤。
“樓盤名是最外觀的包裝,我覺得這種包裝其實也抬高了樓市價格,是樓市水分的來源之一。”潘祥輝說。
據網易房產數據庫2017年對中國137個城市的五萬多個項目名梳理顯示, “國際”和“中心”是中國地產商最喜歡的詞,共出現3116次和1362次。外國地名中,“巴黎”最受歡迎,其次是“威尼斯”“歐洲”“羅馬”“維多利亞”“凡爾賽”“香榭麗舍”。
杭州樓盤名稱的歷史變遷也是全國的縮影。潘祥輝發現,上世紀80年代,“街道或地名+新村”的命名方式是杭州樓盤命名的主流,樓盤主要服務于普通市民的“剛需”有關。
1990年代,房地產業開始迎來大規模的商品化階段,出現了大量以“苑”為通名的樓盤案名。進入2000年,杭州逐漸告別“平民化”的房地產時代,房子開始成為一種“奢侈品”。表現在樓盤命名上,名稱也日益“奢侈化”。“村、弄、區、巷、家”變成了“灣、庭、郡、居、府”,頗有古代大戶人家的感覺。
2010年以后,樓盤名越來越“高大上”。潘祥輝寫道,“此時的樓盤名早已超出了指稱功能,而是越來越具傳播功能,突顯品質、檔次、身份與意境。”
事實上,地方政府對商品房命名也有明文規定。2000年出臺的《杭州市住宅地(區)名稱及大型建筑物名稱管理辦法》規定,若以“花園”作為通名的房地產項目,規定建筑面積必須在2萬平方米以上,綠化面積必須占總用地面積的40%以上。但規定并未限制住樓盤起名中的虛假宣傳。
“洋地名興起的現象可以說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與中產崛起的結果。”界面文化指出,中產群體對身份地位更敏感,“階層區隔意識”不斷提高。
文章引述《格調》一書中美國文化批評家保羅·福賽爾的觀點指出,對階層區隔非常敏感的美國中產相信,英國和歐洲才是上檔次的。
法國社會學家讓·鮑德里亞也指出,在消費社會,人們更多的不是對物品的使用價值有所需求,而是對商品所被賦予的意義以及意義的差異有所需求。人們通過消費物的符號意義而獲得自我與他人的身份認同。
過去幾十年,各大城市幾乎成了高檔樓盤名稱的試驗田。這也引發了政府的“焦慮”。
被壟斷的命名權
其實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早在1996年,民政部發布的《地名管理條例實施細則》中,就有“不以外國人名、地名命名我國地名”的規定,但其中“地名”多指的是自然景觀、行政區劃、公共建筑等,并未將私屬領域的酒店、房地產樓盤等涵蓋在內。
“樓盤命名權基本都被開發商壟斷,在項目開發建設之前就先行確定了樓盤名,購房人取得房屋產權后亦無權對樓盤名稱進行變更。樓盤產權人無權對開發商命名進行更改,已是普遍存在的現實。”在2013年的一波地名整治中,人民網評論道。
根據規定,開發商在開發房產時,樓盤命名需向政府有關部門備案,接受地方政府監管。但現實中,樓盤登記名與實際宣傳名不相符的情況時有發生。
一位地產營銷公司負責人介紹,項目宣傳案名與實際登記名稱的差異,在過去其實是常態,且基本無人監管。業內普遍將此認定為廣告營銷的范疇,只要符合工商規定,就問題不大。
潘祥輝在文中指出,作為利益共同體,地方政府實際上也沒有強大的動力對此進行監管,因為房地產商的利潤和政府的稅收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這種泡沫之上。
“如果我們聯想到房地產商強大的政府公關能力,他們想取什么名字大概是自己說了算,誰會為難他們呢?”潘祥輝說,“房產命名為什么要政府審核,這是基于它的公共性和外部性。我認為是政府有關部門失職了。”
復旦大學的歷史地理專家葛劍雄教授在近期接受媒體采訪中也指出,知道一些地方的命名是房地產商公關的結果,中間是否涉及腐敗,值得調查。一些本已被通知整改的地名,后來反而通過了,有關部門應反思。也有一些地方是為了招商引資,想以洋名展示一種開放的態度。
不過,近些年,政府官員對洋名的態度也有所變化。
“國家現在要文化自信嘛,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化,在中國的領土上叫這些洋地名合適不?這不是傷民族的感情嗎?在外國干嘛不叫中國的地名啊。”海南省民政廳辦公室一名工作人員說。
界面文化提到,國家對洋地名的焦慮,實質上是對附著其上的象征性符號的焦慮。它打破了以國家為主體的意義壟斷,將“外國的”定義為“更好的”“值得追求的”,損害了國家尊嚴。
媒體報道顯示,從2008年起,“中國化”的樓盤越來越受歡迎。也有業內人士表示,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靈感,將是國內樓盤命名的大趨勢。
在這種樓盤命名的轉型期,催生了六部委發布的地名整治通知,強調要科學合理確定不規范地名清單,確保地名總體穩定。
但各地施行中,還是出了一些“打擊面過大”的問題。
葛劍雄提到,有些地方政府名義上是向專家“咨詢”地名整改,但大部分時候早已定好了,只是讓專家去“背書站臺”。不少情況是主管部門“自己拍腦袋決定,沒充分考慮公眾和專家的意見”。
“如果不能按照令人信服的邏輯推進,如果不能按照合法依規的程序落實,那么就容易引發物議沸騰。” 《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號俠客島在《小區因“崇洋媚外”改名,好經不要被念歪了》一文中寫道。
若魯莽改名,房本、戶口本,和身份證上的名字是否也要改?城市地圖、路牌、工商登記信息等一連串的更新,成本誰來承擔?
面對來自企業、媒體、學界的質疑,民政部6月21日發布消息表示,個別地方存在政策標準把握不夠準確、組織實施不夠穩妥等情況,要準確把握政策,嚴格按照有關法規和原則標準組織實施,防止隨意擴大清理整治范圍。
“房名和人名一樣,每個年代都有每個年代的命名。有些命名本身無所謂對錯,它體現的是社會文化心理的時代變化。”潘祥輝說,“如果我們的社會心理足夠成熟自信,恐怕一個名字不用改來改去,而過度包裝這樣一種策略或現象自然就會失效、消失。”
(楊洋薦自《讀報參考》)

2015 年12 月17 日,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一處名為“城市維也納”的樓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