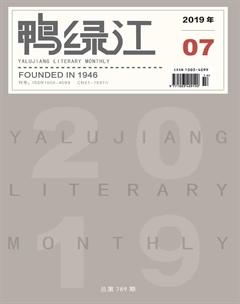嚴歌苓《老師好美》的敘述特色
“嚴歌苓小說的敘事視角具有靈活多變的特點,并常常根據小說情節、主題的需要,選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人稱交錯敘事。嚴歌苓的這種敘事方式,可以讓讀者超越敘事人稱的單一性,獲得較為廣闊的視野。”《老師好美》全篇小說分章進行,一共二十九章。整篇小說,作者在用不同的人物的口吻來談及此事。小說的開篇,表面在用檢察官的聲音和類似于旁觀者的人的眼睛在放映著事情的結果,實則揭開了故事的篇章。作者用檢察官的口來敘述案情“就是這個男中音把被告席上少年情殺者的壯烈故事講得平鋪,無關痛癢”如作者所寫,這是在用具有權威性身份的人的話來證明事實的真實性,切斷臆想,事實如此,不可更改,不存在口傳與事實大相徑庭的情況,給人一種沉重的心理感受。利用旁觀者的眼睛來看站在庭上的少年的樣子,無關乎對被告方的痛恨,對被害方的掩飾同情,客觀詳實,“少年瞪著眼,似乎無奈地陪著眾人把檢察官的陳述聽下去”,樣子描寫入木三分,將這一冷情少年與他所作出的殘酷的行動吻合。作者開篇就用這鐘敘述方式來講著悲劇,冷漠中的悲劇,已經為文章奠定了悲傷這一主調。而第二章開始至以后,作者筆鋒一轉,換作以故事的主導者—丁佳心的口吻來進行敘述,然后又是旁觀者的口吻講故事,這兩種口吻相互轉化,直至小說的結束。
綜合整個小說,作者用了三種人的口吻來寫,“我希望每個人物都作為犧牲者,也作為犧牲他人者,同時顯示出自己行為、心理的正當正義性。所謂一個人的真理可能是他對方的謬誤,各說各的真理,各有各的道理,各自堅持的真理殺害了也自認為持有真理的他人,一個人以為她出去的是愛,卻毒化了她愛的對象,所以用三個角度來敘述比較好。”這是嚴歌苓自己對這種敘事方式的解釋。丁佳心的口吻,不似法官和旁觀者那樣的平靜,她飽含著各種情緒:深情、擔憂、惆悵、后悔和自責。回憶往事時,她總是稱劉暢為“暢兒”、“我的暢兒”,稱邵天一為“天一”、“親愛的天一”,屬于他和她,他和她之間的稱呼,親昵而又深情。作者筆下的丁佳心,沒有用老師和學生之間的稱呼,正如他們對丁佳心的稱呼“心兒”,而這正體現了作者那種獨特的情感表現方法,就用稱呼來印證著他們三人之間的感情的不平常,脫去了淡漠和疏離的客觀稱呼,這遠比劉暢和邵天一的那句“我喜歡丁老師”表現更加直白。有一種“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效果,兩個男孩對于老師的喜歡和愛總是在言語中表現,覺得說出口的愛意更加深厚。而丁佳心,因為是作為一個語文老師的緣故,已經過了少女般熱戀的時段,內斂含蓄,但是也難掩情意。
作者的出色之處就是會運用女性那種細膩的感情與精細的筆觸,借助文字這一工具,將丁佳心、劉暢和邵天一之間相處的日常點滴進行描寫,寫出了一段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的感情。正如邵天一所表達的那種愿望,他希望自己考個好大學,給自己的丁老師最好的一切,然后他們生活在一起。在我看來,嚴歌苓在這部小說的創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她將她自己在小說中的安放位置—兩種人的附體,丁老師和旁觀者的附體。一會兒她是丁佳心,一會兒她是旁觀者。她是丁佳心,就與小說中丁佳心口吻來敘事一樣,情感波動大,帶著對兩個男孩的關愛與依戀。她是旁觀者時,她目睹著劉暢進入監獄的場景,她就像是一個現場直播的記者,把畫面直接切換到了囚室,無生命的氣息充斥著整個空間,還有他身上那件可以被嗅出無情的非人的干凈的味道的衣服,一種毫無掩飾的死刑犯的生活的描寫。這種敘述方式的作用,就在于較好地控制了情感與理性的融合,不是一味的感情泛濫,不會將心痛與惋惜等心情充斥全本小說,而忽略了事情的真實真實狀況與氣氛的營造,理性節制感性,達到平淡無情的敘事中流淌著心碎的效果,這種對心理的穿透力與震撼力更強。
這三人之間的戀情,以及他們三人之間的相處模式,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不光是日常的語言交流,而且還加入了網絡用語520(我愛你),880(抱抱你),30(想你),130(也想你),這也是作者的另一種敘述特色。作者此時就為他們創造了短信這一虛擬的世界,只有語言的交流,在虛擬的世界中數字化地表達著真實的情感,作者此處的構思與他們的感情給人們的感覺不謀而合。網絡用語,也十分符合兩個高中生的學生身份,叛逆的年齡段總是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也做出與年齡相符的事。而丁佳心隨著他們一起玩轉網絡用語,一方面映射出她的年齡與她的心態無關,她依舊對新的事物充滿興趣,包括了對處于新的綻放的年齡段的男學生產生興趣,于是開啟了一段三人之間的師生戀;另一方面,她的思想可以與時俱進,所以她與男學生的相處并沒有格格不入,而是一拍即合,感情升溫。
因此,作者在小說中對此種語言的運用,巧妙地對于表現人物的特征和感情的表現做了透視,而且本篇小說講述的本來就是一個悲傷的故事,加入一些網絡用語,為沉重的氛圍添一些俏皮。整個故事的結果就是三個人都不再存在,被殺害者、殺害者、女老師,他們的感情也隨之消失。所以,文中選擇短信交流也突出了一定的優勢,短信可以為他們提供見證,短信,短的信,作者也可以借此表達小說的主題:短,時間短,感情短。信,三個人之間的信。短信,短的時間的短的感情的結果,也是故事的結果“斷信”。足以見得,作者創作構思時那種與眾不同的想法,尤顯女作家心思的縝密。丁佳心作為一名語文老師,本就是對于語言的使用極其考究,而她與學生間交流所使用的網絡用語,顯出了她與一般老師的不同的體現,是她主導并參與了這一場三角戀。
作者在語言方面的作用,集中體現在以下幾點:符合“人類總是對未知的世界充滿好奇”這一觀點,這兩個男孩對于自己未碰及的愛情世界蠢蠢欲動,而丁佳心則是對于兩個男學生的好奇,所以三個人都陷入了師生三角戀的漩渦。網絡用語的臨時性注定它們不能長久地存在,也不能被所有人接受并使用,作者通過網絡用語暗示著他們三人之間的這段感情也不能長久,不能被全部社會大眾所接受。而選用短信——網絡媒介這一紐帶輸送著他們三人之間的感情,沒有選用通話這一可以撞擊內心的聲音,是因為作者想到了通話結束了,除了錄音,其內容也就不得而知了吧。另一方面,短信可以將難以出口的話出口,并且可以留下感情的見證。短信就是這個見證者,見證著他們他們三人的感情。白天,短信也隨著上課時間沉睡,夜晚,短信就蘇醒著,存儲著他們相互表露感情的曖昧而又明顯的愛情宣泄。
作者簡介:
雷娜(1995.11—),女,漢,甘肅張掖,碩士研究生,西北師范大學,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